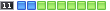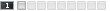文/心之初
贺敬之有句诗: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小时读的,特喜欢。人对爱就想搂,情到深就想搂。革命者就爱搂巍巍的“宝塔”,情和感在这句诗里表述得可真好。我记它在我心里,刚成年就出家,走过了很多岁月和地方。直到我在美国扑腾八年,离开亲爱的妈亲爱的家却从来没回去过又决定要回家看看的那个时侯,这种贺敬之感觉,我也有了。我家在大雁塔下,我双手想搂定大雁塔,雁塔下有我的童年和青春。
二十三年多了,我回过五回国,每回的感觉都不同。去年底回来,我突然想把我这回故土的五回回变成文字,留做一份记念,把一个在他乡的人用他不变的中国眼看到的中国变写到纸上。真就像歌里唱的: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家。
这二十多年,中国变,迅猛,昏眩;高楼叠起,道法大乱。有点“乱了敌人”,也乱了自己。钱和权,成了鬼,推着磨。
离开自己的国家久了,对国对家都有说不清的想:想那些久违的熟悉,想曾经的温暖。想得痴呆,想了又想。想回去看看,想吃个团圆饭,想看看那些梦里的笑脸。这世上的亲情,不管离多远,离多久,心里就是老想着,老惦记,老放不下。
一回回
订好回的国机票,我欢天喜地好几夜都睡不着。一九九四深秋,我出国已快八年。读完学位后在美国的政府部门干过了半年。天下政府都一样,怎一个“无聊”了得。闲时想总想,国里现在是什么新模样?辩证法说,世间万物,变化是绝对的。咱中国可真是成年累月“绝对”,难得有几天“相对”。变化里好忽悠,变化里好胡说;变化里需要软硬横跨,变化里方显江山老大。咱中国的忽悠, 咱中国的胡说特别多,只是江山老大一茬软过一茬。总设计师也和伟人毛一样,不按常规出牌,让个没怎么听说过的人领着中国走向新时代。
风波过了五年,上上下下,人困马乏;划圈老人在中国南海上画的圈十来年了,圈里有了新世界。改革开放活经济,道理讲起软硬。世上有多少道理是讲软讲硬?印象里,喜儿唱的“我不死,我要活”,是个很硬的道理。党还叫共产党,路走开了特色路。干的不说,说的不干,左右逢源,上下搞活。呼啸的商品大潮,让所有中国心,来个全激荡。发财,先富,下海,是 鬼推磨时代开端的最强音。
我是个普通的读书人,在美国有个小日子,但中国的大浪那会也让我萌出过做点生意的春心。生意是什么?从没做过。但不知为什么,那年我就想去看看中国南海那个圈。想在圈里冲动?还是想在圈里春潮?我也说不清。我那会是个一想就要做的人。先飞深圳再回家。
[B]香港半个夜[/B]
飞机抵达香港,夜半正三更,行李找不着了,折腾三个来小时。还好,没丢。天明,不用盼就要到了,人好困,只好在机场呆着,心想,等东方一红,太阳一升,我去把油条找。八年了,没吃过油条。这油条豆浆,就是我中国心里的“长江黄河”,老在梦里。
香港机场的侯机厅,空荡荡的,找个空椅打盹,不费劲。迷迷瞪瞪,嘴角想必有微笑,“梦里不知身是客”。我的中国脑想着好吃就快进肚,我的中国肚则正等正宗好吃的来临。突然,一阵幺喝把我惊醒,港警查大厅,吓我好大一跳,揉眼两边一看,竟好多美女在身边,警察带走几个,说她们是娼女。平生我可是第一次这般被查,心头的小鼓打了好半天。
天亮了,没睡意了,太阳还欲出没出。十月底的香港风还真有点冷飕。我拖着两个大箱,打的去个热闹点的地方,早看“东方之珠”。港人很勤快,到处都是生活气息。大菜场吵吵嚷嚷,鸡叫鸭叫人叫。让我有了重回人间的感觉,美国是个适合机器人生活的好地方。
一边瞎转,一边瞎想,转着想着就碰到了豆浆油条。三根油条,一碗豆浆,解了我梦里的想。也是我在香港的唯一的纪念。在香港,最苦恼的是跟人说话,同是黄脸黑发中国人,却没法语言沟通。真港语,我是一句不懂,而他人也不是都能讲点英语或普通话。和人说个话,费死人劲,时不时还得写纸片。比如去火车站,给的哥写:TRANSPOTATION再画个火车。就一个多点点钟,我就回到大陆国了。
香港,在刘德华和那英唱的”东方之珠”里,很让人神往。我在香港吃了油条,也算来过吃过。其实途中我还在东京,台北停过。世上到处听着好,当对我言,好不好都得住踏实,吃踏实后慢慢玩,才知好不好。实话说,我对商业大城,都没啥兴趣;但对到过一下,却老是兴致勃勃。
9/1/2010
[em35][em35][em35][em35][em35][em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