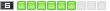一 玫瑰寓言
邻居家的花园长了一棵玫瑰,美丽而带刺,高高的枝丫越过院墙,引来了围观的人群。人人都想得到她。有人架起梯子直接去摘,却被刺得头破血流,跌了下来。有几个聪明一些的人吸取了教训,低声下气地帮玫瑰浇起了水,想用默默的付出换取她的垂青,却反而使玫瑰越长越高,离他们越来越远。于是人们失望了,渐渐离开了。
有个花匠的孩子也在人群中。在别人吵闹时,他在墙边徘徊,看到地上有几个小黑点。原来,这些不起眼的小黑点正是玫瑰的种子。小男孩把种子捡回了家,种在墙边上,用心浇水,悉心照料,耐心等待。
经历了寒冬和酷暑,终于,花匠家的院子也长出了一棵玫瑰,一样地高而美丽,惹人注目。慢慢地,两颗玫瑰开始互相凝视,为彼此间的相像而惊讶:啊!可不是么?就像看见了镜子里的自己……
在红太阳的照耀下,两颗玫瑰并肩而生,茁壮成长,渐渐枝叶交织,血脉相通,终于突破了高墙的阻隔,结合成了一体。旁观的人们被深深地感动了。他们拆去了围墙,将各家的院子连成了一个大花园,而那棵并蒂玫瑰也成了新花园中最美丽的一道风景。
“册!什么乌七八糟的?”钟少德暗暗骂了一句。在他看来,这篇所谓的“玫瑰寓言”实在是滑稽和做作的典范。
文章刊载在《新声》杂志1950年5月号,这是一本名气不大的月刊,办了有些年头了,内容大致是社会纪实类的,从眼前新刊的目录上可见一斑:
“上海市民防空妙招大全”
“苏联红军歌舞团访沪纪实”
“沪西工人俱乐部一日游”
“消防队员的日常生活”
“我要去苏北——少年游民王XX的心声”
……
那篇“玫瑰寓言”上承“苏联红军歌舞团访沪纪实”,下启“沪西工人俱乐部一日游”。放在这么一堆文字当中,这篇有些小资的豆腐干文章显得很不协调,突兀极了。文章署名“时英”。时英是谁?读者如有疑问,只需翻回杂志第一页便可知晓,责任人名单的第三行印得明明白白——“主编助理 李时英”。
“哼哼,小赤佬,倒是无所不用其极啊!”钟少德冷笑一声,摇了摇头。
在这位资深警探的法眼看来,不,应该说,在任何非盲人看来,这篇“寓言”都是一封情书,一封变相且变味的求爱信。预期中的读者不是别人,正是钟少德的女学生。这么说的理由有三:
第一,他这位女学生是西南分局的局花,尚还名花无主;
第二,这本《新声》正是邮寄给她本人的;
第三,她叫关玫,玫瑰的玫。
不过还好,这小赤佬的东西写得真不怎么样,有种延安鲁艺杂交上海亭子间的感觉。作者的努力和创意有目共睹,只可惜效果实在一般。尤其是到了最后,“红太阳”还是忍不住冒了出来,而这一出来就足以令人作呕,那棵“美丽而带刺”的玫瑰貌似也被恶心到了,至于证据么,再明显不过了……
“老师!!”
一个熟悉的女声打断了钟少德的推理,与此同时,声音的主人一把夺走了他手中的《新声》,扔回了脚下的废纸篓。
“老师,您又无聊了吗?!”
抬眼一看,关玫已经站在了他的面前,瓜子脸上带着三分怒容。今天她的话音明显是升了一调,婉转中不失激昂,确实有如高而美丽的刺蔷薇。
“哈哈……大概是有一点,最近没什么大案嘛……”钟少德讪笑道,随之看到了对方手中的案件夹,“又出事了?这次是什么花头?”
“大花头!您最喜欢的那种!”尽管嗔意未消,对方还是切入了正题,“这次是在大自鸣钟监狱。今天凌晨,一个犯人被枪杀了。”
“哦,喋血天牢?听起来有点意思……”钟少德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稍一沉吟,旋即换了一副脸色——
“召集人手,十分钟后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