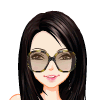//心之初
一九六九年,对中国人民而言,有着特殊且伟大的意义:长着倒八字眉,有着吸毒者的脸,干任何事都要讲个数字(三快一慢,四个第一,五好战士,一句顶一万句),喜欢嚼黄豆,特别会打仗,和我爸同一年生的林彪元帅,正式当上了副统帅。接班人的头衔隆重地写进了党章,但没写万一他死在 “太阳”落山前怎么办。全中国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里里外外男男女女那个高兴,别提了。
“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满怀激情迎九大呵迎九大,我们放声来歌唱,我们放声来歌唱!”。一九六九年四月一号吧(“过路行人欲断魂”的清明节在四月)我们伟大光荣从不犯错的"折腾"(那会胡锦涛大概刚入党)的党的九大召开了。
现在,参加过庆九大的中国人还得有三四亿吧?还能想起那一天吗?
在那个特殊的日子,伟岸脸红(智取威虎山里把“精神唤发”说成脸红)的手稍稍举过头顶,像人民致意;瘦小脸白怕冷的林彪元帅幌本语录紧跟在“红太阳”的后边,“周到脸黄目光炯”的总理保持点和元帅的距离走在领导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最高领导铁三角的最后。铁三角的后边有康生(中国的捷尔任斯基),伯达(政权两杆子的一杆子),“天生一个仙人洞(毛主席专门给她写诗)”的旗手,其他若干。清一色,绿军装,大满贯。
那天,我是在西安东大街红旗如海人如潮,欢声锣鼓敲不完,载歌载舞表忠心,两眼不睁走向前的庆贺“浩浩”里。到现在,整整四十年了,我还能记得和平门东边那个厕所门前的那一望不尽的排队。郭沫若有诗:“人间出现双太阳,天上地下放光彩”其实他很“形象思维第一流”,只不过他的着诗不能在吃饭时来念。亿万人民欢腾“九大”的那天,人人都仿佛是葵花,向日的。
一九六九年,大约是儿童节后,我被我上的小学贴布告给开除了。我成了小“济公”,每天玩得更欢实了,没了组织,也不上山找同志。过完暑假,复课闹革命了,我上哪闹去?没地上学了,大概是我人生里第一次犯难。要吃粮,找紫阳,要上学,买个麻花嘴里嚼。我主意再大也没辄,只好给亲妈老实坦白。爱我我妈没打我,赶快帮我想办法,东打听西打听明查暗访,在我们家属院找到了一个认识离我们家很近的文革前西安最好的中学的革委会副主任的一个人。我妈领着我,带没带白皮点心我不记得了,去见那个教小学的她老公长的特像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白阿姨。第二天,白阿姨领着我妈,我妈领着我去找那个好中学的革委会副主任,他姓呼(应该是呼延),呼风唤雨。呼副主任见到白阿姨,二话没说,就把我编进了七连一班,我耷拉着的脑袋立马支楞起来了,小腰也立马挺直了,站在队里,冲我妈笑。后来我知道,呼副主任那会正忙着勾搭白阿姨的大闺女。幸亏。
人生如梦还是如戏?转眼,我个小坏蛋,又成了好中学里一学生。
这人呆的环境,真就像染缸。我们那拨中学生,甭管周五正王的,婷婷玉立的,肌肉发达的,身上没肉的全都(或许有别的)三年没念书,女的比我们高,谁让人家发育早。大伙每天上课都得首先站起,眼睛向前,脸色凝重,“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看着身旁高我大半脑袋的MM,我心里就来气,甚至都想当黄世仁。每天要上五六节课,想当黄世仁的念头每天在脑子里闪过十一二次。
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明打明地瞎掰。那会每天上学,光早请示晚汇报就让人想上吊。我们那会还是小小少年,真不知有理性的大人们是怎么活过那些岁月?
上了个曾经的好中学,高兴了没几天就郁闷不堪。但那年头,人是不能郁闷的,也不能自杀,你得成天唱语录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你还得跳忠字舞:雪山上升起“鼬”红太阳,翻身农奴把歌唱唉把歌唱,献上一杯青稞酒呀(九十度弯腰,两手做端酒状,抬头,碎步向前,注意节奏,来来回回。最后,巴啐嗨!上学比上工还累。
我的第一个班主任,和贞观年间的皇上一个姓,单名一个军。是个教政治的,兼教体育,那会政治就是体育,没有那会的全民体育,把人的脑袋弄傻,把身子骨在吃粗粮开大会文攻武卫里给弄结实了,孙儿们怎么会能在二00八北京奥运里拿金牌第一。这和没有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卓绝,就不可能有今天红哄的江山大家红火的日子是一个道理。我的李老师挺喜欢我,知道我小时侯描过红,老要单教我写美术字,我不爱学。我爱我,不爱美术,美就行了。
中学,是追梦的日子。头学期,没多大功夫就没了。一九七0年,会咋样呢?
文字,有一种奇怪的力量,当你把你生命里所经历过的苦痛变成文字,那苦痛或许就不太那么撕心裂肺肺了。我们这一代人,生命里最痛苦的事情是:我们曾最相信最爱的人把我们骗了,而且在我们生命还蓬勃的时侯,我们就明明白白地知道,我们被骗了。
被骗,其实也没什么好害怕,人活着,怎能不被骗?大不了朗读一下普西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风风雨雨,晃晃悠悠,转身飞身,坚定或者呆坐,葵花就得向阳。
2/1/2009 写
[em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