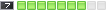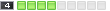是一粒风烛残年的虫子,仰面八叉躺在一堆枯草前。我蹲下来,数了数,共八条腿。虫子似乎知道有人在偷窥它,前面两条腿动了动,想翻过身子,努力摆一个好看的姿势,但最终没有成功。也许,它已经在风中耗尽了所有的气力,当看到这堆柴草的时候,就停下来,把这里作为最后的栖息地。
我把虫子轻轻放到手掌,想暖热它,让它重新活过来,但却无济于事,它已经老去,永不会醒来了。
一阵小风越过柴草落下来,它似乎专门来告诉我,小虫的翅膀不是我吹折的,它在空中飞得太久了,自己掉下来了。有一根柴草在枯草堆里抬起头,对我说,我们只想为它挡风御寒,为它筑起了一个窝,可是它没有入住,这个窝里住进了一条小蛇。它们争相向我诉说,对一粒虫子的死亡表达深深的歉意。它们知道,我跟虫子是最好的朋友。
这是我熟悉的虫子。很多年前我在马寨村居住的时候,常常与虫为伴。早晨醒来,必定有一粒虫子在我床前守候,默不作声,静静等我从梦中醒来,它等我没有别的事,只是来看看我,同时也让我看看它,它知道,我醒来看到它在身边就不寂寞。黄昏我去田地里干活,虫子们绕着我飞,嗡嗡嗡地唱着歌,可惜它们吐字不清,我听不清它们唱什么,但我知道它们想表达什么。它们商量好齐声对我说,我们来过,要记住我们啊,不管你将来走多远的路,记住都要回来看看啊。我直起身来,捶捶有些酸疼的腰,拄着锄头,有时是一把铁锨,歇一会儿,用目光跟虫子们交流。偶尔有些冒失的小虫飞到我脸上,吻我一下,接着又飞回队伍里。我眺望原野,看到近处有人在弯腰劳作,但看不到他身边是否有虫子在飞舞。我还能看到远处山脚下的人,也许是距离太远,也许是黄昏太浓,他只是个模糊的小点,像一粒在原野里蠕动的虫子。
我搬离马寨村的时候很兴奋,离开这样小的一个山村是村里很多人的想法,我是其中为数不多把想法变成现实的一个。
走的时候我跟邻居们道别,他们知道我要搬到很远的地方,都有点不舍。你大爷走的时候还不到二十岁,现在都八十多了,想回来看看,一位婶子拉着我的手说。
走的时候我在各个屋子里仔细查看,在厨屋里我看到没有锅的空空灶台,这里曾经冒出无数的炊烟,一次次让饥肠辘辘的我带着甜美入眠,如今它像一圈大大的伤疤,在空屋里静静无语。空空的灶台上趴着一粒虫子,不忍离去,好像这里有很多它留恋的东西。圈棚的房顶裂开了一个角,一缕阳光正从那里漏下来,照着拴驴的石槽,里面有一把断根的稻草。我知道圈棚里住着很多虫子,它们曾经跟驴一起度过无数个漫长的冬夜。
走的时候我在院子里站了很久,院子南墙已经坍塌了一半,是一场风雨在某个夜晚把它推倒,一窝小鼠在破墙里凄凄哀嚎了整整一夜,我曾经打算找个时间修一修。
走的时候我没有太多留恋。去外面寻找不一样的世界是我很久的梦想,我也以为我会经常回来看看。可是走了之后,我才知道回一次家是多么不容易,离开之后我才明白,那些过往令我如此怀念。青山绿树怀抱的小村,天天在田地里劳作的乡人,残垣断壁杂草丛生的院子,以及小院里住着的那些虫子们,都是我一道一道的梦影。
一粒虫子在今天老去,我的很多虫子在很多个秋天都这样在缕缕夕阳中一一老去。夕阳说,它们是自然消亡的,走的时候很平静,我把一缕光披在它身上,走的时候它很温暖。土说,虫子都会老去,就像人最终也会老去,不管他走得比路远,还是飞得比尘土高,最后都会跟我们在一起,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我说,我从没有忘记它们,一粒粒虫子,从我一出生就伴随着我,我离开小院时,曾经仔细嘱托阳光、秋风、泥土,要替我好好照顾它们。没有它们,我就无法回到家园,密密的虫鸣是我回家的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