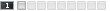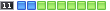近来,有一种思绪野草般疯长,徘徊河边,彳亍街道,荒草凄凄,惶惶然的阳光下,心像垂系辘轳的古井。夜晚翻书,看到如下文句:“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顿时耳酣目热,我突然明白:春,快来了!
家乡的春天孕育在冬梅枝头。腊月里,瑞雪飘飞,褐色的虬枝,洁白的雪花,掩盖着磬口的鸭雏黄。日日从它身旁经过,推摩托车时偶尔还会因为碍路,以致枝折花落;邻居那只凶猛的藏獒也时不时蹭着它的枝干;天晴时,调皮孩子的皮筋一头系着它的主干,一头绑着竹椅。年过八旬的莫爹有次失足滑下,幸而被梅枝挂住才免于伤筋断骨。总之,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它存活了下来,而且打我有记忆时好像它就立在路边了。
如果,一个人可以精致到以梅花雪煮茶,那一定是妙玉。 远远的,梅花笛幽幽穿过泱泱水面,低诉而来,妙玉,独立花下,陪伴她的只有身后长长的影子。团聚、喧闹、繁华、绚丽,一切的浓妆重彩都被强制的从她身边抽离,所保有的,只有一颗孤寂骄傲的心。
阳光,渐渐有了温度,大地的内心,也变得五彩缤纷。要不,这些永远被踩在脚下的泥土,怎会滋长如此荣荣的青草、开出那般美丽的花朵?大片大片的紫云英铺满田野,接着是油菜的金黄明亮整个三月。柳眼桃腮,各竞风流;莺莺燕燕,悠扬婉转。“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祁”,《诗经》,给了我无尽的遐想,正是这样的遐想,让春天穿过淅淅沥沥的忧伤,走进母亲种着红苔菜香芫荽的园子。
那天傍晚,我跟着母亲在园子里扯杂草。苔菜正抽苔,芫荽发出脉脉的香气。那时,父亲经常出差在外。母亲穿着父亲的大衣裳,但仍显臃肿。其实母亲本来比较瘦小。那时的我太小,不知道母亲腹中有了我的小弟弟。突然,母亲劳动的手停了下来,她急急地对我说:“快回去叫你奶奶来。”看着母亲严峻的眼神,我知道事情紧迫,撒腿就跑。园子离家较远,中间隔着一条河。正是初春,河水不深,可趟水而过,但我听着 “哗哗”流水,莫名的心慌,把刚伸出的脚收了回来。然而,当我气喘吁吁跑回家时,却发现母亲已早我回家,躺在了床上。奶奶在烧开水,平时很少登门的接生婆谢婆婆站在母亲床前忙乎。“快出去玩。”已是大姑娘的金莲姐连忙把我拉出房间。“你妈妈要给你添个小弟弟啦!”谢婆婆七岁的小孙女悄悄跟我说。“你怎么知道一定是小弟弟?”“我奶奶说的呗。她看得可准了!”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后,发现父亲回家了。谢婆婆不在了。奶奶看见我,摸着我的头说:“好孩子,能当耳报神了。昨晚你妈妈是趟水回家的。”我着急地寻找小弟弟的身影,奶奶说:“没了。可惜!还是个伢子呢!”直到我自己也做了母亲,我才把隐藏在母亲内心的伤痛读懂,而它也成为我成长过程中刻骨铭心的事情之一。可以这样想象,当父亲和我,在大路上奔跑的时候,我的母亲,聚集着她生命中所有的力量,趟着二月刺骨的河水,只为她心爱的孩子能平安降生!可是天不遂人愿,孩子窒息而亡……
一个月后,母亲的身影又出现在了园子里。她弯腰摘菜,光影氤氲。这时,一只蝴蝶翩翩飞来,竟然停在了她的发梢。母亲注视着那黑色的小精灵,唇角渐渐有了笑意。这是她失去孩子后第一次笑。那天午后,我在我自然成型的眼睛画框里,装上了一帧画面:母亲梳着一个长长的发辫,阳光像珐琅梳子由上至下地滑落,我听见春天的气息在她的长发里,哗啦啦地翻腾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