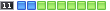今年似乎比往年都要冷。雪,已下过几场。昨天黄昏时分,不得不出门买趟菜。帽子、围巾全用上,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然而,凛冽的寒风夹着雪花,仍无情地往脸上、脖子里钻。到菜场时,人已寥寥。女儿喜欢吃饺子,买点肉,再称两蔸大白菜。一问价:大白菜涨到了一块钱一斤!“前天还是四毛呢!”“这样冰天雪地的,明天还会涨,一块钱一斤只怕是调都调不到了!”菜农呵着气称菜说。我付了菜钱,匆匆往家赶。
现在是除了工资没涨,啥都涨了。粮油、液化气、水费、电费,样样都贵。一千多块钱一月的工资,别说存多少,只能应付基本生活开支,还要祈祷一个月的人情别太多!我们还好一点,两人拿工资,只有一个小孩。有些光靠一个人菲薄的收入养活一大家子,那多不容易!我们一个小巷子百把米十多户人家,真正是双职工的家庭才两户。他们怎么生活?开娱乐室,摆漫酒摊,甚至做让人恶心的“生意”。只要是还能走动的老男人路过,就有并不年轻的女子笑着嗲嗲地问:“进来喝口茶吧?”一来二去,她们就有了较固定的“客源”,电话联系,更为方便。做这样“生意”的大多从乡下来的,早过了如花似玉的年龄,孩子大都大了,在外打工。她们租住县城,房东提供“庇护”,也收取适当数额的费用。她们的丈夫偶尔来县城看看,住一两夜就回去,终年守着几分薄田。人,难道要这样活?大家已见怪不怪,可在我觉得说不出的悲哀沉重!
习以为常能使人对一切变得淡漠,所以,最能唤起我们对美好事物记忆的,正是我们似乎已经遗忘的事情,在我们记忆之外,存在于婴儿时的母亲乳汁的气味之中,存在于邻居送来的一块时新糕点里面,或存在于冬夜的“荜拨”作响的火苗中。在凡是我们的头脑来不及记忆,或不屑于贮存,可是在一瞬间突然洞现的地方。更确切地说,是在我们心中,但是避开了我们自己的目光,存在于或长或短的遗忘之中。在她们的身上,我看到的分明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小说里才可能出现的生活情景。我记忆里残存的美丽乡村的影像不是这样,那里有大片的荷塘,乳白色的菱角,那儿有哪家都可吃到便饭的乡邻,那儿还有袅袅的炊烟下勤劳善良的母亲……
雪地里,一行行污浊的脚印,显得触目惊心。卖甜酒的老婆婆在叫卖:“甜酒糯米浆”;一个担小菜的中年男子缩着脖子急急走过,雪花飘落在他没戴帽子的头上; 望望灰蒙蒙的天空,雪花还在飞飞扬扬,似乎要把所有的肮脏掩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