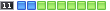母亲在长途电话里跟我说,邬伯伯去世了,是前年十二月的事。
果然是这样。
三年多前,我从伯伯家告别出来。他亲自出来送我。军队干休所大院里整洁干净,路旁杨柳轻拂、泡桐唏挲作响,我左牵右拽地带着孩子们走着,伯伯的话传到耳边:“欣欣,不要再生了啊。”
伯伯又说了什么,我嘴里应着,似听非听,心里有些怅怅的。伯伯这是心疼我带孩子辛苦。
我的到来,伯伯是真高兴。“我这个人是人来疯。”他这样说,兴奋溢于言表。 他不嫌孩子们吵。七岁的宝宝,中文不会说几句,要跟伯伯下象棋。棋桌上,宝宝煞有介事,伯伯高声笑着。两个五岁的双胞胎女儿,总是动这动那,一会儿也坐不住。伯伯的太太李阿姨的身体不好,腿也有毛病,忙得一个劲地给她们拿吃的。想起十多年前死去了的父亲,我真希望自己有伯伯这样一个父亲,孩子们有这样的一个爷爷。一起户外散步时,伯伯叫住一个手里拿相机的年轻军人,让他为我们照几张相,年轻人好奇,问我是伯伯的什么人。“她是一个象我亲女儿一样人。”伯伯说。
可我这样一个人,福份不够。几十年中,与伯伯见面并没有很多次,可他使我有如此亲近、尊敬和依恋的感情。对我来说,他是比其他长辈都特别的人。如果当年和他的儿子结了婚,我就是他名正言顺的家人,而现在,我只是个晚辈,一个已故朋友的女儿,一个远住海外,断了来往的人。我平淡地道了别,忘了为他请的午餐道谢,拉着孩子们转身走了。
奇怪地,我告诉自己不要回头。伯伯可能在后面看着我,这又不是最后一次见。一面心里又想,山隔水远的,难道这是最后一次?
我六岁那年,文革如火如荼地搞起来,两、三年下来,运动不仅不减弱,反而越来越厉害,涉及的人也越来越多。父亲被揪出来,挨批斗,住牛棚,母亲在单位也被揪斗,还被关进监狱了一段时间。我们住的单位宿舍大院里,批斗父亲的大会就开过两次,家也抄了两次。邻居像躲避瘟神一样地躲着我们。打倒父亲的标语,贴得家门口,大街上都是,我成天担心同学们看到。还担心父亲因为受不起压力自杀什么的。厂里已经有人自杀了。我们一家三口人,生活在孤立无助,令人窒息的环境里。
那是春节的时候,家里突然来了客人。伯伯穿着军装,带着一个大眼睛、慈眉善目的阿姨,一个大我四、五岁的高个子男孩,还有一个与我年龄相似的女孩。他们全家来看望我们,这对我们,真如久旱的甘霖、雪中之炭火,父亲兴奋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多年以后,他还带着骄傲和感激一再提到伯伯一家那次的来访。
伯伯和父亲的来往,可以反映出伯伯交往广阔,平易近人。
父亲出身北京郊区贫民家庭,四五年参加解放军。他生前对当年的事讲得很少,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参加过战役。(但知道他曾经因为玩枪走火,把一个战友的腿打伤,自己吓得昏了过去的事。进军西藏是去过的。有照片为证)。他参加过部队的文工团,练过唱歌。因为没有什么音乐天分,又改学摄影,跟着从苏联回来的苏伯伯(当年广州起义领导人苏兆征烈士之子,周总理的干儿子)当助手,后来成了一个很好的摄影师。他们的部队应该是属于北京军区的,他们几个战友都是当年北影厂长汪洋的部下。后来归到地方,他工作的电影厂直属文化部。他主要的工作是拍摄国家领导人的外事接见,出国访问,党政会议,还有一些党政、国家领导人生活资料片等。文革开始时,父亲还因为拍摄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在拥挤混乱的场合,腿部被主席和总理的车一前一后挟伤。不久,他就被揪出来,戴上了反革命分子,假党员等帽子。一次在批斗会上,头被一个造反派踢成脑震荡。
伯伯的历史和处境其实与父亲很不同。他的回忆录里有很完整的介绍。他是山西忻州人,从小父母双亡,因为不堪忍受收养他的堂伯父的打骂虐待,在三七年底,不满十一岁的他独自逃出,流浪中,辗转参加了晋西八路军领导的军队,和日军打过仗,负过三次伤。四五年,从前线被调到延安,从事中央保卫部门的工作。从周恩来院外的哨兵,毛主席警卫班的战士,到建国后成为金日成、赫鲁晓夫的访问时的卫士长。文革初进驻钓鱼台,负责包括陈伯达,“中央文革小组”等保卫工作。后来在所负责的钓鱼台国宾馆里接待过访华的基辛格和尼克松。因工作关系,他跟江青打了多年交道,受过不少刁难,又险些卷入政治斗争旋涡。后来他还亲自参与抓捕“四人帮”的行动。周恩来去世之前,最后想见的人就是他。他见证了许多政治斗争,最后又为政治所累,受过委屈,又被命令提前退出工作岗位。他从一个流浪的孩子,参加革命,后来通过自学和进修,达到了很高的文化水平。他的命运,起伏跌宕,非比寻常,他的作为,充实丰富,可圈可点。
我最初认识伯伯,应该是他在钓鱼台工作的时候。父亲曾为中央领导外事活动摄影,和伯伯在工作场合认识,伯伯等于是父亲的领导。他当时的身份,与父亲是有很大距离的。文革残酷斗争,没有触及到他。他所经历的政治斗争和生存危机,与父亲的不是一个层次。
我当时不太懂这些,只是真心地喜欢这家人,特别是伯伯。他中等身高,一身整洁的军装,浓眉、笑眼、高鼻、鼓脸,给人一种温厚的感觉,一口浓重的山西口音,说起话来声若洪钟,把我的名字“欣欣”叫成“星星”。其他长辈,往往无视我这个年龄的孩子,而他亲切地对我讲话的慈祥,在那冷竣的年月里,让人感到温暖。我小他们的女儿一岁,他要我们交朋友,还邀请我去他们家玩,晚上就住在那里。
他们家在钓鱼台的宿舍楼里。那时候,条件那样好的房子不多。宽敞明亮的房间,厨房浴室俱全,全天都有热水供应,随时可以洗热水澡。伯伯的女儿,性情安静,随和。那个哥哥长得高大挺拔,眉眼英俊,不大理会我们。两个女孩儿缠着他玩,才答应跟我们打牌。他总是赢,赢时就说“洗牌、洗牌,劳动、劳动。”我们还是很开心。不久,他就当了兵,穿了军装的他更英俊了,让我很羡慕,觉得他高不可攀。
他们生活简朴,饮食简单。阿姨是山东人,炒菜时按照伯伯的口味放醋,刚吃时有些酸,后来也觉得很好,青菜变得很鲜脆。
逢年过节时,我也会去伯伯家玩。一次,部队开春节联欢晚会。在一个大礼堂里,到处是军人和家属,演出开始前,领导同志入场,大家热烈鼓掌,我看见几个领导模样的人走入会场,我认出前面是汪东兴,他后面就是伯伯。我不知道伯伯是什么级别,父亲说他是八三四一警卫团副团长,我想他是个团级干部。后来才意识道,这跟一般团长不一样。
“四人帮”倒后,我上了大学。伯伯的位置也变了。他从中央被调到安徽省军区当副司令员,家也搬出了钓鱼台宿舍。他这时来我家,与朋友们见面时,讲话时仍是笑声朗朗,谈起调动时有些低落。我不解,后来才意识到,国家改朝换代了,一朝君子一朝臣,伯伯已经不再被重用了。也许是那会儿,他开始喜欢钓鱼。他给我们看了一把钓鱼竿,深红的木干,一节节的可以接在一起。他说这是甩竿。我想,将来我有了钱,一定给伯伯买一付好鱼竿。
伯伯家的哥哥,从部队退伍回来,当了工人。他变得更高大,健壮的体格。我们见过几次面,他借一些书给我看。他不是我印象中那样骄傲,但我们之间似乎也没有什么可谈的话题,后来连见面的理由也想不出来了。年少时曾向往,将来嫁给一个象他那样的英俊的解放军。这个幻想,也如其它许多美丽的梦一样,不意之间苍白地消逝了。
八十年代末,我出国去了澳大利亚。十多年后,我的生活改变了,国家更是改变得让人有隔世之感了。再见到伯伯,和他交谈,我知道会有分歧,但又难以抑制地想谈点什么。文革的发生,毛泽东的评价,当然是最敏感的问题。不想和这个一直在政治中心工作的人发生直接冲突。我装做偶然地谈到李志绥。伯伯说,李志绥他在干校时打过交道,是一个没有骨头的人。开个批评会就把他吓得要命。这样的人写的东西,可信度不会高。伯伯又说,你想想,毛主席那时有多大年纪了。五十年代就有六十多岁了。他的身边又有很多的工作人员,有些事情是不可能的。我又说:那么文革呢?他没有责任吗?我的记忆中装满了一次次的运动。反右、镇反时我还没有出生,但后来的事我记忆犹新:反修防修,造反有理,揪出“走资派”,打倒“一小撮”,铲除“封、资、修”,清理阶级队伍,到后来又“批林批孔”,“儒法斗争”,“批右倾翻案”等等,一批批人被整,被抓。做学生的我们,也会跟着搞,整老师,整自己。 伯伯说:文革是错了。但开始时的确是为了反修防修。他说:你读过‘九评’吗?当时面临着多大苏联的影响和压力。如果不搞,就要修了!他又说:后来运动发展到了失去控制的地步,是谁都始料未及的。这个时候,阿姨在旁边忙给我递眼色,轻声说:“你伯伯有血压高,不能激动。”关于政治的谈话,就这样结束。我转过话题,问伯伯有没有写回忆录。伯伯说有,马上就找出一本,回忆录的标题是:[《红色警卫_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XX回忆录》。伯伯在扉页上写上“XX小女存阅留念_邬XX二零零四年十月”。我又问,是不是所有的事都写进去了?伯伯笑了,说:当然不是。
不能谈很多了,但我相信伯伯绝对不是完全谈不来的那种。沉默的我,感触良多。在我们之间,有一个历史的代沟。但善意、良知、通达的个性,可以轻易地搭起一道道的桥梁。后来读伯伯的回忆录,更看到了,他不但有过人的记忆力,清晰的思路,看待事情还很独立豁达,既忠于组织和军人的职守,又有历史客观的高度。书里写的事既有趣味,更有纪实价值,让我受益良多。
战乱动荡的时代,造就了伯伯和父亲他们一代人,为了理想而生活,而工作,而受苦,而受不平的对待,而他们中的多数人,仍旧怀着一样的理想,有着同样的思想方法。我们这一代,受的是理想教育,也经过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却放弃了父辈的理想,认识到人的尊严和权力,自我的价值,是更可宝贵的,是更要为之奋斗,为之追求的。我们成为自私的、务实的、反叛的一代。两代人之间,无可避免地,有全然不同的见解,有难以相融的观念。老一辈看我们,会认为我们是没有理想、不懂历史。我们看他们,是头脑僵化的时代的牺牲品。
为了理想,他们奋斗过、牺牲过,而结果是后代的我们,把他们从精神上、成果上都否定了。是非曲直、功过得失、道义良知。难道历史的真实是,一代的主流总是被后一代的主流否定吗?也许正是。每一代都有其不同的历史使命和与之相应的道德价值观。每个人也有其独有的命运和世界观。我自己,一个只为自己活着,更离开了自己国家的人,对长辈们仍旧报有尊敬和很深的感情。离开了中国,给了我们从全新的角度看世界的机会,也使我们对世界产生更多的困惑。角度越多,困惑也就越多。不记得是谁说的:历史不是苍白的。在我看来,历史也不是一条线,不是一个平面。历史是多层面、多空间的。像大海、像山峰,又都不确切,它给每个人的人生和内心,都刻上不同的痕迹,印上不同的烙印。
我发感慨地脱口而出:“这些年,世界的变化真是快啊!”
伯伯听了,也同样地感慨道:“是啊!‘长江后浪推前浪’嘛。”
他爽快积极的态度让我感到安慰。他看到了,逝去的、现在的、还有未来的,不就象长江的流水,一浪推过一浪吗?
伯伯看起来心境开朗,晚年过得很幸福。参观伯伯的家,宽大的房间,厨房、卫生间设备也很好。平时伯伯跟阿姨还有一个保姆住。他们的女儿有时也回来。学校放假时,孙子也来住。伯伯对我说:以后你回国,也过来住,这里房间多、方便。
伯伯给我看了一家人的照片,儿子,媳妇,女儿,看上去都很好,孙子已经长成一个高大的小伙子。很多伯伯旅行时跟朋友们的照片,不少是年轻人。伯伯还是喜欢结交朋友。阿姨也找出了一张他们保存的父亲当年工作时的照片送给我。在书房里,我看到伯伯写的毛笔字,就提出要几幅。别看他军人出身,多年来不断的练习,毛笔字写得很漂亮。我说要挂在家里。伯伯高兴地挑出来几幅送我,还叫我去琉璃厂去一家店去裱,说提到他的名字就会给优惠。
我建议伯伯出国,说如果能来澳大利亚看我们多好。伯伯说,以前的工作性质,不允许他出国。也许等到若干年以后,或许可以得到出国签证。
若干年还没有到,伯伯就去世了,也没有再给我一个去看望他的机会。去年十月回国,因为安排紧,没能跟伯伯家里联系,连他去世了都不知道。妈妈说,伯伯得的是肺炎,医院没有及时用药,给耽误了。这让人心里更加难过。伯伯还没有过八十岁的寿辰。
我想对伯伯说:天上又多了一个我爱的人看着我,我会好好地生活的。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于澳洲悉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