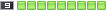梦 与 睡 眠
刘荒田
午后,踱进下城一家电影院,花十来块钱,为了消磨上班前百无聊赖的两三个小时。看了一出《访客》(Visiter),说的是非法移民和美国西海岸一位活得极乏味的教授的纠葛。片名可作多重解读,移民于新大陆和土生美国人而言,是访客;教授到移民羁留所听完被囚禁、即将被遣返的新朋友,是访客;扩大开去,我们在世间,也是访客。影片中一句平淡的台词,却感动了我:“若要梦,得去睡觉。”如果说梦也是访者,那么,你须布置一道让梦叩击和推开的门,有让梦活动的空间,还得有让梦存活的时间。梦的计时方法和非梦时间不同,烂柯山上一梦以百年为单位,一觉醒来,连斧柄都腐朽了。由此可推论,“梦时间”和世外桃源、仙界、天国这一类我们生前绝无缘进去的好地方相似。这个算法倒也和“日子越平和安宁,时间消逝得愈快”一普通常识合拍。
“唯睡乡才有梦”这一命题,和“有耕耘未必有收获,无耕耘必无收获”相似,睡眠未必有梦,无论美梦还是噩梦;无睡眠的“白日梦”,严格而言,只是走神而已,肯定不成片段。好莱坞的大导演斯皮尔格的“梦工厂”,开明宗义,以“梦”为产品,换言之,这工厂的功能和睡眠相同。所以,进电影院就是“入睡”。银幕上悲欢离合,恩怨情仇,人性的艳丽与黑暗,尽在观众眼前浮现。看电影就是“一枕黑甜”,如果从头到尾全神投入,看出一脸泪水或者笑疼肚皮,那便是酣眠。
看电影和睡眠稍有不同,前者的梦是现成的,笃定的。《访客》一片中的老教授,20年来教同样的课,每年把教科讲义抬头上的年份用涂改液涂抹掉,仍旧讲得头头是道。但他向非法移民的母亲承认,陈陈相因的日子,无异行尸走肉,直到老年,他才在随非法移民学习击鼓的过程中,从咚咚的鼓声和急骤的节拍找回因丧妻而失去的爆发力。我随着他在地铁站拍出的鼓声梦游八方。至于睡觉,能否做梦,做什么梦,却绝不由人说了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