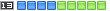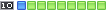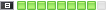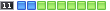看过电影和原著后, 又看到一些有关评论, 其中有说故事是”一个自欺欺人者的非典型自我毁灭历程”, 就似乎是太批判性了. 他似乎也不太了汉纳内心的世界(在作者笔下内心的世界), 他似乎认为人的内在世界是一贯的, 有明显的动机, 事实上, 这是不可能的. 人, 大多数是活于浮移笼统的不确定中, 与其说汉纳是因为内在世界的定型而会如此, 不如说是她内心的不确定(亦不可能确定)而如此. 实际上, 在第三帝国中生活下的人, 除了那手操生死大权的极权者外和他们极端拥护者外, 其它人亦不可能不如此. We live on, only vaguely are we aware of a purpose, even a direction.
汉纳说的: It does not matter what I do. It does not matter what I think. The dead are dead. 不是悔疚, 不是自辨, 而是反映出她认知的现实. 把今天的现实来批判往日现实的善恶对汉纳是没有意义的, 她需要的不是原谅 (除了死者, 她不需要其它人的原谅; 甚至是死者, 她亦觉得没有必要得到他们的原谅, 事情就是这样, 那就是了.) 汉纳在第三帝国时至她自杀的一刻, 都不为她所作的有一丝的罪恶感, 这与策划这一切的人不同, 对她来说: 她只是做她必须攸的, 没有所谓良知, 亦没有所为逃责的问题 (她的早期逃避只为了生存和不被捕), 反之, 同时是被告的其它人内心是知犯了滔天大罪, 所以才希望脱罪, 甚至不惜把所有罪名推向汉纳. (我们可能觉得屠杀鸡鸭是残忍的, 可是屠夫本身没有这罪恶感, 他只是做他要做的事而已, 不是他发明杀鸡, 他没有创出菜色要杀鸡, 我们又能否看着他而觉他满手血腥? 我们不杀鸡而吃鸡的, 是否更应负上责任?)
第三帝国中的德国人何尝不是如此? 他们也许没有亲手杀人, 却一直拥护这个制度, 甚至从中得益. 假使德国是战胜了, 而不是战败, 他们会如何看这段历史? 会否追究屠杀的责任?
甚至后来一代的德国人, 以和纳粹划分界线为责无旁贷, 可是, 真的能划分吗? 他们的父辈都是同谋犯(无论是否积极参与)在与当时的现实不一样的情况下的骂屠夫, 是否有意义? 只有当有一天他们面对同样或近似的现实时, 他们能拿出勇气来说"不!", 这种正义才是实质的. 因此, 唯一有资格说他们是清白的就只有那些曾站出来反抗说"不!"的人(如Sophie Scholl 等白玫瑰运动者), 同是共犯者能指控执行者? 因共犯者的行为而幸存下来的又能指控父母辈的共犯者?
所以,Reader 不单是一本有关汉纳和少年的"爱情"故事, 所审的只是汉纳与其它在犯人台上的被告, 甚至不单是第三帝国中生活的并犯者, 而是每一个以控诉指向汉纳等的德国人.
汉纳在法庭中向法官问了很有力的问题: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 if you were there? 法官没有直接回答, 这句话亦问向我们任何一个人 当然, 理智会对我们说: 当然打开门放出被困的人啊. 可是, 真的吗? 如果是平时, 这答案是当然的. 救人就是英雄. 谁不愿意? 可是, 当救人可能会成为叛徒 (近卫军可能随时会回来), 我们会吗? 何况, 当时在汉纳的脑中的priority, 救人不是第一个浮上来的念头, 那个decision chain 与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很不一样.
汉纳不是穷凶极恶的人, 不像如希魔及他手下的纳粹党狂徒一样冷血屠杀, 她当然亦不是一个英雄, 她亦没有想成为英雄的念头. 她只是一个平常人, 在命运的驱使下去干一些事(她参军是因为她不识字, 因此在西门子没法呆下去),她没有亲手杀人, 只是因为她没有打开锁上的门而导致里面的人死亡, 而杀害那些人的直接加害者是盟军的空军, 只因为不想把未投尽的炸弹带回去就把它们丢到一个没有军事价值的小镇上, 而这些人, 因是战胜者, 没有人追究责任), 在这之中她没有使用她的良知, 亦没有蓄意埋没她的良知. 她也许不值得我们"原谅", 可是我们有权把指控的手指向她吗?
汉纳到临死前也许从不要求Michael的原谅(这种原谅本来就是没有意义的, 当"原谅"者不具备原谅的资格时, "原谅"很可笑; 她甚至不需要那幸存母女的原谅), 她需要的只是他的接受, 作为一个聆听他阅读者, 作为一个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