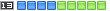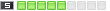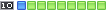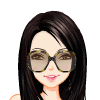//心之初
要是还活着,我爸今年正好一百。他和林彪是同年生人。那一年,慈禧和光绪都还活着。
我爸比我大几乎整整半个世纪。据说老爸岁数太大,生出的孩子不好,我没做过统计考据,也许有几分道理。三十多年前,和现在不一样,那会的人都比较显老,如果再喜欢倚老卖老,那就更加显老。从我记事起,我爸就是一个老学究,老先生和老头。“老学究”是说我爸爱念书,鼻尖常在书上走。老跟毛主席一样学英语:翻个“没死的英雄麦贤德“就能翻半个月。再闲着就填词:“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还偷偷地和“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相比。“老先生”是指我爸老爱“说人”,他还能说得动话时,就总是不停地说着那个时代的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是也不是,不是也是。而“老头”则是我爸总是自己让自己:“看上去很老”,他近视一千五吧?.我呢,见着他就绕着跑。
在我爸百年辰诞,好久不写文章的我为领我到这个世上来的人写下段文字,用我的记忆和我的心写,不想艺术加工,算做永恒的记念,因为,是个正常男人就能做爸。或许别人的爸伟大,但我爸就只是我爸。他有他的品性,他有他的可爱。他走了二十二年了,我并没忘了是他带我来这人世。
人世,是个“一天等于二十年”,“坐地日行几万里”,”我们自己哭着来,人家哭着我们走”的好地方。假如有人走时没人哭,说明走的人坏或者洒脱,不活在活人的心里让活人难受。
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以前”,抗战后期和抗战胜后,据我爸跟我说,他是国府重庆保险总公司的付总经理。同时还给我讲,保险,什么的干活?就是用嘴巴把别人的钱说到自己的包包。我爸在打完小日本的那些国共开战的日子里,赚了不少的银子。我爸能说,赚钱不难;守钱不能靠“说”,他自己知道不行,所以,干脆不守,上班精业,下班打麻将玩钱,吟诗词谈天。再不就给“左翼”捐钱。我们家的照像本的头一页,就是郭沫若赠他的亲笔签名的照片,以感谢我爸为党的文化事业捐的钱。郭沫若后来写臭诗,让人喷饭,其实老郭真是才子,很多喜欢不喜欢他的人,都得让他坐中国现代(这年头,我已不知什么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二把交椅,至少刘大杰先生是的。我爸爱不爱党,我不知道。因为给钱不一定是爱。
重庆解放得比北京晚点。解放,人民翻身,“当家做了主人”了,“社会的全部生产资料和产品都归了人民所有”了,人人都是人民,人人都没管着什么,人民的人人不知道实际上人民就只是个人人。人人都唱:“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新中国不需要保险公司。中国刚一新,我爸就失业了。按那会的“阶级划分法”,他成份有点高,但他又一没地二没钱,因为他把钱都买成了笔挺的西装,锃亮的皮鞋,还有好些书,所以党和政府,就没要他的脑袋,也没让他坐牢,只是让他失业。(成份高就失业,想想心中真有些不平,但失业总比毙了强,我爸也就闭了嘴,(“红太阳”上天安门,说给全世界说:咱站起来了,但没告诉咱站起来后干什么?)。我爸没事干,没钱挣,就写诗,就生娃。
一九五零年,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欢天喜地得站起。我爸,打一手好算盘,写一手好文章,却不能“为党做工作”,在没工作的日子里,城里租不起了房,我爸就住到了重庆乡下的丈母娘家,整天“山清水秀”,整天“雾里看花”,和我妈生下我哥,取名五零。我长大才知道:我哥是在娘肚经的“新旧社会两重天”。
刚解放,全社会都是“新生”,没人想挣钱,只想为党分忧.。毛主席为首的党那会刚开张,先忙着用中华儿女的生命去帮金日成统一朝鲜,也不管台湾还没解放,也不管抗战前的战,八年抗战,四年内战多少人都还没娶个媳妇给自家留个种尽个大孝。抗美援朝,合辙对仗,“雄“蹴蹴”,气昂昂“,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决心大,没人管待业的我爸。当兵,岁数太大,我爸就自学毛主席:“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失业不可怕,只要有个娃!“万一”我一个,还有后来人。那年我爸想给党做工作,没地,又有娃,日子,肯定哇哇。在乡下,他学着东坡苏,自己种粮养自家(我瞎编的,我爸没力气)。
我哥落地那年,我爸和我妈的日子定是不好过。好在那会我还在“无极”,咱当成亲娘的党常给人”惊喜”。也不知馕格(川语:怎么)一回事,党,突然需要一个懂保险业务,又不怕吃苦的同志(没银子买粮的时侯,谁会怕吃苦?),带队到比较落后的陕西帮忙去开展保险业务。我妈托人让党看上了我爸。“放心吧”,我老爸在他最需要工作的时侯,党让他上山下乡走街串巷(那会的陕西,李世民武则天都死了好多年了,连李自成刘子丹也死了好多年了,从陪都到陕西,不是快饿死,谁去?)。“放心吧”或者让党把心放到肚子里,我爸孤胆英雄不怕蜀道难时定是在心里给党说过这话。不过,那会没我。
大概是一九五一年的年初吧(那年头重庆到陕西没火车)?。我爸领十几个人,带七八个算盘,“船”武汉,跨河南,中间还经很多地,历尽艰辛,到了陕西省三原县为党开创保险业务(那会发达的地方不需要保险,而穷得连饭都吃不上的陕西小县却需要尝“保险”)。新社会嘛,和旧社会就是不一样。听我老爸说:那会的三原,穷!坐马车,走泥路,吃包谷,喝面汤。我到现在也没去过三原,不明白,那么穷的地方,那么穷的人,党到底为啥要给那的穷人送保险?收不收钱?谁交钱?反正人民翻身有了党,党也不正常。话又说回来,要不是党给穷苦百姓送保险,我爸没准就饿死了,我也不用来这世上瀟洒。
我爸从重庆到陕西三原县的时侯,为了完成好党交给的任务,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以为党要他经常给齐整整静悄悄的边远人们讲课或者做报告,所以带了好多漂亮西装,好些瀟洒皮鞋,大概也想能在穷苦三原漂亮行,瀟洒走,虽说上了些岁数,没准碰上MM。结果,结果现实总离“人想”远(“央视”无敌:人的思想),三原没人请他上课,只是县剧团每次要演资本家,地主,坏人,就找我爸借行头。我爸那会是不是要求进步的中年,我不知道,县剧团的“老借”差点没把我爸给气死。我爸一生气,西装,统统剪了做鞋,皮鞋,一侓扔了喂狗(狗都不吃)。要是那会我爸把他的漂亮行头都留下,我日后定是比人说的“风流倜傥”还更衣冠楚楚。我爸没给我仔细讲过他一个人在三原的 “望星空”,我妈那会在重庆给党打工。到了一九五二年,我妈才离开大重庆,去了小三原,和我爸鹊桥相会久别重聚,把我姐生在那风吹草低啥不见的穷地方。
岁月那会也不知是不是如梭,有了爱,日子就走得快。
一九五六了。那一年,听比党小两岁的我妈说:是解放后最好的一年:鸡蛋,两分一个。“蛋年”,我爸妈到了“月下红袖香”的西安,我就出生在那一年。我爸那会在一个中专教 什么,好像是打算盘,但我爸酷爱的是“飞流直下三千里”。一般言,一男一女有了一儿一女,就不会再生孩子了。但我爸在他走进“知天命”前高兴,和我妈生了我。男人真怪,腥风血雨艰苦卓绝时爱生,比如,毛主席在长征路上。老人家还有语录:长征,是播种机。春风得意踌躇满志时,也爱生。我爸平生好像生过八个,我是老八。不过,我爸不识数(说过了,我爸算盘打得极好,只是我的数学太好)。我爸和毛主席有同样爱好,但我爸的诗里好像从来不用数,不像毛主席,压根可能就不知道地球直径有多大,有了直径怎么算周长?就敢写:“坐地日行八万里”。人的伟大,就是不管,啥都敢。
日月慢慢地还是快快地荏苒到了 饿死人的“三年”完,又三四年,我上了小学。大约在我小学二年级,有次我把我们班上的一位飘亮小MM的脑袋打破,那小MM和黛玉一个姓,也有点黛玉风采。老师告到我家。那次,我爸把我打得认识了我爸。人小,力气小,胆子就小,我那会怕我爸就像老鼠怕猫。
五十年代末,时代大大进步,神州大大跃进,我爸教的中专,变大学了。我爸凭他写的诗,和院长成了诗友,我爸开始教了大学汉语(想想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咱中国的太阳还是那个太阳,咱稀里却哗啦,咱中国的大学更大更全名子更吓人,多少“清一色” 多少“一条龙” 多少“十三不靠),大学长得和麦子一样,当然和现在“全民博士”还差点意思。
按说,我爸是读书人,但教育孩子,我爸坚信:“黄金棍下出好人”(在甲骨文里,或是在“尔雅”里,这“教”还真就是我爸理解的那意思,一点都没错)。我爸最让我伤心难忘至今或是给我的心里种下颗“仇恨”的种子的一件事就是把我在我们全家屬院里很自豪的蛐蛐大将,蛐蛐二将,蛐蛐三将全都用刚开的水,统统活活烫死。我那年好像才十岁,我“孟姜女哭长城”,从太阳出哭到月亮升,想不清亲生的爸咋就这么狠?
我爸有俩儿子。老爸打我要比打我哥少多了,不知是不是我爸那会对我有些什么想法。当然,我哥和我挨打时的作派也不同,我哥是“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砍头只当风吹帽”,而我则“不管是上级的姓名还是下级的姓名“,只要老爸要,统给,绝不高喊:“共产党万岁”。我儿童时代的这些“王连举”的行为,给我自己保住了日后还算能用的脑子。但长大之后,死倔,不爱低头,多吃了些苦,还爱说:人生难得二百五。
文化革命前,我们家有好多好多书。“六六六”(文革大幕正式拉开,该是一九六六六月一日),文革卷席,红卫兵造反,挨我爸打最多的上初三的我哥就扎着武装带戴着红袖套领着一帮人到我家把我爸看得跟命差不多的书,拿出去统统烧了,埋了。我爸昏死(他怎么也想不着毛主席会闹文革,要是他能知道,早该把我哥当个菩萨供着呀),没辙(晚了)。我,那晚躲在门后瞪小眼,羡慕我哥,佩服我哥,那的我哥,牛人也。按咱祖宗的传统:爸,几乎就是皇上的同意词。我哥,听毛主席的话:敢把皇帝拉下马(不过我哥,把“皇帝拉下马”后也就算了)。好像从那以后,我哥就没跟我爸打照面(闹革命,脑袋别在裤腰代上,从延安走到北京喊声毛主席万岁回来就上山下乡,偷鸡,摸狗,扒火车,搞偷盗,背艾思奇,学辩证法,和张铁生一年考大学。没曾想,还考一全县第一。谁不想改邪归正?谁不想穿着四个包包的干部服走路?我哥在农村的黑房里等了快两个月,也没等到大学的入学通知书。他,寒冻腊月,穿个衬衫,拿本红宝书,顶着鹅毛雪,唱着什么歌,回到了家。人,“精神”了,还能记得家门?那会,我中学还没毕业。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给过我不知多少清规戒律。比如: 吃饭时两手必须放在桌子上;吃饭时不要讲话;大人不来就不能自己先吃;不能玩洋片,不能玩弹球,不能玩三角,不能斗窸蟀,写字要工整,念书要认真。成天给我子曰:“学而时习之”,要我天天 “逆水行舟”。老人家好像不知道一个喘着气的活小孩成天想啥?我没我哥刚猛,算个听话的孩子,所以天天也习点“之”,行点舟,念点书,背点诗。
我爸就两个儿子,一个是他心情最不好生活最不好时生的,和他“水火不容”;另一个是在他心情最好生活最好时生的,和他“水油不溶”。也许,我爸也会难受。小孩其实都是你对他好,他就对你好。我老觉得我爸很难理解的,或许,经过民国总统若干,国民总统几个,共党主席一个,换脑变脑洗脑,人爱,没剩多少。
在我很小的时侯,我爸老要我得好好练字,成天说“字是打门锤”,要我练好字,长大好打门。在他高兴的日子里,常常给我每天写的毛笔字上画红圈,写得好就“口头表楊“,胡乱讲评,诲人不倦,误己子第(后来我长大才知道他不懂书法)。当爸的,对儿子 “不懂装懂,小懂装大懂”很常见吧?
我爸做事极其认真,甚至有些过分地认真,对我有没影响,我不知道,但谁拿说不清的遗传也没办法。其实,人生最难的事,就是怎样认真?认真到哪?现代社会,特别是在“成天都得讲闹不懂也不信的话的国家”。太认真(虽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最讲,但他认真了吗?),咋混?
我当过三年工人,为我认为的正义,曾用毛主席的语录去和工厂党支书“认真”,党支书昏死,根本无话可说。但党大腿放倒个把小胳膊,也不费多大功夫。“高帽一戴,小鞋一穿”我就成了“哪里最艰苦就去哪里”的“好同志”了,还被任命为民兵排长,本职工作是:打铁兼敲铁皮。好在读过点“砍头不要紧”,一顿饭能吃水饺一斤半。吹归吹,闹归闹,每天打铁“具体得很”,幸亏还有点其它枪法笔法棋法排球法乒乓法,总厂今天让我去文章,明天调我去乒乓,后天叫我去比棋,再后天送我去学习。我也没真吃多少苦。打住意识流,接着怀念我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