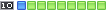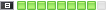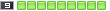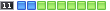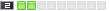我老了!真的老了!
有此感觉和心境,是在这次回到北京时萌生的。
三年没有回到北京,自然要和“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一起下过乡”的老同学、老朋友、老战友聚聚。当年书生意气、风华正茂的我们已经两鬓飞霜,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情已经不再,激情燃烧的岁月已成遥远的回忆,真正到了花舞秋风、荷立斜阳的暮秋时节。
我们这批人都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走上社会的,学的都是外语专业,毕业后绝大多数留在北京,在外交外贸外事部门工作,或者常驻国外使领馆,或者跟随专家组长期在非洲、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老挝、柬埔寨援外。都说世界很大,可有时候显得很小,那些年漂流海外,常常是他乡遇故知,甭管是男是女,激动得又是握手,又是熊抱。那时我们朝气蓬勃,激情洋溢,可是现在,我环顾四座,哈哈,多数已经当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W是我们当年公认的帅哥,文艺宣传队长,来自齐鲁,有着一副天然的好嗓子,每次文艺活动,他的“定计”必定是晚会的压轴戏,一句“溯风吹,林涛吼”字正腔圆,赢得满堂喝彩。退休前是驻某国公使。而今成了家庭“煮妇”,天天演奏锅碗瓢盘交响乐。
Z是我们当年的校花,来自西子湖畔,一双美丽的大眼睛,一对深深的大酒窝,窈窕的身材,靓丽的相貌,曾经把哥们迷倒一大片。退休前是驻某国使馆文化参赞。而今,哎,发福啦,天天在街道的老年秧歌队健身。
Y是我们当年排球队的台柱子,壮得像头牛,退休前是人民日报驻法国首席记者。当年到单位报到时,因为他的名字是女名,恰好和另一个一起分来的女孩儿名字一样,于是管理部门把他俩安排在一个集体宿舍。他进去一看,见里面有个女同胞,以为走错了门,可门上的标签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写的是他俩的名字。他乐了:嗨,这单位不错,不但分房子,连对象也给分配了!如今,哎,成了干巴老头。
H是我们公认的笑星,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说得一口好相声。以往每次聚会都会听到他最时髦的段子。这次没有来,一问去年已作古人。原因是长期在非洲援外时得了肝病。我不由得一阵默然无语。
至于我,再也没有人叫我“小X”了,阁老成了我的称谓。
这次回到原单位办退休手续(原来是内退),人劳处的小年轻对我说:阁老您的关系已经转到老干部处,一切活动由他们安排。到老干部处,小年轻说,阁老听说您喜欢字画,您就参加老年书画班的活动吧。
和文学艺术界、书画界的老少朋友们聚会,同龄人称我阁老,稍年轻一点的叫我前辈,再年轻一点的居然叫我老爷子!上楼下楼、坐电梯,有晚生一边扶着我一边说:您老慢点儿,慢点儿!说话时怕我听不见,声音还提高八度。
打出租车,上车时司机说,老人家,您慢点儿,坐好啰。下车时司机说,老人家别拉了东西。
挤公交车,刚上车,售票员就嚷开了:哪位师傅给这位老师傅让个座!谢谢啦!老师傅,您请坐!
坐火车,乘务员说您老脚抬高点儿,别绊着,然后把我引到座上。
坐飞机,办票时,服务员说,您老人家挨着通道,进出方便点儿。
上街溜达,外地来的民工拦住我:老大爷,往西便门怎么走?
上饭店吃饭,有小姐引到专门为老年人预备的老年优先桌。
逛书店,服务员给我推荐《老年保健秘诀》。
你瞧瞧,这走哪儿已经离不开一个老字。
我开始享受老年待遇了。
我真的就老了么?真的能被称为老爷子了么?我有点愤愤然。
不是摆虎,别看我年在花甲,可吃得比小年轻还多,走得比小年轻还快,登山决不拉在他们后头,游泳我还能蝶泳,在草地上还能翻跟斗,怎么就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了呢?
我站在镜子前面,对面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头,耳聋眼花,牙齿缺仨,一脸的褶子,一脑门子的车道沟,还吊着两个大眼袋。那就是我,那就是我啊!
老了!确实老了!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
可以不服气,可以不服输,但不能不服老。
老了,下一步该怎么办?我开始考虑这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这道理我明白。但是朝霞以后是丽日中天,而晚霞以后是冷月星空,不同啊!
“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这话倒合我意。
我想,人都有两个年龄: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生理年龄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犹如花开花落,云聚云散。可是心理年龄,可以自己把握。那么在今后的日子里,应该以尽量年轻的心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比如写字、码字、为自己立传、为他人写真------
人可以老,但心不能老。如果心老了,那才真正是老了。
此见不知朋友们以为然否?
[em39][em39][em39][em39][em39][em39][em39][em39][em39][em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