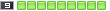暖水瓶
甲午初春,经朋友介绍,我到云雾县一个曾经著名的工厂去打工。上任前工厂的上级大领导向我交代任务明确责任:负责文字工作,主要是打造工厂文化。我想自己虽才疏学浅,但凭着自己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好学的精神是能胜任的。
在一个满天飘散着雾霾的上午,搭便车去单位报到。车行驶在一条刚刚通车的高速路上。道路上因过往车辆较少,路显得格外宽。我透过车窗随着一会儿见浓一会儿见淡的雾欣赏着疯跑的景色。虽然还看不到山上的绿色,但一株株的杏树已经一串串的开满了花。偶尔那些早绽放的花朵已筋疲力尽,没有了精神气儿,散落的花瓣无精打采的落在车的前窗上,好像要对车的主人诉说自己的不幸似的。可是车的主人没有在意,也许是主人集中精力在路况上,也许是主人不在意自己兴趣之外的东西。我生起了怜悯之心,以示同情吧,自言自语到:初春早探头,自己弄风流。不见游人赏,繁花在后头。
下了高速,路况就越来越差了。路面窄还不用说,路面还坑坑洼洼的,弯道还挺多。过了近一个小时,车子停在一块较平坦的场地上。我下车一看,好家伙,这里的地势很奇特,在一处高高的山脊上有一排房子,在紧挨房子的前边硬载上了一排松树,房子里的人出入需要侧身弯腰从松杈的缝隙里过往。在停车场的北侧也有一排房子临悬崖而建。这里其实最引人注目的是进入工厂的大牌楼上的一副对联,木板材质,彩喷大字,长有丈余,上联是:此处我为大,下联是:安全最可怕。我很疑惑,这么一个很负盛名的工厂,咋有这么一幅联呢?
单位的老员工帮我安排了宿舍,我开始收拾床铺,床上用品整理好后,我刚坐在床上,呱嗒一声,床板落在地上,床散了架子,我重重的摔在地上。我又重新整理,做了些加固,后来的日子里床铺虽然没散架,但嘎吱吱的音乐伴奏了一个春天。
初来乍到,人不认识,说话不随便,地况不熟悉,不能随便转。只好到办公室慢慢熟悉自己的业务去吧。办公室空间很宽大,尤其是顶子很高,靠南墙有两个文件橱,厨子里的文件盒子歪七扭八睡着,对面笑的两张办公桌上布满了尘土。东南角里放着一台电脑和传真机,电脑也没网。左右两面墙上是悬挂的用电脑激光打印的挂板,是单位的规章制度和领导分工,字数虽然不多,但白字不少,从挂板的颜色上看,已有些年头了。我翻看了一下考勤薄,除分工的主要领导之外,薄上原来的一些不关紧要的领导早回家抱孩子去了。门的两侧放着七八个暖水瓶,这些暖水瓶可不是一般的暖水瓶,它会暖出很多故事来的。
这个单位有个亮点,这里的领导的职务名称很有意思,主要领导叫“统、副统”主任级别的叫“厂卿”,听说给我安排的职务叫“副卿”,后来这单位的员工们见面叫我“刘副卿”,我窃喜,看来我到美国就是国务卿了。当时我的心情那正是:从未当大官,今在总统边。可怜无三军,眼前仅是山。
在三两天里,人们都到单位报到了。蛰伏一冬的工厂开始复苏了。我在办公室里上班,开始整理文字资料。我有一个搭档,是这里的老人,比我年长两岁,中等个,留着分头,白净脸尖下颌,说话轻声慢气,走路轻健如猫。他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早点名,晚签到。平时没事在电脑上弄这个球儿滚来滚去,乐此不疲。这里的文字材料不多,有的大部分多是电脑下载的,十几年都是用的一套词。我第一步,写出一个《工厂产品概览》,把这里的十大产品,四字一句,用韵文的形式共二十八句一百一十二字囊括清楚,做到了朗朗上口。这是一篇我从事写作以来自认为最得意的文字。当我满怀希望拿给统和副统看的时候,我的心一下子被储存在冰箱里了。
我走进“副统”的办公室,我把打印好的《工厂产品概览》递到副统手里。文章在副统手里停留的没有三十秒,连声说“好,好”。就递给了我。我心里感觉“好好”的含金量太低。也难怪听说这位副统是小学文化程度。我走进另一位“副统”的办公室,结果也是不到一分钟就结束了战斗。我想在抗日战争时期,要能多打些这样的歼灭战多好啊,何必八年抗战呢。后来我想副统潦草些,可能是“副”字在作怪,你看“副”字这个造像,多不容易啊,总得拿着一把刀,才能守住自己的一口田。一天,我走进了“统”的办公室,打算让“统”
看看我写的东西。因为“统”十天半个月的不在单位,碰到他也很不容易,逮住机会就不要放过吧。当时我认为一定会得到“统”的肯定,会给个亮帽顶子戴一戴。您看“统”的造像多好,一边有根绳索,为官又能充个大个,说捆就捆,说绑就绑,可充军,可发配,呼扇大了去了。“统”虽年过六十,但脸膛红润,没有胡须,穿一身红色西服,随身听的耳机总在两只耳朵里塞着。手里一只纯银水杯,雕龙画凤极为精致。我走到身边,把材料要递给他,他没言语,冲着桌子努了一下嘴,示意让我把东西放在桌子上,这时我听到从耳机里挤出来的几句梆子唱腔“这小刁一点面子都不讲”,我走出办公室,轻轻掩上门,怕打扰了下面阿庆嫂的“这草包道是一堵挡风的墙”的那清脆的调子。一直到我离开那个单位,也没见“统”给个说法。那正是:弄文不值钱,权利沉甸甸。
我主动的做了些文字工作,计划,我制定的详详细细;总结,我做的全全面面;档案,我搞的整整齐齐。领导也从没交代我做什么文字,我的工作一直很清闲。下班以后我就看看报,练练字,我的搭档没完没了的在电脑上滚那个球。我突然发现“统”们对我总没有对我的搭档热情,表情总是怪怪的,我心里有点纳闷儿,后来我终于找到开锁的钥匙,原来是办公室里的暖水瓶起的作用。
八只暖水瓶上标着数字,四个“一号”,四个“二号”。我的搭档有个习惯,不滚球了,就站在窗前往外看,办公室在高处,下面人来人往看的一清二楚,有时拎起四个一号,有时拎起四个二号,矫健的到水房打水,时间不长就把暖壶拎回来了,当我提起暖水瓶时,可总是空的,怪了,水呢?初来咋到的我也不好探秘,过了一段时间,我仔细留意,注意观察,原来如此啊!我在窗前往下看,搭档手拎灌满水的四个一号,走进“统”的办公室,不足十分钟的时间,他又拎着四个一号回到我们办公室。这才是“有来无回”啊,实际上是八个一号暖水瓶,八个二号暖水瓶。他在窗前看的是领导来不来啊,领导来了,他熟练的完成打水---送水---沏茶---换瓶,一套程序完成的那么熟练,完成的那么自然。有一次我见“统”晚上喝高了,统坐在宝马车的驾驶室里,半开着车门,向外呕吐不止,我的搭档拎着一只暖水瓶,端着一杯水小心的侍奉着,原本比“统”年长几岁的他,却“您老,您老”的叫着,我浑身在起着鸡皮疙瘩。我们几个副卿把统驾到统的卧室了,安顿他睡下,反身去收拾被吐得狼藉的车子,这时大领导不在了,我的搭档早又滚球去了。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的过着。
这是一个只有正式职工不足二十人,雇佣工七八十人的单位,等级还很森严。开会时领导前排就坐,就餐“统”居正席。“副统”们架子也很大,平时下级汇报工作,员工反映情况,眼皮都不撩一下,无形中领导和群众就产生了距离,领导就像瞎子一样,厂子里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有一天中午社会上一些人到厂子里闹事,大打出手,领导吓的变毛变色,往日的威严没有了,员工们却没有一人挺身而出站出来解围。我不知深浅,把闹事的几个人礼让到办公室里,看来我几年的法律教学经历在此时也发挥了一点点作用,从法律角度晓知厉害,几个人愤怒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多了些理智。说准确一点,不是法律起了作用,而是在你来我往的谈话中发现有两位是我教过的学生的家长,从私人角度给了我面子。他们走了,事态算平息了。“统”们走出了办公室,胆子又壮了起来,七个不在乎,八个不轮力。看热闹的员工面露惋惜之态,好像少了一种什么刺激似的。
上半年厂子里继续亏损,工资也没及时发放。有一天夜里我做梦接到一个通知,说让我到一个世外桃源听陶渊明讲课,我愣梦游背着行李步行百十里回到了能当二把手的家。梦醒后,感觉到家里的天是那样的蓝,家里的地是那么的平,家里的空气那么纯,家里的人那么真。那正是:云雾连天不见天,文人弄笔太寒酸。庙小妖风能掀浪,暖水瓶里可行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