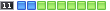贵阳是我住过生活过的五个城市中呆得最久的地方了。整个的青少年,整个的人生拐点都是在这里完成的。按理说这座城市应该是承载了我最多的故事,最多的悲欢离合,最多的感慨,是我最应该留恋的地方了,但很遗憾,它并不是。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我从北京到贵阳的那一天开始,就天天等待着离开了;等我真的离开,就从来没有想过再走回去。(当然我还是经常回去看望亲戚朋友的,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在远离它的日子里,它从来不会让我惆怅,从来不会给我乡愁。不过让我奇怪的是,在贵阳人夏小焉(她也应该算是新浪的名博了吧)的博文中,每每读到她有意无意提到的那些我熟悉的地名,一种莫名的温温的暖流就会在我的血管里冲撞,好像春天冰河里涌动的冰块……。自己都觉得纳闷,好像只有在别人的记忆里,贵阳才能与我相会,而且还有点温情脉脉,想起来就觉得这很暧昧很诡异。
今年,我又一次去贵阳的时候,闲得无聊,挑了一个雨天,打把雨伞毫无目的地走上大街。(贵阳多雨,阴雨绵绵是她的符号,阳光明媚,那便不是贵阳了)如今交通方便,几乎人人有车,出租车公交车满街跑,一般人上哪都不会再走着去了,但我偏偏想走路。从观水路走到大十字是我十四岁时每天必走的路程,如今我可还能走得动?甲秀楼,西湖路,大南门,中华南路,位置没变街名依旧,没有了熟悉的建筑又何妨?我沿着记忆中的方向顺着街道朝大十字走去。说巧就是巧。就在快到大十字的地方,确切的说在达德学校门口,(这里过去是南明区文化馆,到贵阳后的最初几年我在这里度过不少时光)我遇见了一位四十年没见的老朋友。
其实一开始我们谁也没认出谁,当然不可能认出来!四十年是什么概念?四十年前我们是什么样?她十九,我十七!而此时,岁月已把我们的脸扩张了一倍,身躯扩张了一倍,身高缩小了两公分,还在我们的脸上横竖八叉不客气地刻上了皱纹。在雨中,我撑着伞,站在达德学校门口,被唯一的,还有一点点过去痕迹的,如今挂着达德戏馆牌子的建筑吸引。那些睡了过去的记忆,我以为早已忘记的往事,这一分钟不管不顾地脑子里开始回放。离我不远处,我注意到也有一位妇人,和我一样凝神望着眼前的达德戏馆。我侧目朝她望去,见她头发挽成一个发髻高高地盘在头上,对襟衣,高高的领子,很古典,而且让我一惊的是她也正望着我。眉宇间有一丝我似曾熟悉的影子,怎么这么眼熟,她是谁?还没等我再看她一眼,她却已经走到我面前。不好意思打搅一下,你可姓高?她问我。哦,我是呵,你是……?我是夏小宁啊。她的话音一落,眼前这人的样子一下子就清晰起来,瞬间,时间堆在她脸上的赘肉皱纹就退了下去,隔着四十年的岁月我看见了十九岁的她!惊喜之余我们并没有拥抱,甚至连手也没拉一下,说实话我和她都有点不知所措,有那么一会儿我们就那么愣着,什么也说不出……。你说,这,这,这地方哪还有以前的影子啊,我结结巴巴地说。
唉,她终于叹了一口气。这么多年,这么多年你都跑哪去了?!
我们找了一家半岛咖啡坐了下来。结果,事实上,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沉默。咖啡很难喝,空气很污浊,我们好像谁都找不到话说。当然,都结婚了,有孩子了,她的是儿子,我的是女儿。她的儿子都结婚了,但还没有孙子,我的女儿准备不结婚当然也不会有孙子;然后呢,还说什么?还能说什么?我们俩都显得无比尴尬,没话找话都找不出来,你说还能不尴尬!可是四十年前我们无话不说,常常聊天通宵达旦。夏小宁争着要付钱,我争不过她,随了她的意。四十年前,我也是争不过她,但不知道那一回可真的随了她的意?
那时候我还在一个区属的棉织厂当一名挡车工。好像是在一九七一年底吧,区工业局要搞一个什么庆祝湘黔铁路胜利开通的汇演,我和夏小宁都是临时被抽出来的“创作人员”。我编舞,她写歌词。我们歌舞组的负责老师姓孙,性别,女,他们音乐组的老师姓姜,性别男。他们编得曲子铿锵有力,节奏明快,歌词无非就是什么清水江欢歌,湘江浪,黔山湘水换新貌之类的;我们呢,舞蹈动作当然也就是迈大步,抡大锤,把推鸡公车的动作扭成秧歌。典型的红歌红舞。只要你看过那个舞蹈史诗《东方红》,你就知道,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舞蹈都是那个味儿,就像如今的春晚,几十年不都是一个范儿?不过话说回来,他们的姜老师,我们的孙老师,那倒都是很有才华的文艺青年,要是放到今天,他们没准都成大腕了。现在想起来孙老师那时最多也就是二十五六岁,姜老师嘛,可能大一点,但也不会超过三十岁。可在当时我的眼里,他们简直就是未来世界,渊博,深刻,简直就是深不可测。
孙老师除了会跳白毛女,沂蒙颂,我偷偷地看她跳过天鹅湖里那段四人舞,自然也跳得超级棒。她身段柔软,有表现力,跳过很多独舞,我们都很崇拜她。她好像还是个单身,而且没有男朋友。那位姜老师呢,更别说了,虽然他戴副眼镜文质彬彬不是那个年代流行的革命形象,但他出口成章,一口气写一段快板,外加报幕词跟玩似的,不费吹灰之力。关键是他特别幽默,一说话就把我们这些女孩子笑得前仰后合。他结婚了,还有一个几个月大的女儿。孙老师和姜老师关系好像不错,常看见他们一块聊天。而且孙老师好像和他老婆也认识。
那时我十七岁,有一副煞有介事的老成外表,浑身都是北京孩子的臭毛病,自以为是,喜欢对国家大事夸夸其谈,好像政治局开会我都列席了似的,动不动就分析国际形势。其实呢,现实生活中我连自己的衣服都不会洗,连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都不知道。无论对孙还是姜,只要是成年人,我都是仰视的,他们的世界对我来说很陌生很遥远很深奥。不知是不是因为,按他们说的,我很单纯,(有一次我偷听见他们这样评价我,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们说的单纯有一点贬义,好像和傻乎乎的意思有点像,对这一点我那时还拿不准)孙老师对我很不错。比如说我编的舞蹈动作她都认可,我出的点子,她一般都说好,这些在我看来都没有什么,最重要的是我觉出她对我不一般。因为她请我去了她的宿舍,给我看过她小时候的照片。这我才知道她以前参加过省体操队,参加过很多比赛,难怪她身体那么柔软。我由衷地赞美她,心里佩服的不行了。那一年过春节,她说她回不了家了,问我可不可以陪她过年。那时我正逢青春叛逆期,每天都盼着逃离家的管束,能有这样一个借口不在家过年,真把我美死了,我当然一口答应。
不过那个年过的可谓是乏善可陈,孙老师既没有找人来凑热闹,也没有带我出去玩。她随便做了两个菜,(俏俏说一句)手艺一般,看来孙老师也并不怎么会做菜。想着家里这会儿肯定是一屋的人,一桌的菜,心里有点酸酸的。但是一想到自己是自愿要来陪孤单的孙老师,马上一股悲壮之情油然而生,自己被自己感动着。孙老师好像心情不怎么好,话很少,只是有一句没一句地东问西问的,没有重点。好在她有一部手摇的唱机,有那么两三盘唱片,其中一盘居然就是天鹅湖。虽然唱机已经太旧了,唱起来咿咿呀呀哼哼唧唧,但总比没有强。她的房间很小,床是唯一可以坐着比较舒服的地方,我们俩就这样蜷在床上,听着唱机哼哼。管他呢,总比没有强,起码在那个年代我就囫囵吞枣地听完了天鹅湖全场,听说了柴克夫斯基。唯一让我觉得有点奇怪的就是吃完饭后姜老师来坐了一下,没说几句话就要走,孙老师把他送出去了,把我一人撂下听唱机哼哼。半天她才回来,神情幽幽的,但我哪里懂得问,一觉就睡过去了。从此我自以为和孙老师关系不一般了。
夏小宁好像和他们姜老师也不错,常看见他们坐在一起“交头接耳”,当然那是他们在切磋,一首歌词的问世毕竟不是像呼吸那么简单。夏小宁和我就简单多了,没事嘻嘻哈哈,有事稀里哗啦。虽然她只比我大两岁,十九,但她俨然已经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家闺秀”,我老是这样悄悄取笑她,因为那时这可不是个正面词汇,比地富反坏右是稍微强点,但也是和资产阶级小姐是一样的意思,算是骂人的话了。她倒是没有为此恼我。夏小宁非常清瘦,细细的像根筷子,脖子很长,平时老是穿着一件对襟棉衣罩衫,耦合色的,我记得很清楚,还老是围着一条象牙色的围巾。说实话在那个文革时期,别人也都这么穿,但不知为什么她穿出来就是不一样。我老说她有点像家春秋里的梅表姐,她说梅表姐命不好,你可别咒我。我说那就说你像林黛玉,她说那就更不好了,我说可是你的确不像红卫兵不像工农兵啊,要不说你像林道静吧……,就这样和她闹起来总没个完。
有一天她很神秘地对我说想给我看一样东西。排练完以后她就把我拉到排练厅的后面(就是现在的那个“达德戏馆”)从她的包里掏出一个小本子递给我。咖啡色,非常精致,说不出哪与众不同,反正肯定没有毛主席头像和语录,反正在当时商店里买不到。我打开,第一页是一首小诗,好像是两段,每段四行。我完全记不得写的是什么,只记得肯定不是革命诗。谁抄的,不像是你的字啊?谁的诗,普希金?(那是因为我只是道听途说过这个洋气的名字)我只顾翻,一页一页地翻,完全没注意夏小宁眼里闪动的羞涩。那时我除了革命诗抄几乎没读过什么诗,我的笔记本里唯一抄的诗就是闻捷的那首《我思念北京》,那还是我悄悄从我姐那偷来的,因为一看到那开头“我殷切地思念北京, 像白云眷恋着山岫,清泉向往海洋, 游子梦中依偎在慈母的膝下……”我的眼泪哗地就下来了。但是,当然,我当时的理解力只到那,比如眼下夏小宁给我看的诗,我就无动于衷。我翻到第六页就没有了,怎么就这么几页?我问,夏小宁一把把本子夺了过去,算了。不跟你说了,你根本不懂!我怎么不懂了?我也急了,你还没好好让我看呢!但夏小宁理也不理我,把本子揣进包里,走了。
这事发生了,过了我就忘了。随后就是每天忙着排练演出。我们自排自演的组歌《湘黔战歌》在汇演中获得了一致好评。本来汇演一结束我们就该回厂了,可没想到铁路系统的领导对我们的节目有了想法,他们当中不知哪一位提出希望我们能顺着铁路沿线给战斗在第一线的筑路工人表演表演,再给他们鼓鼓劲。就这样我们又多得了几个月的快乐。在外面演出再苦再累条件再差也是我最幸福的时候。每天东跑西跑说说唱唱蹦蹦跳跳就过去了,多好!我一想到要回到车间去守那些不死不活的纺织机,我就郁闷。夏小宁说她也不想回厂,虽然她的工作是绣花,乏味指数比我略低,但她说她也不喜欢回去。
到外地演出,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就更多了。夏小宁还是忍不住又一次把她那个宝贝本子拿给我看。这一次我可不敢那么冒失,仔细地从头再看一遍。我发现后面又多写了好几页。有一首诗引起了我注意,“我愿做你颈间的白围巾”,哦,我惊叫起来,这是写给你的诗!我像是发现了新大陆。这我才注意到夏小宁脸上那几分羞涩几分甜蜜的表情。谁,谁,我追问。我向毛主席保证给你保密,快告诉我!她摇摇头,根本不想说。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她的表情有那么一点凄凉。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这个本子。后来,演出任务完了以后,我们就都回厂了。
回到工厂的日子自然没什么好说的,如同死水一般。每天都盼着能发生点什么,随便什么都行,惟恐天下不乱。(所以我就特别理解为什么富士康的工人爱闹事,那是给乏味憋的。)结果不知是不是因为我天天念叨,那天真的发生了一件我绝对没想到的事。姜老师到工厂找我来了,而且竟然是那样一个场景!
那天厂门口值班的师傅跑进车间告诉我有个男的找我,我大惊失色。倒不是什么别的,只是因为我那时除了我爸我哥,我以为不会有任何男性会来找我。但是如果来人真是我爸或者我哥,那一定是出大事了。我惴惴不安地跑到门口,连围裙帽子都没摘。姜老师好像没认出我,等我把帽子摘了,让两条大辫子重新挂在耳朵旁边,他才连忙说,哦,高明明,是你是你啊。我叫了一声姜老师,我想我肯定就是瞪着一双询问的眼睛看着他,肯定什么都不会问。那天也是下着雨,雨不大,姜老师没有打伞,雨水把他头发都淋湿了,有一缕头发掉下来贴在他的前额上,落魄得让人心痛。就在那一次我第一次发现原来人是可以有许多面孔的。我,我,我,姜老师脸憋得通红,但一会儿又变成惨白。出了什么事吗?我有点慌了。
你听我说,姜老师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平时潇洒幽默满不在乎的劲儿全部消失殆尽。你能不能,帮我去找找夏小宁,……夏小宁?!对,帮我找找她。请你转告她,请她无论如何不能把我给她的本子交出去……,本子?交出去?我脑子飞快的转了起来,难道是……?你知道吗,如果她把本子交出去,我就完了,妻离子散都不说,我可能还会被判刑,而且,我还有一个老母亲啊,说着,姜老师泪如雨下……。我完全傻了,不知如何应对。我说姜老师姜老师,你别急,你先说,是什么本子,小青她知道有这么重要吗?你需要我怎么说?你想让小青怎么办?……我一定去找她,立刻就去,好吗?那一刻我甚至都想抱抱他,对他说,别急别急,会好的会好的。
回到车间我就去跟班长请了假,摘了围裙帽子就开始跑。好像接受了一项什么革命任务,好像去救什么人,生怕我去晚了,夏小宁不知轻重已经把本子交了。可是到底是什么本子,姜老师写了什么会让他坐牢,我却一点也想不明白。 我先找到夏小宁的工厂,可她的工友说她今天请了假没来,我赶快又往她家跑。还好她在家,我气喘吁吁地还没坐定,她就问,是不是姜老师找过你?她脸色有些苍白,眼睛肿肿的好像哭过。我不知该怎样回答,愣愣地看着她。
我告诉你,你什么都别说,说也白说……,好好,我不说我不说,我被小青的脸色吓住了。那个姜X X是个胆小鬼,是个懦夫……!她咬牙切齿直呼其名,我一下子好像看到了姜老师被揪斗的样子。小青小青,你听我说,那一刻我觉得我无论如何必须把本子的事说出来,那个本子,本子,你知道吗,千万藏好,不然姜老师要被抓的,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说完我就瘫了,但心里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好歹我算是把话带到了。可是没想到我话音一落,小青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我不知所措,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只好傻呆呆地陪着掉眼泪。虽然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哭,但我知道她心里很难受。也不知过了多久,夏小宁平静了下来,她帮我抹抹眼泪,说你掉哪门子的眼泪啊,回去吧,我知道了,你千万不要把这事跟任何人说,求你了!我连忙点头。你,还有姜老师,我要你们都好好的……。小青的眼泪又流下来了,她推我走,我就走了。
之后再发生的事我就不太清楚了,只是听说姜老师离婚了,后来又结婚离婚又结婚,但是绝对都和夏小宁不沾边。工作上他怎么样我不知道,但至少没听说他被抓。后来我自己的生活开始了,离开工厂,读卫校,上大学,谈恋爱,活得是风起云涌不亦乐乎。贵阳并不大,但我再也没有碰到过他们。后来离开了那里,遇到的机会就更微乎其微了。渐渐的,这件事就成了我记忆卡中的一个独立的文件夹,没有再打开过。
我要离开贵阳的前一天,接到夏小宁的电话,她邀请我去她家做客。
你还记得当年你为姜X X专门来找过我吗?当然记得,我脱口而出。世界上就有这样的事,如果不提,你永远不会自动想起,但一旦点到,历历在目。
你还记得我曾经给你看过的那个本子吗?当然记得,但是记不得内容。哦,难道就是那个本子惹的祸?我有点猜到,但那个本子怎么会让姜那么害怕?因为后来他又写了很多露骨的,别人一看就知道是写给我的情诗。那不是重点,重点是他老婆知道了我,知道了那本诗集,而且,她说是你告诉她的。天呐?我连他老婆都没见过!小青很犹疑地看了我一眼。你怀疑我了?你知道,第一我没见过他老婆,第二,那时我也并不知道那是姜老师的本子啊,我怎么会……?我知道我知道,其实我并没有怎么信,但姜就被吓坏了,他问我是不是给你看过,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人知道!他来找我,求我把本子还给他,求我把诗全烧了……,你知道他那副失神落魄的样子,现在想起来都叫我恶心!我当时气极了,对他说,你那些破诗都写什么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了,还是下流淫秽了?最多就是不够革命。你写给我的,我都没怕,你怕什么!夏小宁如今说起来像是漫不经心,似笑非笑,可我看出来了,即使过了四十年这事还是没让她释怀。
他害怕,所以他又去找你。人家姜老师现在可是名人了,电视上常常露面的。真的假的?我着实很吃惊,脑子里闪过的印象还是多年以前最后一次见到的,脸色苍白,在雨中,雨水把他的头发贴在额头的样子。小青突然笑了起来,要是当年我没有烧掉他那些诗,如今拿出来还不让他名声大噪啊!我也笑了起来,那些诗真的写得很好吗?我不禁问。
你知道,那个孙老师为了姜,终生未嫁。去年死了,才六十五岁!我又一次被惊住了。
孙老师和姜老师是校友,在学校时她就开始爱上了姜老师,但姜却和别人结了婚,这倒也罢了,但后来她看出姜对我有意,她就不干了,她找了姜好几次,骂他是伪君子,以为拒绝她是因为对婚姻忠诚,原来是另有新欢!孙找我聊天,装作很随意地提到姜的妻子孩子什么的,她以为我不知道姜已经结婚的事。我呢,是不知道她的用意。各说各话,谁也没有明白谁。 可是,夏小宁停顿了一下,我一直想知道你是不是跟孙老师提过诗本的事?我,跟孙老师提过?我一下子茫然了。是,那时,有那么一阵和孙老师挺好的,但是,我会吗?我会不会有什么话被她套出来过?我是说不清楚了。也许会,我那时毕竟是个不懂设防的傻丫头。夏小宁笑了笑说,我不是要追究什么,时过境迁,一切都过去了,我只是想女人为了男人,为什么什么损人不利己的事都敢做?!
孙老师不知是怎么就知道了姜老师写了很多的情诗给夏小宁,或许真的是我告诉她夏小宁有一个神秘的小本子,而她以她女人的嗅觉一下子就猜到了作者。她毕竟是单恋了姜老师那么多年的人。接下来她做的事居然是跑到姜的家,告诉姜的老婆。是你,高明明,看到了姜写给夏小清的情诗,这本诗就在夏小宁的手里。姜的老婆是个个性极强的女人,自然眼睛里容不得沙子。如果姜能够坚定地一口否认,也许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他们毕竟才有一个几个月大的女儿。但是心虚的姜,支支吾吾,似是而非,既不说Yes,也不说No。结果可想而知,姜的老婆二话没说,只扔下一句话,法庭上见,抱着女儿就走了。
孙以为搅黄了人家的婚姻,她就能趁虚而入了。结果老姜离婚后,宁愿找了一个没工作的小学都没毕业的半文盲,也不娶孙。再后来,文革结束后,他休了那个半文盲,又娶了一个比他年轻许多,七七级毕业的中文系大学生。无论怎样就没她孙老师的什么事!
那你呢,后来老姜没有找过你?当然找过,只不过再也不是为了写诗的情,而是为了要回那些他害怕作为证据的诗的文字。你还给他了吗?我全烧了,一字未留。
后来我在网上搜索到了姜X X,他果真是社会名流了。除了介绍他的文章,还附有大堆的照片。 在那些图片中再也别想找倒他年轻时的一丝一毫,无论是洒脱幽默,还是苍白落魄。一切都已经好好地掩埋在他恰到好处的,如文章中所形容的“儒雅达观”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