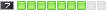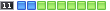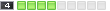当我站到陈家大奶奶面前时,她正拄着木杖站在她门前的老槐树下,眯缝着眼向远处张望。她似乎不是在看我,而是在看远方,远方某处好像有比我更让她好奇的东西。
其实她看到我了。她的目光已经从远处转到我脸上,端详了一会儿,便轻声叫出了我的名字,像叫他的儿子一样叫出了我的小名。
陈家大奶奶从屋里拿出一个大石榴让我品尝,这让我立刻想起了母亲。那年也是在秋天的某个下午,母亲拿出她放了很多天的石榴,站在我身边静静地看我吃。陈家奶奶让我想起了那些远去的时光,这个小小的村子总有许多古老的时光。
我看到她门前的石榴树上正有一片叶子在风中摇摇摆摆飘落到地上,这片叶子似乎很多年前也从我眼前飘落过,但我实在记不清是哪年是哪月了,当叶子摔落到地上的一刹那,我的心疼了一下。
这所院子后面是一片空地,我听到羊的咩咩声从空地上传来,那些声音像陈家奶奶的目光一样让我温暖。
那肯定是陈家奶奶喂养的羊。她的年龄虽然已经让村里最年老的马、最年长的牛相形见绌,但她仍然在放牧几只羊,羊是她生命的一部分。也许在她看来,只要有空地,空地上只要有草,就该有羊,不然空地会寂寞,草也会寂寞。在她心目中,世界有它自己的模样。
两条年幼的狗从门前戏耍着跑过,它们把正在地上专心觅食的两只鸡吓了一跳,其中一只母鸡慌慌张张飞起来,另一只是公鸡,在它后面急匆匆地追,它急着去安慰受惊的情人。
院子外面的高树上,有一只鸟在操弄着不知哪里的方言,说个不停,只说不做的鸟肯定是在虚度光阴。
站在陈家奶奶的院子里,我想,世界的模样应该有两个:一个是空地、草、羊的模式,一个是高楼、水泥路、拥挤的车辆的模式。
很多年前我在城市里的一个大街上看到过一个贵妇人,她姿态优雅,站在古典的马车上向周围的人招手。她年纪很大了,对这样热闹的场面依然留恋有加。她习惯了前呼后拥,习惯了人潮涌动。然而,在繁华中我也看到了她眼里流露出来的疲倦,疲倦的眼神有些空洞。
陈家奶奶眼睛里永远不会有疲倦。在我的记忆里,陈家大奶奶的年纪很老了,我们村里的所有人都该叫她奶奶。
很久之前,每逢下雨,村子里总会一片泥泞,我的车子陷进泥土里的时候,总有人出现在我身后,把我车轮子里的泥巴抠出来。那个人有时是陈家奶奶的儿子,有时不是。
有时是德根叔。他常常悄无声息地拐着一条瘸腿来到我跟前,帮我收拾夹在车轮和车圈之间的泥巴。当我和一瘸一拐的德根叔在泥水混杂的街道里走过陈家奶奶的门前时,我们常常会看到她。她拄着木杖,站在老槐树下,若无其事地望着飘着碎雨的街道。她像一架破旧的摄影机,把我和德根叔,连同街道连同细雨静静装入她永恒的屏幕。所以现在我来到她面前时,她会讲起这些事,我好像在重温一部关于自己的黑白影片。
我经常回到这个村子。我在这里长大,又逃离了它。回到这里,我内心就会踏实。每次回来,我都会去看望陈家奶奶。在她的院子里,我享受着美丽的古老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