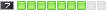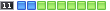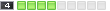昨晚登山,走到后山石深林茂处,忽见一泉自石缝里汩汩而出,在石间草丛流动,流约丈许,遂悄悄钻入另一道石缝。
看来世间万物皆有寂寞,泉也不例外,身居山间多少年,遇不到一个行人,遇到我这个凡夫俗子,也不免羞羞答答,像一尾小蛇,探一下脑袋便急匆匆隐入草丛。
游山见泉,如读古人书而忽见名言佳句,真有无边的惊喜。近来读清人张潮《幽梦影》,大有在月清风霁之宵入得深山老林,偶遇石上清泉之感。张心斋曰:花不可无蝶,山不可无泉,石不可无苔,水不可无藻,乔木不可无藤萝。想必心斋先生在五百年之前的某个晚上,一定与我有相同的月夜艳遇,才有如此的感慨。
《幽梦影》,初看此书名的人会错以为是琼瑶阿姨描摹风花雪月的言情小说,错,它其实没有故事,全书是由一句句格言点缀而成,就像老如来脖子上的那串念珠,粒粒皆晶莹。读过此书你一定会被惊倒,“片花寸草,皆有会心,遥水近山,不遗玄想”,这就像林黛玉在潇湘馆读《牡丹亭》,那才叫惊艳。
心斋先生风流,满脑子风雅颂,“艺花可以邀蝶,累石可以邀云,栽松可以邀风,贮水可以邀萍,筑台可以邀月,种蕉可以邀雨,植柳可以邀蝉”,他一定在他居住的小县实践过,不然何以会有如此想法,他一定也是个失败者,所以只会用“可以”。“可以”者,往往是不可以也。
心斋先生一生著述甚多,但却不是个得意者。他说“愿在木而为樗,愿在草而为蓍,愿在鸟而为鸥,愿在兽而为豸,愿在虫而为蝶,愿在鱼而为鲲。”樗者,不才终其天年;蓍者,前知;鸥,忘机;豸,触邪;蝶,花间栩栩;鲲,逍遥游。心斋先生想长寿如樗树,却只活了五十多岁;想前知如蓍草,却曾被陷入狱,不曾预卜自己的未来;想忘机如海鸥,却深陷官场,身不由己;想正义如豸,却没有谋得显赫官职,替那个黑暗的世界伸张正义;想艳福如蝴蝶,却只能与孔尚任这般老夫子终日在一起耳鬓厮磨;想逍遥如鲲鹏,却置身世俗不能自拔。天底下好事多了去了,他一样也没有占得,只能痴人说梦,一部《幽梦影》貌似闲情逸致,其实是如影似梦。明清文人皆好闲情逸致,写有艳文《肉蒲团》的李渔一部《闲情偶寄》,让他品味高了许多。张宗子《夜航船》文题充满诗意内容实则是百科全书式的的著作被后人膜拜。无论李渔还是张宗子,他们与心斋先生一样皆不是得意者。好在明清那帮哥们有治疗失意的良药,煮字疗饥,著书立说让他们纾解了忧愁烦恼。“目不能识字,其闷尤过于盲,手不能管,其苦更甚于哑”,一管抵千军,这就是古代文人的精神寄托吧。
文人苦闷,不过,他们也会消遣自己。“楼上看山,城头看雪,灯前看月,舟中看霞,月下看美人,另是一番情镜”,所以,文人狎妓,不可当真的,没人知道,他们在风花雪月之后内心深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烦恼。
中国古代文人抑郁苦闷是众所周知的,在心斋先生之前多少年,苦闷的中国文人在长长的文化路上摩肩接踵踉踉跄跄艰难前行。这队伍里有披头散发形容枯槁的屈子,他久久徘徊在汨罗江边,对摇摇欲坠的楚国的爱恨情仇让他再也无力走下去,纵身一跃,汨罗成为他最后的归宿。生于乱世的杜子美心怀长安,却不得不衣衫褴褛混迹在逃亡的路上,面对无边落木,他仍念念不忘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生于香软朝代的苏子瞻,一生颠沛流离,但生性豪放的他,竹杖芒鞋,把一切的不如意放至名山大川,把旷达的精神留给后世。
他们都有自己的幽梦。屈子的幽梦是不能为国家尽力的爱国梦,子美的幽梦是面对生灵涂炭而茫然无助的忧民梦,东坡的幽梦是因无法掌控个人命运而纵情自然的山水梦,而张心斋则是抛却现世追求个性自由的自我梦。
心斋才情学识令人惊叹,可惜他生在思想禁锢的大清朝,自己尚且难以自由更如何让他人自由?和他同时代的生于法国的伏尔泰,却没有顾影自怜,他的启蒙思想让法国摆脱了封建专制,让整个欧洲走上了自由的航道。
心斋先生没有把中国引入自由之路,他做不到,我也做不到,明晚还去登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