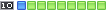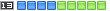甕公呆癡的手托江甕瓷瓦,望著諒山妹突然脫出握掌,他如何去何從都沒有,凝視她的蘭花指把他掌中的酒甕頸椎小心翼翼的拿在掌心。然後整個兒蹲伏地板上,抓起地板上散落的酒甕瓷片托在掌心,像捉摸而玩賞著相陪甕公數十年的酒甕精靈。但見諒山妹站起身子,朝甕公作了個神秘的微笑。諒山妹打此時開始,整個人的神儀投注於梳妝鏡裡,心靈感覺陶醉也似,鏡裡的俏麗臉矯情地浮映笑靨。剎那後,她就拉開抽屜,拿出一方收藏多年的手帕。手帕是艇王的泰國婆娘芭蕾姐留給她的信物…
(那年啊,初創時代的五月花飯店,我難民妹江湖情如橫刀騎馬萬丈豪情。買下湖邊宅院,艇王帶著芭蕾姐來五月花飯店賀喜。甕公最愛講他的酒甕情,七分醉態是裝出來的。我也嗜酒如命,知他人大顛大廢如馬戲團小醜,知他也是一往深情,同他對飲三杯撩心思。怎想到艇王會留芭蕾姐在「香閨」過夜…就是那回啊,夜來同芭蕾姐同裹被褥,我情不自禁同她肌膚親…然後聽芭蕾姐講她同艇王「商女萬里飄泊情,人生如夢愛如夢」。這夜是難分難解夜,摟著芭蕾姐我哭泣了。抱芭蕾姐想諒山在萬里外煙雨山前,留下夢醒離情不知何處夢何處…我空留諒山仙師懸念,逐出師門都是我的兵…罪過在他在我,我初夜為誰?為我的兵?我師仙師啊,我蒙昧何端呢我…山谷不再山谷,都因一場胡塗春意抱憾終身,我的兵齊小兵,這輩子我忘不了你啊也恨你,懲越毀我家園啊我的兵。青春夢碎失心也失身呢!…一方手帕留下芭蕾姐的臉頰香也體香我體香…哦哦…體香!芭蕾姐一去不復返…)
甕公看諒山妹用手帕包裹了他失落的酒甕瓷瓦。望著她細致的手指動作——左右手指細致的打了個手帕結,悄悄然臉頰轉過來,雙眸瞳仁鏡也似滴溜溜旋轉,嘴角含笑映照頰邊泛蕩漾迷人的小酒窩。激情過後的甕公,是真實的黃利九,彷彿如夢初驚的蒙昧。望著大妹子神秘地包裹酒甕瓷瓦動作完畢,把酒甕放進抽屜裡。他剎那間回到十五年前初會五月花飯店的情景——
(初會五月花事頭婆。手執酒甕望著諒山妹臉頰笑靨…為甚麼妳臉頰酒窩子,總讓我想起阮春雨啊…堤岸唐人街窄巷門前坐板凳,賣春的姑娘媚眼含春有情,阮春雨啊,妳姣羞裡豪興我也衰敗我,當年收買我浪子性根情根阮春雨…堤岸街阮春雨湮沒歷史煙塵裡。美國佬北越軍越南仔中國解放軍。怎料人間風雨交加,多少年後邂逅懲越兵,會同我初戀阮春雨生死相連…我阮春雨真蒸發人間嗎?…那回初會諒山妹,一甕拔蘭地咕咕咕咕咕咕瀉進喉嚨流進肚子,溫馨也溫暖的感覺泛濫了滿懷,裝醉掩飾自己難為情嗎?也不是。都是莫名其妙的傷心舊事,在阮春雨和諒山妹的溫馨夢裡流露。…那回妳領我踏邁阿米海灘,我第一次說了我和師父在九龍城寨,說了我的酒甕情…九龍城寨風光不再,我連師父的屍骨都無處尋。…妳我背井離鄉人。妳說了母親屍骨埋葬在妳和懲越兵追蹤的水牛破地雷陣裡…然後是諒山,妳叛師門的諒山。諒山大妹子,我想親愛的月花妹諒山妹,妳永遠不想說背叛師門為何?但我說了我和阮春雨,妳怨我嗎?…女人啊女人,我的諒山妹啊,我好想妳做我媳婦啊諒山妹。…)
就是這個時候,諒山妹放好手帕包裹的酒甕瓷瓦,從抽屜裡拿出一壘衣衫,放在梳妝台上,雙眸卻含羞答答望了甕公一眼,敢地地站在他面前。
「酒甕留給諒山妹收藏。寶劍佩英雄,太極劍歸主人好嗎?」諒山妹說。
「…」他才領悟諒山妹為甚麼?
「酒甕供奉蓮花寶座,分日我代甕公哥點香叩頭。」諒山妹說。
「哦…」他唯唯若若的。
「我的過去命哥,艇王贈甕公哥的過命槍金曲尺由諒山妹收藏紀念好嗎?」諒山妹說了。
「哦…」甕公領悟了為甚麼?
「邁阿米是甕公哥家。好好洗個熱水澡,穿上這套衣服。契女張月妹住月花妹家。」諒山妹說,臉頰邊笑靨漾溢。
「哦…」他唯唯若若的。
「諒山妹把你打扮好,甕公哥開始美國生活。」諒山妹微笑。
「遵命。」他是甕公神儀了。
「月花妹和甕公哥都戒酒。」諒山妹說
甕公望著他心目中的諒山妹雙腳踩著她的半高跟鞋噗噗噗噗噗載著她的腰身踏向地窖階梯。他也覺得自己腳踏實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