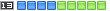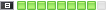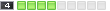快乐何达
最近不知怎么,想起了何达的诗。
做每一件事,
都给它一个快乐的思想,、、、
多年前的一个严冬,北京的校园。何达,一个来自香港的诗人,五十多岁的样子,不高却壮实,花白头发,红色的T恤,白色短裤,一双运动鞋。笑着走进了开足暖气,坐满了穿着冬衣的教师和学生的大教室,大大咧咧地坐在了给他准备的高凳上。谈笑风生地做开了他的报告。
他讲的具体的内容,已经不记得了。大概是从他早年求学,追随朱自清,后来在香港社会的挣扎求生,还有近期参加聂华苓创办的国际写作计划之作家创作室的见闻,当然还有他如何锻炼身体,冰天雪地里还能穿短衫短裤之心得。男同学们似乎特别欣赏他,他的一言一语,都有深厚的男性笑声附和。
他长得跟平常人没有什么不一样,一个普通的中国男人,说的普通话也意外地标准。但他又太不一样了。他的穿着,他的讲话的态度,他流露出来的随意不羁的风格。从他身上,我似乎隐约意识到什么是中国的文人、中国的诗人,什么是生活在中国大陆以外的文人诗人,也就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文人诗人。没有象牙塔的风雅,没有头衔尊称的灵光,没有钟鸣鼎食的优越,有的,只是抒发自我的随性与嬉笑怒骂的无忌。他,有点北方人的粗犷豪放,又有南方人的敏感油滑。有见惯世面的豁达从容,又有捉襟见肘似的寒酸委屈。他,像是一股冷峭不定的风,又像是一潭浑浊不清的水。是他,让我把“诗人”和“穷”第一次联系到了一起。我的心,为他感到酸酸的。这种感觉,我始终没有说出来。当他结束报告时,我随着大家使劲地为他鼓掌,绝没有敷衍和虚伪。
不住的掌声,鼓励诗人何达继续演讲下去。这时,他突然对身边的系领导轻声说:刚才是讲够了两小时,现在我再加讲半小时,在原来的报酬上,要再加十块钱。说完,又笑容可掬地对听众们开讲。在场的人,没有对他的话有任何的反应。那年头做报告,没有听说过有报酬的事,更没有见过当场讲价的报告人。也许是在场学生们涵养不错,也许多数人没有听到他说的什么,也许是听到了也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大家只是急切地想听他继续。学生们对他的耐寒抗冻的能力,似乎特别热衷。提出了各种问题。于是何达就更多了些英雄气概,述说着六十出头的他,如何短打扮地在俄亥俄的雪地里跑步,招来白人对他伸出大拇指,说中国功夫了得。又说他曾经把新生的孙子光着身子抱进雪地里。新生儿的母亲会怎么想呢?他是有妻子儿女的。我暗自思忖着。他是在用他的身体,来表现他的诗的。他这样一个人,和亲人的关系会是怎样的呢?做这样的诗人的家人,不会是简单容易的事吧?
作为报告的结束,何达朗诵了两首他的诗。我用课堂笔记的速度把它们抄录下来。一首叫做《换》,记得其中有一句似乎是:“换一双眼睛把这世界看穿”。另一首叫做《快乐的思想》。
何达,这么多年没有人提他,似乎比较暗淡。我上网查找他的诗和消息,居然少得可怜。他出版过几本诗集:《洛美十友诗集》、《生命的升腾》、《长跑者之歌》、《何达诗选》,还有三本散文集,但网上没有他的诗。关于他的事迹,记载更是少。一篇署名古剑的人写的不长的一段文字,让我恍然。
文中说,何达是香港专业作家,全靠稿酬为生以前写诗,写专栏,也写影评。一九七九年去北京开文代会,到处演讲,红遍大江南北。回到香港后,专栏地盘为他人所占,日子不再好过了。他曾去中大校外课程教点书。文章作者在《新报》副刊给了他一个专栏,也没有维持多久。作者说,八十年代中,又听说何达仅以面包果腹,就跟别人凑了些钱给他。在香港这个高消费的地方,也维持不了十天半月。后来听说他入院,他和西南联大同学的妻子离了婚,孓然一身,病后,也没有亲人来见他最后一面,送他一程。文章的最末问到:“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何达的《快乐的思想》,我至今还可以背诵:
做每一件事,
都给它一个快乐的思想,
就像把一盏盏灯点亮。
砍柴的时候,
想着的是火的诞生,
锄草的时候,
想着的是丰收在望。
与你同行,
想着我们有共同的理想,
跟你分手,
想着会师时候的狂欢。
我喜欢这诗,居然在多年后还想起来,也给了我一个快乐的思想。而最后的何达,是不是快乐的呢?诗,给人快乐的思想,诗人何达,却给我留下了心酸的印象。
2009-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