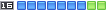跫然有声
走过封闭和野蛮――开化的脚步
无 题
西极有高楼,楼在云之翮。开窗临海市,投手弄清波。
呢喃儿和女,劬劳姐与哥。堕泪涨巨洋,吞声咽长河。
举头东北顾,尘沙障大漠。阴风御晦雨,夜长梦苦多。
难得天南地北同寒暑,歌伦常兮舞婆娑!
难得母女兄弟共一堂,戮心力兮历坎坷!
三十年华如流水,萍飘蓬转奈若何 !
— — 1966三十年华
题记:
当思念在琴弦与指间腾起,一朵白云飘进了我的窗棂。
它托着我越过无际的波涛,来到千百次梦境萦回的海滨!
于是我看见----
— —《遥寄姐姐》1955
北山岭上不老枫, 月下望眼正朦胧。
南海滩头相思子, 月下当摇向北的枝!
强忍泪啊莫悲咽, 打扫愁容对月色。
莫若随风上天去, 眼作星汉身成霓!”
――《月下》 1965
拂面尘沙笼禁阙,袂惹香山蝶。御苑拥明湖,玉溅金喷,把桨儿轻曳!
凄惶三十九年别,剩有碑如铁。罄北海清醇,仿膳佳羹,难洗心头雪。
――《醉花荫•北京》 1981
悲怆的呼号!我们一家人凄然相思的三十九年!
曾经有这样一个时代,昆仑山焦渴地呻吟,莽原上沙漠横生。流散在异国他乡的亲人们不能团聚,只要有这种团聚的愿望就会大祸临头。辛酸离乱,疮痍满目!
这个时代终于结束了!大门敞开,游子归来!走过礼仪的荒漠,让倨傲化为友善,野蛮逐渐归附文明,乌托邦演进于现实的自强奋发。这是不可小觑的大进步。亲人间可以经常来往彼此参与,这世界也可以互利共赢,带来的是累累硕果。
开放给人团圆、美满希望和成长。也让百姓对不时会有的鼓噪后退封闭的呓语,不论其自诩多么权威,敢于嗤之以鼻!顽梗至死者难免会有,而其下场也难免如古人有言:“汝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时值羊年春节,“三阳(羊)交泰,日新惟良”!祝福我们历经重重磨难的伟大的民族!
这里是这段历史的一份纪实。
于2015羊年春节
怀念Robert
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星期四,晴。
Robert在四月二十日去世了。一个八十三岁的老人,患了好几年的老年病--帕金森氏病,语言能力几近丧失,生活不能自理,那状况是十分痛苦的。好在是在发达国家的一个比较殷实的家庭里。他一周前出现发烧等症状,住进医院后转为肺炎,医治无效,无言地离开了这大笔家业、满堂儿孙和无限牵挂的世界。我知道后心情十分沉重,随即打电话慰问姐姐。姐姐还算镇静,她已经在他去世后过了两个不眠之夜了。
姐姐是在1943年离开我们远走他乡的。
这一年日本鬼子从慈利、石门侵入桃源的家乡,妄图进犯贵州,打通通往重庆的大门。沿途烧杀抢掠、无恶不做(按:日本鬼子侵入漆家河我的家乡,我全家逃难是1943年阴历十月二十三到十一月二十三、整整一个月。出走那天和回家那天都紧跟杨公忌日,据哥哥的记忆、不会错。这次抗日战役就是著名的常德会战)。外公留下的几十间瓦屋被烧光,外亲女眷中有的被日本鬼子糟蹋。附近的漆家河镇是从川黔顺流而下的桐油、木材、干鱼、山货的聚散地,原有沿河的挤密的吊脚楼木屋、封火营子连片的大宅院群落和整齐的顺河蜿蜒的石板长街,其中有名的德裕饭店是外公留给我妈妈的产业。这些都被日本鬼子一把火烧成一片灰烬和瓦砾,连烧了几天几夜,冲天的火光几十里外都能看到。我们一家大小几十口以及祖父学校的师生们,就是在这冲天的火光中由祖父统领连夜逃难。这时我七岁。
记得我抓住大人的衣襟被拽着、拖着,在瞌睡中跌跌撞撞地前行。记得在难民拥塞的善溪港渡口妈妈艰难地把幺姑爹硬扛上船,再顶着日寇飞机的疯狂扫射去撑篙。幺姑爹(这里爹字乡音读成dia,dia是祖父的意思)是祖父的小妹,独身、奇胖,一路蹒跚着,可敬又可怜。当时日本鬼子飞机一梭子弹从三叔腰间穿过,幸好他在腰上围了一根通带,里面装有十三块银洋,这是我们的生活费;银洋被子弹穿出一道槽,但是保住了三叔的性命。而独自留在麒麟岗下绍益湾家里的爸爸,拼死从一个鬼子军官手中抢回一箱整套的《二十四史》却毛发未伤;这是文化的力量,真是洪福齐天。
我们全家逃难的这一路行程,漫长得就像这贯串一生的记忆,是对日本强盗永远的仇恨!终于我们逃到了叫做“耙子界”的高山坪顶上。这山坪就如同如今世界闻名的邻县张家界里,贺龙家乡天子山那样的山顶大台地,下面是丘壑层叠的深沟。我记得祖父和刘爹爹(diadia)结拜为盟兄弟时的那场盛宴,那桌子连接成的长阵和善良纯朴的山民。刘爹爹是一个一样笑容满面的干瘦、精干的长者,山民都听从他的话。在这里祖父还去附近的国军抗日司令部会见了会战主力74军军长王耀武表达支持。我们在这里住了几十天,隐隐地看到零星的日本鬼子的膏药旗从遥远的山下树影里穿过。之后,我们才将扶着,踩过漆家河摇摇晃晃的浮桥,穿过漆家河镇的废墟回家。其实也就七八十里地!
姐姐就是在这一年离开我们逃难他乡的!
当时姐姐随就读的学校西迁,辗转到达贵阳,见到在那里工作的四叔。随即又几个同学结伴,或徒步,或搭便车,历时几个月到达成都。后来姐姐与在成都工作的姑母姑父会合,在那里上协和大学。姐姐读书读的十分地艰难,妈妈自己纺纱、织布、喂养山羊,企望有补于姐姐的读书费用,可是又能挣得几个小钱?我也从桃源民报看到,姐姐向县参议会申请资助,只得到寥寥无几的经费。
姐姐是1947年结婚的。我从照片上见到的姐夫是一个浓眉阔额的英俊青年,三代海外华侨,中山大学毕业后去英国里兹大学深造。当时他在飞机制造厂作技术工作,Robert是他的英文名字。
他们后来回到了海外的家里。可是,星移斗转,漫长的岁月里,我一直见不到Robert的人,也见不到我的姐姐。在野蛮与无知笼罩的漫漫长夜,这种期盼分外的凄苦!
那个年代,这种再自然不过的亲情被涂黑标之为“海外关系”。这是令人谈虎色变的涉及“特嫌”“内控”的关系,是可能被随便讯问、搜查、打击陷害的。许多人终止了与国外的亲情以求自保却未必能保得了。但我们别无选择,妈妈和尚年幼的我们需要生存,姐姐姐夫已无处不在。
除了无端的文字狱,海外关系是引发我长期灾乱的半个主题。那年我十九岁,在长沙大古道巷一号衣帽间被囚禁三月、无分日夜交待所谓问题的日子里,要反反复复地写Robert。姐姐姐夫历年的来信被没收,这些信件在后来的文革中又再次被没收,直到最后装模作样发还时只有极少的信封残留。本来平庸的几个同事,霎时成了凶神恶煞,窜到妈妈岳麓山刷把冲的住处拍桌打椅,恨不得掘地三尺地搜寻还有没有Robert的秘密。连大我五岁的同班同学,专擅嘲笑人弱点、失误趁口舌之乐的盛粟壳(长沙方言,油嘴滑舌),自称平民出生却连入团申请都不敢写的,平日里拈轻怕重,这时也积极非凡。我记得他龇开一口稀拉的长牙,狞笑着“卷兄卷兄”地揶揄我,一边学着别人的样拍着桌子威吓取乐。这头猪!
卷兄是我信中对Robert的称呼,看了我被迫搜走的信,有甚么可神气的?我也照样对拍桌子,对骂他不要乘人之危、欺人太甚!我毕竟太年轻,尽管不论态度好坏我都不能逃脱厄运,与他们的这份对抗成为惩罚我的何等多情的话题:所谓对抗运动,“为挽救其本人”云云。这位盛同学就这样在运动中入了团,几个月后按调干生待遇去北京进修并留在那所高校里;退休时,也不过一个副教授而已,未必比同学们谁强。那年老同学聚会盛自觉尴尬拒绝赴会,却对聚会发起者吴君坚持说他们当年那个运动整我没胡搞;足见灾乱的利益既得者是不会说真话的。后来才终于辗转从吴得知,盛不久自杀,却不知为什么?死者已矣!好歹曾是同班同学,愿他的灵魂心满意足!
我那时尽管年纪全单位最小,已经因为省级单位政治学习统考得整个系统唯一的90多分,而按照预先的规定得升入中级班却没有他人,于是成为机关学委会三人组成员,主持大会学习讨论。我习惯于勤奋好学,即使在在挨整期间仍然自行参考美国国家标准ASTM及苏联国家标准ГОСТ,通过实验成功修改了几条我国的国家标准。这些,在被迫离开单位时也不能不被肯定,而且对我宣布日后是要回到单位的。
五年后,我在农场文工团被宣布重获自由。归去来兮!妈妈老而病重,胡不归?
而正在这时,面对财政和就业难的压力,黔驴技穷的体制只懂得依赖惯熟的‘阶级分析’手段处理机构精简问题,首先将认为阶级有问题的人撵出机关乃至撵出城市。
原单位以精简下放正紧又无分支机构为名不能让我回去工作。以后怎么办?执着于我的由学生参加工作的女演员问我,我说万一没办法也可能看能不能去国外我姐姐姐夫那里。这话却被一位老饕辗转听到并随即去揭发了我。这老饕曾是省文化局的音乐创作员。只因前朝当教员时参加三青团在肃反中受到审查,他惊惶无状,自供奸淫了72个自家的保姆以示忠诚却无法宽宥,发配后来文工团的。
两天后我被撵入“就业队”与劳改释放的前军人警宪一起生产劳动算是善待,这里人比较规矩。据称我有双重的罪过,其一、不该任身份清白一厢情愿的女演员对我示爱,何况正有农场医院院长在追求她。这院长是文工团与宣传部头目们的同类,身份何其高贵!
大姐诗人郑玲此前在女演员中称道的爱的执着,这时竟起了作用。文工团的批判会十分冷清。而这反而促成了这段可怜的感情的确认与延续。
其二就是我有甚么叛国意向!这是连“时日曷丧,余及汝偕亡”也千万不能吁嗟的年月,何须的辩解又有甚么用?好在农场人事科的秦建新干事是我初来时曾在农场农科所工作授课的半个学生,我不久就请假离开了农场,并由他帮助转出寄回了户口。
尽管海外关系如泰山压顶,我们已无可畏惧,我们又万不得已!早在从我们离开老家到达长沙起,姐姐姐夫就负担我们的读书费用并一直按月寄给妈妈。而这时我再回到妈妈身边、是连同我一起的生活费。三年里我守护着病在床上的妈妈,其实妈妈也是在用病守护着她担惊受怕、望眼泪干的儿子。
在社教工作队进驻,江青打造的前奏《评海瑞罢官》出台,文革风雨欲来的1966年正月初三,惊恐茫然的妈妈绝望地去世了,她见不到从未见面的女婿,再也见不到女儿。
随后的文革中,我带着被打得血染衫裤、淤伤遍身的双目失明的哥哥,领着幼小的侄女逃难几年,我打工,我流浪,世道令人绝望。
只有姐姐姐夫义无反顾地继续接济我们!
我们会许能见到他们道一声谢谢?
然而物极必反,世道也有穷通的时候。
一九八零年,我们第一次见到了Robert。这时候尽管还没有得到平反,我已在前年被评为市级的先进工作者,多次在全国范围的学术交流会上做过大会报告,心情爽快了许多。四月里我们接到电报,Robert会随观光团在上海南京路的和平饭店停留,望相见。我陪着哥哥,领着六岁的女儿,从武汉上了去上海的轮船。记得我们穿著春装,一路和风丽日。船上的两天,河山壮美,女儿十分开心,服务员阿姨照料着她,给她梳头、洗澡,领她到处溜达着嘻玩。到上海后,经上海市侨务委员会接待,我们住进白石渡附近的海员俱乐部。
Robert观光团的日程是早就安排好了的, 我拨通了Robert房间的电话。我无法听懂接话人的方音,而对方也听不懂我的普通话,只急得重复地大叫:“Please speak English”!这是Robert的同伴,一位闽南老华侨。我们是在和平饭店与Robert会面的。宾馆外观富丽、但内部仄逼黯淡,电梯外面等候着许多的外国人。我们都很高兴,这高兴无须用很多的语言表达,我们早就从照片与信件中熟悉彼此了。Robert语速较慢,语气稳重,仿佛了如指掌。我们也就万般凄苦化为一笑,见面就是一切了。门户初开,也许隔墙有耳,那时的久别重逢想必都比较谨慎!简单的介绍了情况,Robert抱起女儿,请同伴为我们拍了好几张照片。这照片我们一直珍藏着,孩子笑着,我们笑着,一个个笑容满面。仿佛第二天Robert就离开了上海。分别前我拉着哥哥,Robert牵着孩子,一起沿南京路走到第一百货商店。Robert和我一样不会买小礼品,还是我让他买了双小孩皮鞋,价值一十三元人民币。
Robert也是为姐姐回国探路的。第二年,姐姐也回国来了。这是1981年4月底,我正作为两位之一的特邀代表在黄山参加全国会议,与化工部掌管一方的主持人老喻一起住在黄山宾馆据说邓小平曾经住过的大套间里,开窗正对着蜿蜒跳荡的人字瀑。接到电报我就辞别黄山直奔广州迎接姐姐,后来到了西部故城、北京。北京沧桑难改,在慈禧住地养心斋后院见识到皇宫老旧木结构土坑厕所里无从躲避的乱飞的苍蝇。回到家乡省会长沙,姐姐受到湖南省副省长周正在宫殿般的湘菜馆盛宴欢迎。
祖籍所属常德市政协主席专程来到湘江宾馆姐姐下榻处守候。见到这位农民领袖敦厚殷切的笑脸,回想当初祖父辈延绵下来的无情的冤狱,我不觉时光恍惚,浮想萦回,早日撕开的乡情竟然要随着对于投资的渴望回来了。
与Robert的第二次见面是在1985年五月了。Robert将回国到达广州,要我去会合。
我给同吃在一个食堂的市外办也是侨办主任老何谈及,何要我一定要把他请到故城来,为表示欢迎的热忱,坚持要提供宾馆免费住宿。
广州市科技交流馆(科协)1976年就举办过我的专场大型技术报告会,以后我和他们也多有往来。我到广州后,经广州市科技交流馆谭培流介绍,住进珠江河南的一家招待所。而后按照约定去找Robert的一位记得似乎是姓李的乡亲。我在北京路一线走了三个多小时,薄暮时分才在广东省政协宿舍五楼找到了这位几经升迁地址改变的政协副主席。他告诉我Robert今天到达,已住进白天鹅宾馆。我随即赶去,白天鹅宾馆在广州的沙面,倒不算远。这是新建的五星级宾馆,洁白、高雅、依水而立,仿佛要凌空飞去。陪同Robert到广州的是香港的启麟,Robert的侄孙,这时他已在东莞投资办工厂。Robert兴致很高,我们一起在沙面附近到长堤一带徜徉,或在饭馆里寻觅从前的口味,在大大小小的百货商店里欣赏古朴的乡野小摆设、日用品,他是在寻觅几近逝去的乡情!
几天后我陪他来到武汉,住在晴川饭店。并在青山的堂姐家里逗留,品尝她特订有蛇、甲鱼、蛤蟆肉的家宴。然后我们一起去西部故城。武昌到故城的火车我经常乘坐,300多公里行程,约七小时抵达,一向不用提前买票总有座位的。可是不巧,当我们来到武昌车站,却只有站票可买。Robert已是六十多岁老人,又是市里想邀请的宾客,这怎么好?我找到车站的调票室请求帮助,也无法弄到一张座位票。勉强上了火车,车内确实十分拥挤。站了一会儿后找到列车长求助,让在卧铺车厢挤着坐。
后来一位刚认识的洛阳铜矿处长老乡善解人意,说他在上铺,白天里他不用睡,可以让Robert去休息。我却认为上铺高,攀上去难,对Robert不安全;也不好用人家的铺位,急忙谢绝了。Robert一路疲劳,已颇感不适而我不觉。后来他对我说,当时很想攀上去睡,经我一说只好罢休了。这样支撑到了故城,住进市委招待所的带客厅的套间。
市侨办主任何认真而热情,谦逊地跑来,拿了一迭准备好的材料,对着Robert一连讲了三个多小时。他介绍故城的历史、地理、矿产、工商、民族、人文、旅游资源等种种情况,目的是吸引投资。Robert撑住眼睛只静静地听着。我忍耐不住,已在这熟悉的院子里进出多次了。故城的古朴与简陋、落后都是一眼就可以看透的。古文化荫蔽在原始森林的蓊郁一侧,周朝楚国故都与唐人传奇中裴航得道的仙境同在市辖的大别山余脉大岘山一线,山重水复又兵家必争;倒是个流放的好去处!直到这时,来这里唯有火车可通,而且得在武汉转车。“可惜了一个隆中”,Robert叹道:“搞一个洗印摄影胶片的spot都会红火(也许不得赔本)的吧”!隆中曾是诸葛亮的隐居地,Robert去看了。
Robert终于领略到了那时西部的好客与粗鄙,而且必定有深切的记忆。那是第三天临别前侨办主任的筵席上,奉陪的有侨办的小王,有一见面就称呼Robert为大哥的女秘书汪乔和几位记不起姓氏的属员,地点在市委招待所的宴会厅。还有几位高级别的市领导奉陪,但他们要陪的客多,不久就到别桌去了。山野边地,民风豪放,酒杯是不能随便端的。宁可让酒杯覆在桌上,任他百般诱逼也不动手。一旦端起酒杯,必定要一饮而尽。而且会多人连连敬酒,一个也偏废不得,直到一醉方休。我是偶尔见过这种场面,在一间中学酔卧一宿的,所以岿然不动。而Robert虽遍游世界各地,却哪有这等的经历!Robert先是尴尬的微微笑着,后来见对方推汪乔一再说:“大哥游遍世界各地,必定酒量可称,不喝就是看不起我们!”这不就失礼了么?不得已抿了一小口酒。这一下人家以为果然有酒量,于是频频劝敬。Robert哪里喝过这种烈性的白酒,不几杯就面红耳赤。而且因为积有劳累不适,立刻嗓音沙哑,说不出话来;人也歪歪趔趔,坐立不稳。筵席只好讪讪地结束,我很遗憾!当晚,小王拿来辗转托人买的列车乘务员寝车的卧铺票,票钱指定我得用侨汇券付,不要人民币。
Robert抱病离开了那里,好几天嗓音竟还恢复不过来。
第二年、姐姐再次回国。在美国与海外各地的亲属们也都纷纷回国来了。几十年与妻儿隔绝的幺叔回国接走了幺婶。日后幺婶得以带回幺叔的骸骨归葬故土,在初期的狂暴中屈死的他父兄的衣冠冢一起;了却了一个几十年孤苦不安老人刻骨铭心的愿望!
几年后,我们来到姐姐居住地海外观光并小住,为了这,姐姐申请了好几个春秋。我们也得通过省科技局、省公安厅的批准办了几个月的手续。
一切都是姐姐与Robert的妥善安排。我这时虽然已是高级工程师,我俩都是获得国家级科技奖的无妨列为的专家,工资却不过一二百元人民币,哪能承受得起一千多美元的往返机票!而当局批给我俩出国撑体面的外汇票才四十美元,十元兑换一美元,还不是现钞。恰如一只铁公鸡,哪有一毛可拔?当然衣服向来是有的,而我为图简便,只带了一长一短两件衬衫,一条西装短裤,外加两套换洗衣裤和一套季候不宜的西装。这样每天穿著几乎完全相同的衣衫,丝毫不关注是否显得寒伧。我们越过香港,飞进了白云苍海深处。天蓝水碧,鲜花绿草,到处洁净无尘。这就是那个我梦寐以求的团圆之地,那个我在诗里称之为“云之翮”,梦里“一片白云托着我”去的地方!
姐姐开车接我,Robert开车送我,我们走遍了那里的角角落落。团聚让我沉醉,终于了却了我们一宗心愿!
可是这一年发生的事件颇让我难堪。在过路的香港,在凡有华裔人的地方几乎都能听到一种诘问,看到不平的目光;却奇怪走出国门的我们的不知与坦然!
而国人的贫穷如此分明,也总会遇到挑剔的眼神与玩味的喁语。
那偶尔来陪Robert打一次麻将的不过是路边的小贩,每每谄媚而自得地睨着我说他广东老家的姨妈舅舅如何是好钱的老饕,如何地编着法儿向他们要钱得加意提防!
在境外人们眼里仍然既贫且贱!这让我感到炽燃的悲哀和无可奈何的沉重!
积贫积弱更需要智慧、审慎与奋发啊!
多么期望一个焕发出无限创造力,思想上开放豁达并有全球视野的我的家国!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有出了国才越会懂得家国的意义,我相信这话。
我的独立和自强得到的或许不可理解与近乎揶揄!
然而我好不容易走上可以不必国家供养、自主自立的科研路,而且练就了对业内世界一目了然的创造能力。
而时不我待兮!我一生中的大好时光大半被无情耗磨,已经不能怠忽!
这年我已经年过五十,还有几项关于钢铁和热工的材料课题急待完成。与其徘徊沉吟,还不如及早回到自己的混沌里去。那天一早,天还没有大亮,没有叫车夫,Robert自己开车来秀雄家接我们。在机场登机口,姐姐哽咽了。我看到了Robert泪光闪闪!别了,Robert!我会记得你深沉的祝福,你也放心好了!
于是有些年的趋于安心的各自奔忙的日子!
谁知这一挥手竟成永别!我再也见不到Robert了!Robert,我的兄长,多少年来担心着我们的疾苦与生存的人,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Robert是一个宽厚的人,一个深沉的人,一个成功的人。他必定经历过许多磨难,许多痛苦。而今怀着深深的眷恋与遗憾离开了这斑斓杂沓的尘世!
我深挚地怀念Robe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