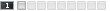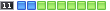十八春
南齐饿鬼
时至今日《十八春》我还是只看了一半。因为一个偶然事件,一封信改变了曼青和世钧。这也应了那句俗话,无巧不成书。那时我在一所学校广播里播放着《光阴的故事》“流水它带走了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人。”许多头发斑白的人相聚一起唏嘘。五十年校庆热烈里透出几许伤感。工作之余偶听音乐,更多的时间看书打发。小雪在来信里说:同事间喜读《半生缘》。我不是张迷,张爱玲作品只读过散文集《童言无忌》。刚好高考的考务费300元,我在书店里淘了半天只得买了本《十八春》寄她。现在想来,那时就应当有黎明、吴倩莲演的影版《半生缘》,我却是在2005年的三月二十六日通霄电影中看到的。整个晚上我看了四张碟《手机》、《十面埋伏》、《半生缘》末一个是《暖》。影片中捡手套,梅艳芳吞食手剪馒头忠实原著,这在香港电影中已是难得,只是结局是否和原著一样不得而知。我不知道小雪有无看遍全书,猛然忆起三月二十六日是她的生日。只是不知道她此刻在做什么,她总是快乐的吧!我在心里默念着,其实我们分手已经二年。
前年春节,我们坐在一起说话时,她对我说《十八春》就是《半生缘》呀。我还是睁大眼睛,小雪说这么笨的,罚你洗袜子好啦!那时我们还不谙世事,相聚之日少,分离之日长。她还没有说出:“一个人不孤独,想一个人才孤独”的话。在一起的时候,喜欢手挽手扎马路,看到街头卖东西的就一起凑过去。开始的时候她总迁就我,陪我吃羊肉串联,鱼片什么的。后来就有些不大情愿,我知道她的职业病占了上风,毕竟她是个护士。看到我捂着肚子穷叫,她总有点幸灾乐祸,放下手头织的毛衣,一边给我找药一边笑,我看你还吃。毛衣织了大半,是当时流行的蓝色,我平静之后。她把毛衣放在我身上比划着,我心里暖暖的,却故意地问,不会是给我织的吧。“美的你,这是给我弟的。”你弟好像比我胖,她像说破心事地红了脸。现在这件毛衣穿在我身上,只是许多的事,已面目全非。
我们相识始于书。有时间一起看《半生缘》吧。好啊。我们就这样说着,以为有的是时间,却无数次与影片擦肩而过。她有时会撒娇地问我,你信不信缘份呀!然后拿起我手看,“活到八十岁,一生只爱一个人,然后坐在椅子上死掉”。我们就这样说起了命运这个东西,县城不大,县城僻静的街道的荫凉处随时可见摆摊的算卦的人。须发皆白,背靠大树,时不时议论,文王,周公、原始天尊、姜太公。电话里小雪说一个好朋友相信这个,我对她说试着远离。我不知道她的女友是否应了算命先生的话,不久之后她们就分了。俩人的说法如出一辙,缘份已尽。《巴黎圣母院》里雨果谈到一个词希腊语:宿命。很多人逃不过,我和小雪最终也成了许多人当中的一对。
认识小雪的时候,她刚好十八岁。她好像总是心事重重,有着和年龄不相称的忧郁。她有一个姐姐,二个弟弟,一个为富不仁的姐夫,爱喝酒却任劳任怨的父亲。知觉告诉我,她试着摆脱什么。喜欢读书,女性作家里最爱张爱玲,写了许多关于张爱玲的文字。热恋之中,我也开始写一些不成样的东西。不过,我喜欢的是推理小说。她收到第一笔稿费的时候,快活得像个孩子。一下子扑到我的怀里,伏在我肩上不说一句话。这里我第一次拥抱女孩子,少女的身体是如此温软,我情不自禁地吻了她的额头。她像被蜜蜂蛰了一样从我的怀里跳出去,你这混蛋占我便宜,抬手就是一拳。而我还得屁颠屁颠跟在她身后,转了大半个城方才罢休,县城虽小,好在也没有走到头的时候。
当电影的画面切换到曼青到南京,世钧的父亲说:“我好像认识她”。我的眼泪止不住滚落下来,从认识小雪,我们一起走过八年,我们相约十年后见面。把碟片抽出时,天已放亮。街面传来女歌手“缘分不停留,像春天来又走”,三月的街道充满了梦一样的忧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