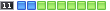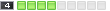文/心之初
我家的小后院,有棵梨树,大年能结二三百磅,小年也能结一百来磅的一种美国梨。味道没有三十年前的中国鸭梨或雪梨那么甜,那般细嫩,但也很不错。有朋友说像咱国内的苏梨,但我没吃过苏梨。
十五年前,我们们刚搬进这所房子的时侯,心里的欢快是难以言喻的,终于割上自家草,好像当时心里也咯噔了一下自己国家的苗,但“无产者一生奋斗求解放”,有时不管“苗”和 “草”。有自己劳动挣来的房,能割自家草,才有点“解放”感觉。“无产者”半生身子上当;"有点产”,却是在他乡挣得,人飘流海外,灵魂有时飘荡。虽说从没摸着过,但我信信人有灵魂。
我很爱我家房。爱高大客厅,爱屋后梨树。房后的梨树结的梨,十几年前我不太爱吃。人成天都在忙苦,没空闲愁,也没吃过多少自家梨,全送人。几年前,我病倒回家,重返人间,自削梨一个,慢吃,好极。我从爱上老梨树结的新果,爱上日常生活。于是我开始每年做冰糖梨水,削皮,切块,再用BLENDER 打碎,熬半小时。每喝时,还爱哼那北京人爱唱的《冰糖葫芦》。冰糖梨滋甚补甚我不太知道,但冰震而喝之,一个人就四个叉。人活,不就老想爽吗?后来我就不成天想“壮士饥餐胡虏肉”了,偶尔还“晓风残月”。
这几年,这棵梨树结的果,味道步步高,年年甜。每年收的梨还是送很多人,众人吃,众人香。丰收时节,正是咱新中国的国庆。真想我妈一大筐,梨,让她能吃着儿家的梨,打麻将。离家的日子太久了,五月,会有不少人想我。
刚送过“清明时节雨纷纷”, “带叶梨花独送春”,春暖花开。红酥酥的五月,老夫老妻新房,”欲黄昏,雨打梨花深闭门”。哪里去找梨花?
5/5/2009
[em43][em43][em43][em43][em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