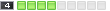乡村常常被描绘成一幅静物画,或被列车的窗口剪裁,或被柏油马路上的中巴的车窗定格。
但乡村更像一幕没有尾声的鲜活话剧。春天,我们可以听到布谷鸟的鸣叫,它们穿透力很强,往往看不到它们的身影,就被夏收后的一场雷雨冲淡。它们是候鸟,是乡村的客人。还有那曙色中的鸡啼,深夜的犬吠,它们是乡村四个季节伴奏的鼓点,不能代表乡村的内涵。
如果用什么比喻做乡村的歌喉,只有唢呐最贴切。它们可以像油菜花一样热烈,可以像槐花一样忧伤,如此的跨度,足可以演绎乡村的沧桑。
它们总在等待着灵感,也许是某个早晨或者某个黄昏,婴儿的一声啼哭,也许是村头或是村尾,乡邻的一阵呜咽,也许是某个吉日或者节假天,新郎新娘酒盏交杯撞出的笑语,都可以让它们润喉。跟随一阵阵鼓点,它们就像田埂上的小草一样刺破晨色。我们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就和整个村庄跌入唢呐渲染的氛围。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它们演绎成摇篮曲和母亲的叮呤和芦叶笛一起呢喃。呢喃成许多美丽的童话,装满我们破旧的裤袋、褂袋。我们开始学会向往,用小鸟初升的绒毛想象乡村外的世界。
当我们一天天的长大,那些高高低低的沟坎,那一道道门框,磕掉我们的门牙,也磕掉我们的灵魂。我们不再肤浅,我们学会深刻的流泪或啼哭。在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看到唢呐的七孔灿烂成七颗星和父母的目光一起照耀我们归家的路。第二天早上醒来,灵魂在我们的眼眸上复苏,沾满了父母掌心的汗渍和乡村小路上的泥巴。
终于熬到收获的季节,桑椹和柿果把我们的脸膛照得很亮,把乡村照得很亮。打谷场上,麦子和稻谷按照节气码得很高,比它们更高的是唢呐发出的欢乐的音符。我们把它们用红头绳串起来,那是乡村的嫁妆,我们把它挂在新娘的颈上。
喜宴散尽,人生有时就像一场宴席。乘我们的笑意还没有完全冷却变咸,我们要送别我们的爷爷、奶奶、我们的先辈们。他们最终成了乡村的游子,如一丝炊烟飘向远方。村口的榆树、槐树,你们在瞻望什么,是不是在偷窥我们昨夜的梦境。喜鹊衔起唢呐凋零的音符,去搭建相会的仙桥。
岁月如梭。时间在蚕食我们的心,城镇在蚕食乡村。唢呐的声音稀了,就像头顶上的星辰,乡村沙哑了。
看着墙上的静物画,我们开始怀念唢呐,怀念乡村的声音。
2009-5-6布谷于苏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