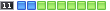从亚瑟到蒙泰尼里
在我妹新家崭新的书房里,我看到装潢精美的世界古典名著们整整齐齐地寂寞地站在她家那古香古色的书橱里。它们看起来一尘不染,但我确信它们无人问津。显然它们的功用已无可奈何地转换成了装饰品,就像是我们女人需要首饰一样,一个家也需要书橱和书橱里的书。不是吗?
但我的眼睛还是忍不住在那些熟悉的书名上徘徊,宛如看见旧日的老朋友,难免想叙叙旧。是啊,在那些精神生活匮乏的失学的年代,就是靠着它们,这不,高老头,邦斯舅舅,贝姨,羊脂球,贵族之家,呼啸的山庄,烟,她的一生,荒原,德伯家的苔丝,名利场,爱玛,简爱;当然还有复活,静静的顿河,古丽亚的道路,勇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安娜•卡列尼娜,约翰•克里斯朵夫……,靠着它们,躲开文化革命时期无法理解也无法改变的现实,编制一点点与现实完全不合拍的青春梦想。如今看见它们,每一本似乎都能唤起那些久远的,如今早被遗忘的陈年往事。不过,人的路毕竟只能往前走,虽然我确信如果再去读它们,必定会有和年轻时完全不同的感受,但终究不会再去碰它们了。
突然,我的目光停在了那本薄薄的夹在青年近卫军与罗亭之间的名字:牛虻!我的手下意识的伸了出去,不假思索地把它轻轻地抽了出来。就在这一瞬,刚才的想法发生了变化。人们常说女人善变,看来还是有道理的。
躲开一屋子的热闹,我悄悄地带着书走到我小侄子那间有个藤椅秋千的小屋,如同带着初次约会的男朋友。坐在那个并不是很舒服的晃来晃去的藤椅上,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这本我曾经用手抄下大部分内容的爱尔兰作家伏尼契的小说。让我自己都感到吃惊的是,我竟然还是和从前一样,感动得泪流满面。 不同的是,以前的眼泪为亚瑟而流,如今为蒙泰尼里。
我第一次读这本小说时是十四岁的样子,一下子就被亚瑟的那股劲迷住了。当时,我和一个好朋友一起拿到的这本书,我们兴奋地秘密分享着这本书带给我们的那种完全不同的神奇。我们咀嚼着牛虻所受的大苦大难,以及之后的那种洒脱,玩世不恭;体味着他那种外表的坚强与内心极为脆弱的巨大反差;欣赏着他冷嘲热讽背后的真诚……。用现在的语言表达就是一句话:酷!
我们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也追求自己的偶像,虽然我们没有现在那么多的选择。自从读了这本书以后,我的偶像就是牛虻了。不同的是,我们不能说出来,也不能与任何人分享,(除了那个唯一的朋友),如果说出来不但会给自己惹来麻烦,甚至会给老爸老妈带来灾难也说不定。我们只能把它悄悄地埋在心里。而恰恰就是因为这种神秘性,无端的给我们的青春增添了那么一点浪漫,那么一点肃穆,让自己与众不同起来。那个手抄本至今保留在我手中,即便飘洋过海,也没让它流失,那真是可谓青春的见证了。
毫不夸张地说,亚瑟,确切地说是牛虻,在一段时间里影响着我对男人的判断。在那时,我心中的白马王子就是那种内心隐藏着极大痛苦却总是把一丝嘲讽玩世的微笑挂在嘴角;目光冷峻,内心却像火一般热情善良的男人。说起来真的好笑,如果说给我女儿听,定会让她笑掉大牙。但这是真的,一点儿没编。
而如今,四十年后,已经走过大半人生的我,再一次读它,当年的偶像——亚瑟,也就是牛虻,他不再有打动我的力量,反而觉得他坚决地反对教会反对政府,有意要毁掉自己的一些做法很是有些幼稚,夸张。而作品中着笔不多的,以前被我几乎忽略掉的另一个重要的角色,蒙泰尼里,这位红衣主教,却意外地深深地刺痛了我。
现在回想起来,以我当时的年纪和阅历我是不可能理解一个神父与一位有夫之妇通奸,并生下一个私生子在当时是怎样的一种罪孽,(就是对当今的天主教来说也是不可饶恕的)更不能理解一个男人不能爱自己所爱的女人,不能爱自己至亲的儿子,甚至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儿子被送上刑场而无能为力的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
蒙泰尼里大人凭借着他渊博的学识,仁慈的胸怀,和他对自己信仰和上帝的忠诚获得了教皇的信任,也赢得了教民的尊重和爱戴。他在自己的事业上一路顺风,当了红衣主教,这一仅次于教宗的几乎是天主教中最高的神职。可是有谁知道他的罪孽,他的痛苦,他内心的暗无天日呢?!他是虚伪的吗?
当亚瑟被关在监狱中,面临死刑,蒙泰尼里大人来到牢房,对死囚犯进行礼貌性的探访,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一次有很强的做秀性质的探访。亚瑟终于忍不住,揭开了自己的面具。他用几乎克制了一生而迸发出的巨大的热情对自己深爱的父亲说:只有你可以帮助我,父亲,丢掉你的上帝吧,它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我年轻的时候用一把锤子就把它砸碎了!帮我逃出去,然后跟我们走,让我们重新开始……
蒙泰尼里面色苍白,浑身发抖,可他做不到,什么都做不到,他只能像个梦游者,失魂落泊地离开了牢房。
亚瑟死了,死于一个列队的抢手之下。
是啊,蒙泰尼里大人是个高尚的人,是他为之终其一生为之献身的上帝最忠诚的儿子,是广大教民心中神圣不可动摇的信念,他如何能!如果能够,他如何能让自己心爱的女人在悲伤痛苦中死去,如何能够,他如何能欺骗自己的亲生儿子,如何能把自己的儿子也领入歧途!他什么都做不到,他早就没有了自己,他早就被他的所谓信仰所窒梏,被他所谓的高尚使命感所迷惑。如果说他还真的能做的,他唯一能够做的恐怕就是连他自己一同毁掉了。他果然是这样做了,在做一次庄严的弥撒中,他发疯了,然后心脏破裂,轰然倒在了他战斗了一生的神圣的神坛下……,仍然没有人知道他的痛,他的悔,他无边无际的内心的暗夜。
埃塞尔•伏尼契,这位伟大的爱尔兰作家,据说是女的,请接受我的致敬。虽然这已迟到了一百多年,但真诚的敬意任何时候都不会嫌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