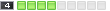转眼就要过年了。鼠年走开,牛年过来。应该有点感想。出国二十年有余了,说实在的,没有过过一个像样的新年。过年对我来说,似乎只属于过去。
小时候,日子过得比现在慢。家里的窗户边上墙上,总挂着一本日历,妈妈每天撕下一张,要很久,一本日历才被撕完。我由此对西历的元旦知道是怎么回事。妈妈可总念叨“阴历”如何如何的。于是又知道还有个阴历。特别是有个春节,跟阴历有关。
早先的农家日子,春节前后应当农忙前最闲的时候,天气又是最冷的时候。人要吃饱,穿暖,才能挺过冬天,才能有体力下地种粮食。在这个时候过节,人们把积攒一年的好东西拿出来享用,吃好玩好,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妈妈曾说,过去农家过年,从腊月二十三祭灶,到正月初一新年,再到正月十五元宵节过了,才算真正结束。比西人如今从圣诞到元旦,只有一个多星期时间,长多了。
我是文革中长大的,新社会,城市中旧风俗被破除了很多。“除四旧”以后就更是不敢讲旧俗。没有贴春联换门神,或是拜神明祭祖先的那一套,农历新年仍是最热闹的一个节日。因为每家都能买到一点配给的花生瓜子,平时见不到的。商店里也多了一些鸡鸭鱼肉,新鲜蔬菜水果什么的,但是得排队买。有个朋友回忆说,有一年她爸说:不要太早买花生瓜子,早买早吃光了,留不到新年。可快到年三十时,花生瓜子到处都卖光了。急得她爸拿着副食本全北京地找。
孩子们最喜欢的,是那些包着红纸的鞭炮。有一种挂鞭,是由一个个火柴棍长短,筷子粗细的小炮仗编成的,可以拆开成一个个的小炮。我们叫小鞭。声音清脆好听。院里男孩子用手拿在手里,另一支手用燃着的香点着上面的火捻,着了之后就扔出去。炮仗就在空中炸开。女孩子们都不敢。我是一个好奇爱逞能的女孩。也拿着放,扔出去之后,就很得意。有时没来得及扔出去,小炮把手指尖被炸得生疼,也不敢说。等不太疼了,又去放。一次,把燃着的炮仗扔到晾衣绳上晾着的一个雪白的绣花枕套上。上面立即被炸出一片炭黑,我被吓傻了。傍边的几个男孩,拿着枕套琢磨着是哪家的东西,互相询问着。有个比我大一岁的男孩,叫小利子。说话结巴。问到他时,很有自信地说:“不不、、、不是我家的。”一会儿看看,又说:“我看着有、、、点眼熟。”一边的我,脑子飞快地转:怎么办?是拿着枕套各家去问,然后赔给他们呢?可怎么赔呢?我妈一定骂我。要不跟那家人好好说说,说不定是个好说话的,不让我赔。几个孩子后来决定拿着枕套挨家去问,我跟在后面。问了几家都说不是。到了小利子家,他妈妈一开门,见到枕套突然大叫起来。吓得我头也不回地跑回家。跟妈妈什么都没有说。都说小利妈妈是有精神病的。后来听说到小利妈拿着被炸破的枕套到处大声抱怨。她没有来我家找,看起来没人告诉她是我干的,她也想不到是个女孩子吧?
还有一种叫“二踢脚”,一个个比拇指粗,半尺长。我也敢拿着放。用手小心地捏住上端,点着下端的小捻,垂直地对着空旷的地方。下面一个炮从下面爆炸,火力冲向地下,上面的一个炮仗冲向天空,在空中炸响。有两响,声音比小鞭大得多。
我家住的是爸爸厂里的宿舍院。有三十几户住家。从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初出生的孩子,也有不下三十个。不知道是从那年开始的。孩子们有了除夕聚会守岁的习惯。一直到七六年地震后厂里盖了新的宿舍楼,院里的人都搬了家。每年年三十,我们这一群年龄相仿的十几个孩子,就会聚在一起,玩一个通宵。
我们几个女孩子,正值豆蔻年华。那天傍晚,就都不约而同地打扮起来。先洗头,洗脸。脸上涂了雪花膏,头发梳得别致好看。再换上自己喜欢的衣服。聚在一起时,一个个看上去都唇红齿白的,非常好看。一个大几岁的男孩子自豪地说:“咱们院里的女孩子,个个都这么漂亮。”
我们纷纷从各家拿来些吃的东西,花生瓜子,糖果点心,还有中国红葡萄酒和汽水等饮料。聚在一个人的家里,就吃喝说笑唱歌。比我们年龄大的那一群,二十岁左右小伙子姑娘们,也会来串门。喜欢热闹的大人们,也会来看看。到了夜里十二点,家家人都出来放鞭炮。放过鞭炮之后,大家又到各家串门拜年。然后又回来玩。后来我们的聚会有了一个固定的地方,李叔叔家。他的妻子和儿子在乡下,而他常年都在外面出差。他的家就成了公用场所。那年我发起,要每个人都要做一个菜。于是就在炉子上座上一支铁锅,又从家里拿来了材料,会做菜的人,基本上是女孩儿,就各自炒上一个菜。喝酒吃菜的时候,就又多了一个节目,评比谁的菜最好吃。记得第一年我做的甜酸肉就得了头奖。这顿饭吃得很长,吃的时候,每个人都出点节目,讲故事的讲故事,说笑话的说笑话。大家还一起唱歌,唱《红莓花儿开》,《山楂树》,《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那个年代,不论在学校,还是在家,男孩和女孩之间的社交基本上是禁止的。唯有年除夕这一天,各家的家长对我们特别宽松 。十几岁的少男少女们,聚到一起,都焕发出了生命的美丽。笑语欢笑之间,是那么纯洁,正气。女孩子们一夜之间,似乎 都变成了淑女,长大了。平时显得粗鄙淘气的男孩子们,也变成了绅士,个个都那么诙谐幽默,彬彬有礼。
大年初一的曙光出现,疲倦的孩子们知道该散了。心情有点不舍,灰灰地就像朦胧的天光。这时,几家的妈妈纷纷又把煮好了饺子端过来,大家分着吃了才散。不久,就又三三两两地搭伴去厂里礼堂看电影去了。
年初一,不约而同地成了拜年日。大人们开始忙着出门的出门,迎客的迎客。人们出出进进地,象走马灯一般。除了邻里之间的拜年。其它地方住的同事也陆续来了。大人们的社交,政治因素多了些。兴趣相投的人们先来了。他们多是老朋友,一起参加革命,一起工作。曾经是一个组织,一个派的人,见面时自然笑容多些,悄悄话也多些。再有就是有目的的人来了。他们可能曾经是你的对立面,但风候变了,想修好关系。在下一轮的运动中不至于为敌,或许有希望成为同一个战壕的战友。甚至连敌人都来了。带头斗争我父亲的人,曾经来抄我家的人。形势变了以后也会来,皮笑肉不笑地寒暄着,尴尬地笑着。也有真诚的。我妈妈在运动初期,被她厂里的造反派抓起来敲锣打鼓地游了通街,又就手送去了北京第二监狱。监狱的人不敢不收。结果妈妈就莫名其妙地住了六十多天的监狱。后来妈妈被平反,抓她的造反派反过来对她表示歉意。过年还特意请妈妈和我到他们家里做客,做上宾招待。
可以这样说,初一拜年谁来了,谁没来,就预示着新的一年里的政治局势、事态和人事组合。
也不全是如此。那年我还小。文革中斗争比较激烈,形势变化得很快,父亲被斗得紧。过年家里很冷清。突然,有一个军人带着一家人来看望我们。父亲高兴得什么似的。这个人就是邬伯伯。他当时是中央警卫局的副局长。跟父亲其实只是以前在工作上有来往。父亲是个新闻电影记者。他拍摄过很多中央领导的工作、会议以及外事活动的影片,拍摄工作都在中央警卫局的指挥下进行。邬伯伯是个好交际,开朗又善良的人。他来我家,不会从我们这里得到任何政治上的利益。只能是出于和父亲在工作中建立起了友谊。而他的到来,给在政治的压力下不得喘息的父亲一个很大的安慰。我也很高兴。邬伯伯的女儿比我大一点,性格很温顺随和。他的儿子大我三、四岁,相貌英俊,举止稳重。我心里对他有了一种朦胧的好感。邬伯伯和阿姨好像都很喜欢我。后来又邀请我们到他们家去。后来的那些年,我们都有断断续续的来往。那个哥哥后来参了军,我曾经希望过,长大嫁给哥哥那样的英俊的解放军。这可以说是我的一种朦胧的初恋吧。
现在的孩子们有福多了。如今过年的内容如此丰富。不说春节联欢晚会。很多传统的花样又回来了,比如红包里的压岁钱,赶庙会什么的。吃的,玩的,都不知有多少。可惜我享受不到了,只能远远地看着。
原来以为是因为共产主义运动使中国人试图放弃传统文化,废弃旧习俗。出国以后不久,在新年时读《星岛日报》,读到一篇《春节感言》,其中谈到辛亥革命后,当局曾把西历定为国历,强迫人们庆祝元旦,在农历元旦却命令人们照常工作。而百姓却照样庆祝农历元旦不误。迫使当局不得不有允许人们在农历新年放假。可见中国的传统根基很深。
以前还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春节只有在中国庆祝。出来才知道,全世界有亚洲人的地方都过中国的新年。原来春节还是一个世界性的节日呢。
2009年1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