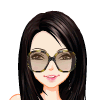(2)
自然喽,钱百山还未告诉古娥真甚麽。他也走进个人的命运旋涡里无法抽拔弄出来吧,古娥真想。而古娥真呢,整个心思仍然走进那年。那年,贾宝雄搞掂她惟一护身符出国护照,但没有没有钞票。(都是奉献的爱胡塗,牺牲得胡塗,甚麽都没有扯平。都是意气用事的胡塗,迎接突然而来的阿公丧事,心被扯碎…肚里的血肉扯碎。…)她想著那年拿著祖父的遗书去县城拜会任式弼。
麵包车车子出了坍塌的古墟老城门。车子很快就跑上公路,在公路上颠簸前进。刚下过一场滂沱大雨,黄泥公路很泥泞。泥浆从车轮两边击射路边的含羞草。含羞草遭遇强烈的射击,像触动了天性里的小精灵,草叶掌神经质地收拢痿缩。麵包车突然一个大弹跳,古娥真上身撞到了前面的椅背。一阵痛楚直透心田,本能的反应令她抓住輭皮靠背。她惊慌的望著风中摇舞的含羞草,但目光毫无著力的被凤尾草挡驾了。大雨後的海湾明媚,但空大无涯,令目光没有投射之处,就像记忆的图谱,铺天盖地的映现眼前,而心灵之镜却像痿缩的凤尾草,给泥浆塗抹了。任式弼是本县街知巷闻的大人物,阿公生前从未说过,临终前怎会留下这封遗书给她呢?…她被阿公的遗书弄得晕头转向。
她双眼望向随车退後的黄泥路和荒芜的田野,很快就把海湾风光抛离。迎面衝来连绵不断的山野景象,车将要进河川山路了。出了河川就是梅岭尽头。梅岭河川几多里?连绵的山川山峰到了梅岭之北,出了雷公山险峻的山岬,就车就朝县城进发,再行个把钟就望见县城大地。…车子驶过跨河的山川石墩桥。她把脸仰起,眺望山口。再没有更熟悉的山川峡谷。桥下流水湍急,车子盘著山壁绕过九曲十叁弯。闭住双眼都能感觉四野的山石草木。车轮在山路上蹬踬前进,弹射一路的山花、含羞草,把她痿缩的心神撼碎如千百片,在空气中飞腾,追逐山野。她恍然如在睡梦中醒来,感觉自己像个婴儿,裸裎著身体与车共同奔驰奔驰。但心灵充满抗争和矛盾,让两颗晶莹的泪珠迷糊了。她不想让同车进城的人看出自己的狼狈相,祇好假装入睡。她把脸重新转到蒙盖泥浆的车窗玻璃,眼光透过车窗,勿论车怎样颠簸,都能穿透摇舞的草野,黄泥弹射像玩弄自己摇舞的心情。记忆的图谱朝清晰的故乡山野映照,随祖父逝世团团转。她听到了小学毕业时阿公教唱的《蝶恋花.闺秀情》,在石墩桥的山野飞扬:
年年月月杨柳枝,无布裁衣,姑娘问羞情。
朝阳初照竹簾疏,红巾遮脸想人亲。
井边阿娥学打水,花枝摇波,惹来双燕飞。
人沾清波谁来看?愁望夕照剪平川。
连绵不断的梅岭有个神秘的传说。那年听阿公吟唱。是阿公教的。後来我在图书馆读到《山鬼》,就被山鬼迷惑了。我打诞生起就接受阿公启蒙,以为自己聪敏过人。每天下课後,跟外婆牵手回家,阿婆爱说说唱唱。屈原说「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後来」。但我仍然在梦醒之後想像未来。因为现实的我无赤豹乘骑,山鬼毕竟是屈原给我的浪漫梦想;就算我真的乘骑赤豹,我怎也不能摇桂旗遊戏神秘缥缈的汪洋。於是我也只能梦想海洋,心灵也像渔火在黑暗的海上明灭不定。
那片浩瀚汪洋,很早就有人横渡了。从前有郑和七下西洋。他
的航行历史一直流传我们家乡。郑和虽然不是我梅岭人,但他的故
事跟家乡传说的关係密切。杨柳河由梅岭发源,自古有许多神话故
事。我国第一个伟大女英雄女祸,会炼彩石补苍天。我竟幻想她双脚
跨过梅岭。阿婆说我就是诞生於山海间的小精灵。是吗?假如我是
山海间精灵,也就如神仙化身了。我一直渴望能在睡梦中与山鬼相逢
,跟她一道骑赤豹,去探看梅岭发源的山泉,然後跟她在石潭一齐
游泳。那是多麽奇妙的邂逅呢…於是我含笑由梦里醒来。
古娥真像从非常境界回来了。心坎里串连的山鬼故事,毋庸说是为拜会的女县长,心灵被命运的山鬼蛊惑了。山野在想像中寂静,远处的海湾也寂静无声,像把命运图谱奉还给心灵,回到行囊里的阿公遗书。如果说将要会晤的女县长是命运捉弄我,那麽阿婆之死隐瞒的秘密档案,就是我追踪生身之谜吧?她想。
记忆还是从石墩桥说起,阿婆说起岩洞的神祕传说。闭住双眼都能感觉爬过水洞的情景。爬过水洞出来,山洞朝著大海,把山水吐纳的就是杨柳河。跨过石墩桥,湍急山河喘急的下山。记忆停留在山泉深处的山川峡谷,然後才迎著湍急流水流去,奔进海湾渡头就消失无踪影。如果说幼嫩心田种下的梦想根源於石桥墩,流水如切肤之亲,那麽神祕的山鬼传说,令我体会了童年心事的沉重,使我身心过早成熟,也许是。…人家把阿婆埋葬在梅岭石墩桥上面的山洞,是有因缘的,想来也是命运的奇妙点缀…
她想起十六岁。也就是由梅岭县城选美夺冠,等待去省城。她和祖母来过石桥墩,然後爬上山樑。她无法形容心灵的喜悦,也无法理解祖母为甚麽陪她来石桥墩,来访神仙洞。从山洞出来,但见祖父坐在盘石上,正襟危坐,他双手紧握他的杨梅手杖,望著桥墩下湍急的流水癡癡呆呆。原来阿公早就在此守望她和阿婆。望著阿公如山样的凝坐姿态,阳光照亮他一身灰白的中山装,望他手扶手杖的神情,总觉得他像个老革命,身上有说不完的故事。眺望山野,山谷寂静,远处的海波也寂静。阳光打洞外映进来,他手掌里的手杖在天光下发光。
很小很小听到阿公说山鬼故事,阿公也讲过他自己。他说参加过革命,做地下工作。阿公说莆北小学是白沙湾文化摇篮。爸妈是谁呢?为甚麽我祇有阿公阿婆?我问过阿公。阿公爱妳吗?阿公问,我点头。阿公您说爸妈在哪?我忍不住又问。阿公沉默无言良久良久。妳妈是革命精灵,妳是山鬼,阿公打破沉默说:妳长大了,总会知道母亲是谁。阿公真像编说故事,但我知他不是故意编说。阿公无再说甚麽,平静的举起手上手杖指著山川。
我和阿婆来到石桥墩,仨人排坐石桥墩。山谷风细悠悠,像绵绵密密的幽音细诉,令我陶醉。但见阿公扶杖的样子,无语凝望山下河涌。我双眼随他的神色越出山野,瞳子映进山下风景。桥下风吹草动,花枝随风款摆摇舞,恍然似万千花朵映进心灵,映照蓝天白云。我看著阿公悠悠然吟唱起来,空气中流漾起伏有致的抑扬顿挫——
孤舟飘蓬万里行,
浪涛飞捲雨霏霏。
天若有情天知地,
我独守望山海心。
天地问我为谁愁?
孤舟遥幌万里情。
阿公为何选择神山洞了决生命?不是谜也像谜。…在墓地盘坐,阳光照不到的岩石阴影,我突然感觉心慌,惊动了记忆图谱,似把未来交给大海,让海涛偷偷洗涤。乍然,我望到一只山鬼如豹,从山洞的阴影处眺望山海。我知道是幻觉而已。太阳快落山了,阳光打梅岭那边射过来。我想像千百只海鸥在沙滩上翱翱翔翔,汹湧澎湃的浪涛,切割层层叠叠的金波,遥远海上帆影点点零散。海鸥啼声会随傍晚夕照慢慢消声匿迹,海岸沙滩祇能听浪涛衝天如雷。遥远的渔火零落也遥远。夜在天涯海角降临,满天星斗在天壁闪烁如亿万精灵。天地会告诉我的,山鬼是我吗?我想。我心灵渡进深壑的海里,我同山海有缘。我心灵还追随阿婆喃喃唱的歌谣飞翔。飞越童年多少路呢?阿婆重複多少遍这首歌谣呢呢?
风呀浪呀啪呀啪,
渔火如星点点,
随波涛飘也飘,
点点渔火下西洋,
下西洋下西洋,
一去不知返。(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