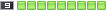老 屋
文 / 齐凤池
推开栅栏,屋檐上的瓦松又长高了许多,儿时在上嬉戏的那块青石依然卧门旁。门虚掩着,父亲没在家,大概又去北山了。
我推开那扇用旧铁皮堵着漏洞的屋门,迈进那已像张弓的门槛,一缕光柱透过屋顶伸到地面,墙上又多了几道雨水淌过的痕迹。说老屋已千疮百孔,饱经沧桑并不是夸张。
因急于赶路,我有些累了。于是躺在散发芳香的土炕上,头倚着那个裹过我童年的发卷,好温馨!那粗布被面贴在脸上好柔软好舒适,这是妈妈亲手织的!蓦地,我的心猛地一颤。手印,墙上那个手印又把我拽进了童年。
在我的记忆中,妈妈总是弓着瘦弱的身子不停地咳着。晚上,妈妈在昏暗的油灯下吃力地摇着纺车,我在一旁搓着棉卷,那雪白的棉卷像春蚕一样快速地吐着丝线。纺累了,她就坐在炕上,眯着眼睛,一边缝补衣裳,一边给我讲着“凿壁偷光”的故事。三个哥哥趴在炕沿上捏着铅笔头,在用过几遍、被橡皮擦出小洞的本上写着作业。爸爸的头刚沾上枕头,就已鼾声如雷了。
妈妈急促的咳声把我从美梦中惊醒。妈妈已咳成一团,脖上的青筋似乎就要崩裂,她用枕头用力地堵住嘴,恐怕吵醒劳累一天的爸爸。她从枕边摸出半截白薯,狠劲地咬上一口,用力地压下去。夜又恢复了宁静,此时妈妈的额头上已淌下了汗珠,喉咙里还费劲地拉着“胡弦儿”。
每当秋末,妈妈总是满脸愁云,因为分的那点粮食是顶不到来年再分粮的。为了不断顿儿,能接上茬儿,我家只好一日两餐,每餐的粮食都星星点点,哥哥们放学后总要带上我去挖野菜。每次吃饭,妈妈都是等我们吃完再吃。她的病情越发严重,咳出的痰中竟带有血丝。“鸡蛋别卖了,补补身子吧!”爸爸心疼地说。“孩子们又该交学费了。”妈妈说。
粮食对于我家已贵如黄金。愁吃少穿的日子,累得爸爸常常在家大发雷霆,他真希望有个帮手。“以后谁也不准再上学,都给我下地挣分儿!”爸爸怒吼着撕碎了哥哥的书,并把书包抛进灶膛。哥哥们都吓哭了,妈妈没有作声,她心里知道爸爸是累的,只是低着头捡着地上的碎片。吃过晚饭,妈妈把那些碎片精心地对着、粘着,又把盖住的文字细心地抄好,泪水一滴滴落在书上。
我也上学了,妈妈从箱底拿出多年积攒起来的布头,为我连夜拼凑了一个五颜六色的书包,并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你要好好上学呀!将来也好有个饭碗……妈的日子不多了……”从她噙着泪水的目光中,我知道了她的病已到了晚期。
大年那天,太阳躲进了云层,家家都忙着过节。妈妈也格外高兴,早早起来,把老屋里外上下收拾得干干净净。嘴里不时地哼着小调,根本看不出她已是一个肺癌晚期的人。紫红的板柜光亮可鉴,雪白的窗纸贴上了窗花……到处充满了过年的气氛。一年总算熬到了头,该让父子们吃顿饱饭了。妈妈边想着,边打开柜子,从那个系得紧紧的布袋里舀出两瓢秫米,准备做米饭。老屋里吐出腾腾的热气,时而传出清脆的叮当声。老屋里已弥漫出浓浓的饭香。“他们父子也该回来了。”妈妈倚着门框期盼着。突然,一阵剧烈的咳嗽,震得老屋摇晃,一股无法控制的热流从母亲胸中涌出,鲜血顺着指缝钻出来,染红了那满是青筋的手。她下意识地用手扶住墙,手印鲜红地印在了墙上。
蒸气汇成泪滴顺着屋梁淌下来,老屋哭了,哭得那样伤心……
“满仓回来啦?”爸爸亲热的问话把我从悲痛中拉了出来。只见爸爸满身灰尘,衣服上扎满草刺,黑瘦的脸上又增添了几道皱纹,稀疏的白发间挂着汗珠。“渴了吧?我给你烧点水。”爸爸关切地说。“不用了,”我边说着,边摘去爸爸身上的柴草。那架老风箱又咕嗒、咕嗒地唱起那首老曲,火苗舔着锅底,水沸腾了。
几声鹊叫从院心传来,我抬头向那棵老槐树望去,一只喜鹊正衔着树枝修补着那个老窝。小鹊早已出窝了,树杈上只剩下那只老鹊和那孤零零的老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