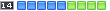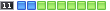浩 劫 逃 生 記
Hao Jie Tao Sheng Ji
曾庆斯
前言
這本書所寫的,是我於20世紀中後期在中國的真實經歷。
我生於1936年,父親是醫生,母親是助産士。他們畢生兢兢業業,救死扶傷,醫德醫品在服務過的地區留下了良好口碑。我自幼耳濡目染,立志獻身醫學事業。1954年我考上北京(大學)醫學院醫療系,畢業後,作為師資留校進修一年,1960年分配到昆明醫學院當助教。那時正值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大饑荒,物質條件極其惡劣,作爲醫學院的教師,仍然免不了餓到營養不良性水腫。但我仍然滿腔熱情地投入工作,作出成績,獲得好評。我性格內向,不善交際,但對人友善,與同事和睦相處。我對政治不感興趣,不入團入黨,被認為是“重專輕紅”的落後份子。
“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因宗教信仰、海外關係,及“重專輕紅”的背景,橫遭迫害,受到自上而下組織的、全學院範圍的大字報圍攻,批鬥抄家,隨後更被勒令“只許規規矩矩,不准亂說亂動”——這種對所謂“階級敵人”的指令。在極度精神壓力下,我被迫鋌而走險,溜回廣州老家兩次逃港,均被抓回。當時廣東逃港司空見慣,我假報姓名地址,在人滿為患的收容所裡,飽受饑餓、疾病折磨,更日夜提心吊膽怕暴露身份被押解回昆明。幸得家人親友大力營救,得以矇混過關。由於我在廣州是外來人口,面對一波波的查戶口,掃“盲流”,家人親友愛莫能助,逼得我東躲西藏。1968年是“文化大革命”最瘋狂的一年,兩派武鬥白熱化,“清理階級隊伍”濫打濫殺。這時昆明醫學院以軍宣隊為首的“革命委員會”派出打手到廣州抓我,在緊急關頭,我拼死一搏逃往越南北方,在農村及山區流亡達七年之久。我無親無故,不懂越語,不但要為每天食宿發愁,更要日夜提防越南公安,吃百家飯,夜宿山野是常事,多次經歷九死一生的險境。幸得華人同胞同情照顧,多方掩護,化解重重困難,我亦盡力為他們治病服務,彼此建立了魚水般的深厚情誼。1975年,在友人建議和幫助下,我向越南當局申請暫時居留。期間曾兩次被要求將申請暫時居留改為“入越南籍”,我沒有改,最後申請沒獲批准,被遣送回國。輾轉經歷幾個收容所,我回到昆明醫學院,經過一段時間勞動和審查,恢復工作,但仍然處於“內部控制”狀態。
其時,家人在美國申請我移民獲准。但我申請護照被諸多阻難,足足拖延了三年,幾經曲折和努力,終於於1983年底得以移居美國。從此不會因宗教信仰受迫害,不會被意識形態所扭曲,多好!一切從頭開始,我和妻子經過二三年打拼,重新投入我們所喜愛的醫學事業。我通過醫師考試(ECFMG)後,參加醫學研究及實驗室工作,曾取得兩項美國專利。我對中醫素来感興趣,其後再考取中醫針灸執照,分出一半時間自己開診所,結合中西醫知識指導臨床實践,覺得很有意思。72歲全面退休。
回想那曠古浩劫年代,無數同胞慘遭荼毒,千萬家庭都有不堪回首的傷心史,隨着歲月流逝及被刻意掩飾而逐漸被淡忘。為了不讓歷史流失,不少過來人陸續寫出回憶錄,讓年青一代瞭解歷史真相,領悟國家民族悲劇的根源,為制止災難重演作出努力。
我只是一介平民,我的遭遇比起數以百萬計含恨九泉的亡靈,可說是微不足道。但我想:滔滔江河,源於水滴,我有必要把經歷寫下來,并希望有更多人寫出真實往事,為歷史提供活的見證。
我缺乏文學才能,只會照事直敘,幸得親友鼓勵幫助,勉力寫成這本小書。書中涉及的一些人,不便用真名。往事的一些細節及時間,記憶難免有錯漏。不當之處,誠請讀者包涵指正。
目 錄
我的家世
禍從天降——“文化大革命”
背水一戰逃港
越北逃亡歲月
重返祖國
移民來美,開始新的篇章
我的家世
家庭出身
我的家鄉在廣東省興寧縣(後改爲市)。興寧地處粵東,鄰近福建、江西,山多田少,交通不便。居民主要爲客家,是自晉朝起不同時期從中原南遷的漢人,以刻苦耐勞著稱。爲求發展和出路,很重視教育,所以説興寧有“三多”:教師多,醫師多,軍官多。1949年以前,幾乎每個區、鎮都有中學;僅興寧縣城鎮,大學醫學院畢業的醫師就有十多位;全縣出過不少師、軍級軍官。平民百姓大批出外謀生,多到廣州、上海;近的到江西,福建,遠的到東南亞等地。
我們曾姓在興寧縣不算大族,我祖父不是有權勢的人,但有一定名氣,擔任縣商會的常務幹事。他熱心公益,為地方做過不少善事。
那年代,窮人家的孩子難得受教育。我祖父聯絡本族鄉紳,創建了新式小學徳新學校,學費低廉,窮家孩子還有減免。教師都是有真才實學的人,教學質量高,在縣內頗有名氣,所以直到現在仍然保留“德新學校”的名稱,常有國內外校友捐款支持。我的伯父、父親,及一位當中學老師的堂叔,都爲德新學校傾注了不少心血,伯父曾擔任校長多年。
1930年代,興寧還沒有醫院,人們看病找私人西醫或中醫,或民間中草醫。祖父聯絡縣裡有名人士,取得政府支持,於1938年興建了興寧縣民衆醫院,以西醫爲主,兼有中醫,為平民百姓廉價治病。從發起、籌資、規劃、選址到動工興建,祖父都親力親為,後期並得到我父親的大力協助。記得祖父說過,當時選址在寧江對岸,他幾次走過搖搖晃晃的兩塊木板的小橋,還真害怕掉下河去。
每年青黃不接的“四月荒”,是窮苦農民的難關。商人圖利,在收穫季節低價收購糧食,四月荒高價賣出。祖父有見及此,聯絡縣裏熱心人士,建立“惠繼義倉”,祖父被委任爲主任。惠繼義倉將收穫季節買入的穀物,儲存至四月荒時平價賣出;又於每天中午設施粥站,赈濟災民,獲得廣泛的好評和擁戴。
1940年冬,日寇攻到離興寧城百里外的“猴子棟”地方,中國軍民奮勇抵抗,戰役非常慘烈,最後反敗爲勝。一支抗日軍隊借駐惠繼義倉倉庫,裝備簡陋,衣被單薄,夜裏凍得直呻吟。我祖父囑咐倉庫管理員,把破舊待修的蔴袋借給那些兵士禦寒。部隊調動時,那些兵士央求把蔴袋留給他們。由於是公物,我祖父聯同另一位鄉紳,出錢買下那批蔴袋,贈送給那些士兵。
祖父留下的唯一照片,自台灣三叔處得來,聖誕樹飾是三叔加上去的
祖父是虔誠的天主教徒,性格善良,整天笑容滿面,我從來沒有見過他發脾氣,大不了只是喃喃抱怨一陣。他同情窮苦人家,樂善好施,爲我們立下表率。他愛我們,經常關心我們。一次我找到他,興高采烈地對他說:“啊!阿公,你倒楣了,倒楣了,又給我考了第一,你又要給我兩塊錢了。”他不以爲忤,反而覺得童言天真,高興得逢人便說。
祖父重視子女教育。我父親高中畢業後,祖父希望他讀醫,說可以幫助很多人。在教會推薦下,我父親考進上海震旦大學醫學院(上海第二醫學院前身)。震旦大學是一個由法國人主辦的大學,用法語教學,醫學院按法國規制讀七年。父親畢業後在著名的上海廣慈醫院做醫生。
父親讀大學時,通過親友介紹,認識了我母親并結婚。我外公的家在山區,我母親小學畢業成績考第一,由於當地重男輕女傳統習俗,外祖父不想讓她到鎮上繼續讀中學。但我母親知道,只要她能讀上第一年,並且成績優秀,外祖父母就有可能讓她讀下去,於是她預先兩年就結伴去茶山採茶積錢。同伴在茶山分散各處,自己孤伶伶一個人,聽見風吹草動都會疑神疑鬼,突然的響聲還會嚇得她驚叫。她終於積夠錢,考上中學自行交了第一學期學費,期終考試又是第一。外祖父母見她志氣可嘉,就繼續供她讀到初中畢業。畢業後不久,兩家為我父母籌備婚禮,母親與父親商量,與其將錢花在婚禮上,不如央求我祖父將錢省給她,隨夫去上海,入讀助産學校,學得一技之長。我祖父是很開明的人,居然完全同意,並且通告諸親友。由於我祖父在當地有名氣,婚禮開支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夠不夠三年學費不得而知,不管怎樣,我母親得如願讀到畢業。隨後在上海母心醫院當助産士。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軍進攻上海,父親帶著腹中懷著弟弟的母親,和一歲半的我,逃難回到家鄉興寧縣。父親先是開診所,母親任助手。不久,父親被聘爲縣民衆醫院首任院長,母親當助産士。
兩年後,醫院各方面基本上了軌道,我父親不想在行政工作上花很多時間,於是和母親一起辭去醫院職務,自己重新開診所,在興寧頗有名氣。
父親不善逢迎,交往的多是知識分子和平民百姓。他也像我祖父一樣,特別照顧貧困病人,我曾幾次聽他說過:“同是一塊錢,對富人沒什麽,對窮人可不容易啊!” 父親做事,按部就班、不疾不徐。母親的理念跟父親一致,但較急性,說做就做,敢於承當。她常常笑父親“屁股打三棍還放不出一個屁來”。
那年代是抗戰艱難時期,我留下的印象,一是走警報躲避日本飛機轟炸;一是看見一波一波的難民潮——從潮汕等地逃來的難民;再有是我們自己逃難:1940年日寇攻到離興寧城百里外,父母領著我們逃避到山區的外婆家,我和弟弟坐竹籮,一人一頭,請人挑著去。在崎岖的山徑上,望着深深的山溝,心裏直發怵。後來日寇進攻被擊退,我們又回到城裏。
父親不參與政治,但富於正義感,他痛恨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聯同一批志同道合的知識分子,創辦了《天下報》,被推舉為社長。主筆撰寫時事述評的是我同祖屋的堂叔,後來担任遷臺灣國民黨中央日報總編輯的曾憲宦。《天下報》與縣裏其它報紙一道宣揚鼓舞抗日,在知識分子圈中影響不小。抗戰勝利後,繼續發表持平言論,針砭時弊,曾被中共地下工作者誤認為是“黨的地下刊物”。內戰興起後,父親和有關人員感到繼續辦下去有很多困難,才決定停刊。
我的童年
我六歲(1942年)上小學。城裏怕日本飛機轟炸,我和二弟是在鄉間祖屋附近的德新學校上的。
1945年抗戰勝利,我九歲。當時我們住在鄉下,一天夜裏,突然有人狂敲祖屋大門,大聲叫嚷,屋裏的人都被嚇著,後來才聽清楚是“日本投降了!”全屋男女老少一百多人立即沸騰起來,大喊大叫,敲臉盆敲水桶,隨後找出的鑼鼓也幾乎敲破了。有人馬上趕到兩里外的洋里搶購鞭炮,有人跑進城去打聽消息和搶購報紙號外。
以後,我們轉到城裏繼續上學。那時興寧縣城新成立一所小學:“福育小學”,是閩南商人在興寧的福建同鄉會創立的,招收他們的子弟及當地學生,經費充足,學費也較貴。師資有福建來的,也有具備師範學歷的當地人。上課用普通話——當時叫“國語”,而不是用當地的客家話。學生統一穿淺藍色制服。老師引導學生與社會接觸,如參觀電話局,發電廠,織造厰,小型蔬果農場;以及舉辦文藝表演。這些創舉有別於其它學校,社會反響良好,興寧縣比較有錢的家庭,包括多數醫生,都把子女送到那學校去。我和二弟及大妹都先後在那裏就讀。
我兩歲和二弟一歲時的合照。我們所有的照片在“文化大革命”時都被抄家毀去,這張是姑姑保存下來翻照的
福育小學對我影響很大,特別是鄧治馨校長,他身材高挑,文靜慈祥,學識淵博,是全校老師的表率,也深受學生家長的敬重。他鼓勵我們多看課外書,在他引導下,我從一個整天愛玩的小孩,轉變爲既愛玩也喜歡讀書的好學生。鄧校長教我訂兒童雜誌,第一次是他幫我寫好訂單,我去郵局訂,我的頭剛剛高出櫃台。以後我就自己接續訂了當時幾乎全國的兒童雜誌:《福幼報》,《兒童世界》,《新兒童世界》,《兒童故事》,《中華少年》,以及杭州的《中國少年兒童時報》,香港的《新兒童》。學校買了一套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新小學文庫》,一共二百本。鄧校長看我喜歡讀,還沒有編好書目便先讓我借。爸爸知道了,便說也可以給我買一套,因為弟妹們都可以讀。但要我自己去郵局訂(爸爸從小就鼓勵我獨立行事),不久書寄來了,鄧校長也為我高興。我每次放學回家,都先到書店看看,那時在我父親診所的那條街就有四家書店,看到有好的書,就回家央求父母給錢買下。
鄧校長告訴我們,抗戰時他作過宣傳員,到前線宣傳鼓舞抗日,有幾次遭日本兵追趕,子彈擦身飛過,炸彈近處爆炸。聽得我們肅然起敬,在幼小心靈裡,覺得鄧校長是個抗日英雄。
福育小學發展很快,我畢業後不久,就在原址重新蓋了很漂亮的兩層樓校舍。可惜一年後就“解放”了,校董事們在他們家鄉被劃爲地主或資本家,受到徹底清算。學校經費無以爲繼,唯有倉促結束,發不出遣散費,教師回去的旅費都成問題。老師們不得已,組織了一場告別表演晚會,向學生家長募捐,不料被新政府的有關部門指控爲“詐財”,落得狼狽離開興寧。福育小學猶如曇花一現,消失於無形,令人惋惜不已。後來我偶然機會聽到:鄧校長回去後,因抗戰時作過國民黨宣傳員的“罪名”,受到整肅,不知所終,令人不勝唏噓和懷念。
宗教浸潤
我祖父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大力協助教會,選址郊區興建了興寧天主教堂,棣屬嘉應(梅州)教區。堂區佔地很大,除了可容幾百人的教堂外,還有節慶日接待各地教友的宿舍和大飯廳,以及一個大花園,教堂後面是“聖山”——教堂墓園。我記得的神父有兩位,一位是馬來(西)亞華人,姓歐,除了拉丁文,英文也很流利;另一位是鄰縣人,姓廖,拉丁文、英文也很棒,曾譯過幾本書出版。附屬女修院有二位美國修女,協助傳教及教小孩學教理。我們喜歡聽聖經故事,輪流做輔祭員,參加各種活動,其中一項是“做好事”:聽父母老師的話,幫做家務,幫助他人等。每做一次,就剪一小截禾桿放入火柴盒,每週交給修女。那些禾稈集中起來作為聖誕節佈景耶穌聖嬰馬槽的鋪墊。修院有一個小圖書館,常從香港購進書籍,我很喜歡去借故事書來讀,新書一到,我總是第一個讀者。中共建政後,神父被捉去勞改,歐神父及本教區的有些神父死於勞改營,美國修女被驅逐出境,教堂被沒收作區政府辦公地。
我母親原來隨家庭信奉佛教,和父親結婚後,漸漸認識了天主教。但她不是夫唱婦隨盲目跟著信,而是看了不少書籍,與佛教及其它宗教作研究比較,最後才轉信天主教。正因爲如此,她的信仰非常堅定,多年後共産政權的宗教事務處找她談話時,她敢與他們公開辯論,互相引用科學和天文地理知識。對方理屈詞窮,只好說:你陳XX思想真頑固呀!1950年代當局掃蕩宗教,她有幾次被宗教事務處“請”去學習。文化大革命期間,她兩次被拉去石室(廣州的大教堂)批鬥。母親懷第七胎時,向天父許願:“感謝天主,我已有兩個兒子,四個女兒,這第七個要獻給天主。如果天主願意,男的就讓他當神父,女的當修女”。第七個是男孩,後來三弟慶導通過自己的認知,努力,挫折,堅定,果然成了一個好神父。
在母親及神父的引導下,我讀了《科學家的宗教觀》,《科學與宗教》等書籍。前者指出,百分之九十的大科學家如牛頓、巴斯德、居里夫人、愛因斯坦等都有明確的宗教信仰。後者談了大自然的種種奇妙:宇宙,地球,特別是生物的奧秘,井然有序的運行規律,如果沒有一個超自然的力量在設計、管理,就像一隻小貓說大廳的音樂報時鐘是“自然就有的”一樣無稽。後來我讀醫學,深入瞭解人體及生物的奇妙,例如,比起眼睛的功能和調節機制,哪怕最精密巧妙的照相機,也不過是笨拙的小孩玩具;最簡單的一個病毒,以它的基因組成和自我複制 就比最複雜的航天器械還要高明千百倍。種種事實令我信服神的偉大,儘管就像小貓沒法理解人的思維,人也沒法完全認識神的奧秘一樣。
由於父母、祖父母敬天愛人,扶貧濟困的表率,也由於我自己在成長過程中的思考體會,宗教信仰逐漸深入我心。我很慶幸和感謝父母和祖父母引導我確立了宗教信仰,使我以後遭遇到難以想像的困難時,在絕望中看到希望,並且出現一次又一次的奇蹟。
“解放了”!
我上初中一年級不久,共産黨來了。剛“解放”,看見男女解放軍在街頭宣傳表演,扭秧歌,打腰鼓,和老百姓有說有笑,跟國民黨警察那種暮氣和霸氣大不相同,我覺得很新鮮,在幼小的心靈裡産生了好感。學校上課以後,氣氛也很活躍。學生會競選主席,各競選團隊演說,表演,貼標語,很熱鬧,覺得真是民主。我還讀了不少新書,如《小二黑結婚》,《李家莊的變遷》,《李有才板話》,《社會發展簡史》,《長征故事》等等。總之,那時我心目中,一切都是新鮮的,前進的,充滿活力。
但氣氛很快發生變化。不到一年時間,先是“鎮壓反革命”運動迅猛開展,沒隔幾天就看見綁著人去槍斃,一個同學的叔父被槍斃了,原來的中學校長也被槍斃了。有一次,學校集隊去看宣判一個家族反革命集團“武軍”,被押上台的二十五人全遭槍斃,其中幾個看起來還是小孩,名單上寫的都是18歲,罪名只有四個字:“包庇武軍”。接著,每天中午放學吃午飯的時候,都會見到在縣人民政府左側的監獄門口,押一批人上車,拉到各鄉鎮去槍斃。我的伯父早年從廣州警官學校畢業,後來被任命爲興寧縣警察局長,做了兩年,覺得與自己的志趣不合,辭職轉去當德新學校校長。那時也被捉去,判刑四年。一個國民黨時代的警察局長只判刑四年,算是異數。不過那時見到天天殺多少人,已把我祖父及家人嚇得半死。
我剛萌芽的新鮮和興奮感覺漸漸消失,開始覺得可怕。
土地改革
緊接着,1950年冬,興寧開始土地改革。初時,我們在老師帶領下,懷著莫大的興趣學習“土改法”,下鄉到山區去宣傳。那時山區還不大寧靜,政府發給帶隊老師一支手槍,但是我們還是熱情地挨家逐戶解釋土改法,組織歌舞表演,發動貧苦農民參加土改。隨後發現不少老師情緒低沉,說是家裏被劃了地主富農,要退賠很多錢。那時政府號召購買“勝利折實公債”,實際上是分派到各人頭上一定數額,從薪資中按月扣除。我們發現很多老師都愁眉苦臉。
我家被評爲自由職業兼小土地出租者,因爲父母親都是醫務人員,只有祖傳的很少一點田,土改後把田獻給政府,沒有受到直接衝擊。但我祖父被定爲“工商業兼地主”,其實他已七十多歲,既沒有工商業,也沒有多少田地了。他被拉回鄉下鬥過幾次,可能因爲人緣好,沒有受到太大折磨,但是要退賠。我祖父家裡能用的東西都被抄去一空,還一次一次來要錢,實際是看在我父親份上,由我父親拿出,最後我父母把新建的三層樓房賣掉,才算沒有再來。那樓房是我父母辛苦積累了十多年的錢建成的,正準備搬過去,樓下作診所,樓上當住家。不料一下子就成了泡影,父母傷心得直掉淚。
土改後农民分得了地主的土地和財物,曾經高興過一陣。但很快地政府號召“合作化”,把土地收回“集體所有”,組成“生產合作社”進行集體勞動。接著又實行“糧食(及其它產物)統購統銷”,農民交了“公糧”還要交“餘量”,所剩無幾,全國開始出現蕭條。最後更強迫農民加入“人民公社”,“大躍進”,種“高產田”,直接導致連續三年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這是後話。
1952年春,上頭(後來知道,是毛澤東及中南局書記陶鑄)指斥廣東土改“右傾”,“殺反革命太少”,指令“村村都要見紅(殺人)”(見《梅州文史》第十六辑,2003年),另派南下幹部來“補課”,大批當年出生入死打游擊的當地幹部,都被說成是“地方主義份子”撤職或投入監獄。所有地主富農都受到殘酷鬥爭:雙手反吊或綁住大拇指吊起來“蕩鞦韆”,口灌泥漿或糞水,火燒胡子,用繩子穿鼻當牛拉著遊行,把蛇放入褲襠等等,被當場鬥死的不計其數(參見《兴宁县志•大事记》1985年)。最激烈階段,差三隔五便會聽到這個同學或那個老師的家庭遭到變故。我有一個要好的同學,他父親少年時去南洋打工,積了一些錢回來買了幾畝田,也被劃爲地主。那同學因此失學了,有一次我們遇見,我關心地問起他父親,他臉一沉,馬上把頭轉過去,說“沒什麽,沒什麽。”語音梗咽小到聽不清,原來是被槍斃了。
縣裏所有較有名氣的人(“毛選”所謂“大大小小的‘蔣介石’”)都被羅織罪名,加以殺害。我那仁慈善良的祖父,因他在社會上尤其在教會裡的地位(所謂“帝國主義走狗”),也不能倖免。據說當時有農會代表委婉提出不殺我祖父,但被南下幹部粗暴否決。
祖父遇害幾乎令我父親精神崩潰,也使得我們無法在當地立足,每日處在哀傷和恐怖之中。那時正值“抗美援朝”,政府號召有大學醫學院畢業學歷的醫師參加“國防建設”,支援偏遠地區。我父親和另外兩位醫師參加了,三位都是當時興寧有名望的醫生,我父親悲憤之餘,決心永遠離開這個“心頭滴血”之地;其他兩位選擇離鄉背井,也各有苦衷。三人被分派到粵西的幾個縣份,我父親到信宜縣人民醫院。1953年,那時還有遷居自由,母親帶著我們七兄妹遷居廣州,要照顧七個小孩,沒有再去找工作。
遷居廣州 我考進北京醫學院
初到廣州,人地生疏,不會說廣州話,居住、轉學都遇到很大困難。教會的教友和神長雪中送炭,領著我們各處奔走,先後幫助我們找到房子安頓及幾個弟妹轉學。我由後來成為我妻子的玉鷗(化名)幫助聯繫,轉入市立第四中學,和她同班。
1954年高考,我決定學醫,做一個像父親一樣治病救人的醫生。我考入北京(大學)醫學院醫療系。我知道這是最後的專門學習機會,必須認真學好,以後才能爲病人服務。我對政治活動不感興趣,不參加團,也不靠攏黨,因此被視爲典型的“只專不紅”落後份子,倍受孤立冷眼。
共産黨的政策是“你不過問政治,政治要過問你”。1955-56年,毛澤東發動清算“胡風反黨集團”,接着導入“肅反”(肅清反革命)運動(1950年是鎮壓反革命——“鎮反”)。氣氛日趨緊張,班上一名同學突然被拘押,有些同學被叫去問話,各班級輪流開鬥爭會。同學中有不少基督教徒,他們定期團契祈禱,被指爲小集團,好些人被審查批鬥,至少一人被逮捕。一位和我同是從廣州四中考上來的同學周X也多次被批鬥。黨團幹部幾次找我談話,說他們掌握了充分證據,周X是反革命份子,要我揭發周的罪行。我莫名其妙,一再表示我從來不覺得周有什麽反動言行。他們大為不悅,指責我不相信黨,不聽黨的話。但是周被批鬥幾次之後,也就沒有下文,並沒有當作“反革命份子”遭逮捕,可見“掌握了充分證據”純屬虛張聲勢恫嚇。
同學中信天主教的較少,互相間雖有個別接觸,卻沒有集體活動,不成“小集團”,可是我仍戰戰兢兢,擔心有一天會整到我頭上。聽說有教友老師或同學也遭到整肅。
整風 反右 “大躍進”
1957年春,毛澤東發動“整頓黨的工作作風”,號召大家“幫助黨整風”,要“向黨交心”,要“百家爭鳴”,“大鳴大放”,。黨支部書記(註)在大班會上信誓旦旦宣稱:“保證言者無罪”,“不打棍子,不揪辮子,不扣帽子。”“那麽偉大的黨,說話能不算數嗎?”於是一時沸沸揚揚,“大鳴大放”,紛紛“向黨交心”。
――――――――――――――――――――――――
(註) 共産政權的統治分兩套體系:行政體系和黨團組織體系。行政體系各部門有各級(如科、處)負責人,但又有與之平行的黨組織:黨支部、黨總支、黨委會,相應有支部書記、總支書記、黨委書記。各級黨組織頭頭永遠比相應行政單位負責人高一等。行政單位的正職(如科主任、處長)可以不是黨員,例如是業務上有成就的人,不具實權,甚至僅作爲花瓶擺景,而掌握實權的副職必定是黨員。或正職雖也是黨員,但副職才是書記,他可以決定正職黨員的去留。當然,也有正職就是掌握實權的黨員同時擔任的。此外,一個或幾個單位(例如科)的黨員組成黨支部,該各單位便歸該黨支部領導(包括非黨團員)。黨便通過這種方式來控制行政系統。
學生也一樣,各班級有班長、組長,但同時有各班、組的團組織來領導。大學生有黨員,黨組織更在團組織之上。
――――――――――――――――――――――――
我對政治不感興趣,也提不出什麽意見,能規避就規避,一有空便往北京圖書館跑。那時我們三四年級的臨床課程在城內西什庫校本部上,離北京圖書館很近。北京圖書館位於北海西邊,隔“海”就是北海公園,環境幽靜。我借了書就躲到北海邊看書,這裏不怕班幹部來找我去開會。
“大鳴大放”才沒幾天,不料風雲突變,《文匯報》發表了一篇殺氣騰騰的社論:《這是爲什麽?》(後來知道是毛親自組織撰寫),要“反擊右派進攻”;說什麼號召大鳴大放,是“引蛇出洞”;這不是“陰謀”,而是“陽謀”……反右運動鋪天蓋地而來。初時大家還以爲:只是說說話而已,頂多不過是“思想犯”。甚至有位中央大人物也說:“右派是人民的右派”。可是事態發展遠非如此,那些提過意見的人被輪番批鬥。最後,黨支部書記拿著名單,在大班上逐個宣讀誰是右派,如何處理。於是有的被監督勞動,有的開除學籍,有的抓去勞教(註)。就這樣,不需要經過任何法律手續,只由黨委會決定,在教室草草宣佈,那些同學便因區區幾句說話,斷送了青春和前途。據說“右派”的定額是5 %,只能多不能少。
我感到震驚和憤怒,如果說以往的各項運動令我逐漸感到共産黨可怕,那麽,反右運動的前前後後,出爾反爾,“引蛇出洞”,“陰謀”“陽謀”,令我認識到毛澤東共産黨的卑鄙無恥。
—————————————————————————
(註) 一種不經過司法審判,只由本單位黨委會決定,就把人送到農場或農村監管勞動的制度,叫“勞動教養”(勞教)。勞動教養不同於經法院判刑的“勞動改造”(勞改),一個有權勢的黨員,往往可以左右黨委會的決定,甚至一錘定音。因此公報私仇、挾怨報復的事情屢見不鮮。
—————————————————————————
緊接着,1958年的一場政治運動是“紅專辯論”(“紅”指忠於黨,加入黨團組織,做黨的馴服工具;“白”指它的對立面。“專”指專業上的努力和成就):佈置師生寫大字報,自我批評并互相揭發,批判“重專輕紅”。要“拔白旗”,我成了小班的重點“白旗”,在大食堂側門被貼了一大版大字報,在160多人的大班上被集中批判了一次,說我只專不紅,只管學習專業,是自私份子;不關心政治,不跟黨走,註定沒有前途,因為黨不會培養這種人。這是我平生第一次被集中批判,令我膽戰心驚。醫學院的許多教授都挨了批判。有一次,一輛小轎車把一位大專家送來接受大會批判,原來是鍾惠瀾教授,國際知名的傳染病學專家,衛生部顧問。他坐在台上的一側,一言不發。
“紅專辯論”還沒有完,接踵而來的是一連串鬧劇:
全民打麻雀:運動一開始就特別強調:“四害”(蚊、蠅、鼠、雀)中的麻雀,是毛主席加上去的,罪名是啄吃穀粒麥穗,浪費糧食。一聲令下,全民圍勦。首都人民身先士卒,組織起來日夜不停地敲臉盆,吹口哨,打彈弓,追殺麻雀,實際上是不分任何鳥類,見鳥就打,整整三天。除了少數鳥類逃到外國大使館尋求“政治避難”得以倖免,其餘都給趕盡殺絕。據說有某大使館人員倚在大使館門前,扠手觀看嘲笑這場閙劇。全民打麻雀的結果,引致連續幾年蟲害橫行,糧食大幅減産。
“大躍進”——要“超英趕美”。先是全民大煉鋼鐵,把鐵門窗,鐵樓梯,以至門環鐵把,鐵鍋鐵鏟,總之能抄到的鐵器傢什,都把它打碎投入土高爐;又把大樹亂砍亂伐當柴薪,為實現年産1070萬噸鋼而日夜奮戰。我們醫學院(城外部分)的右鄰是鋼鐵學院,有一天,周恩來總理親自到來動員學生去各地“指導”土法煉鋼。結果是煉出一堆堆連泥夾沙的鐵坨坨。
接著是農業高産“放衛星”(1957年蘇聯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那時中蘇還沒有公開分裂,中國跟着吹捧),種“試驗田”,“深耕”要挖地二三公尺,“密植”是把幾坵田的稻谷移種一處,小孩可以在上蹦跳。每天報紙頭版用大紅套印報道新的高産量,畝産幾萬十幾萬斤“放衛星”,把牛皮吹上天。毛還請出錢學森作科學論證,說有充分的光合作用和肥料,這樣高産完全可能。可歎一位受人尊敬的大科學家,竟然一時失智淪爲幫凶。據說日本的一個左派代表團來華訪問,“不無敬佩”地說:“你們中國人真了不起,我們日本如果這樣密植,不僅水分供不上,恐怕連空氣都透不進去。”
人民公社、“大躍進”的惡果,造成連續三年大饑荒,餓死三千萬人以上,超過半個法國人口。可是直到2011年1月的官修黨史二卷,仍然自欺欺人堅稱“三年自然災害”。其實,專家查證當時全國氣象記錄,那三年根本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自然災害,從北到南,基本上都風調雨順。
從“解放”初期,我從一個對共産黨抱著好感的小孩,轉而對一波一波殺人整人感到可怕,對反右“陰謀”“陽謀”感到可鄙,對“大躍進”等一連串瞎折騰感到荒謬厭惡。導致這種轉變的理由只有一個:眼見事實。
但是我從來沒有任何反抗意識,只是不想與政治沾邊。
分配到昆明醫學院當助教
1959年我北醫畢業,被安排作為師資留校進修一年,1960年分派到昆明醫學院當助教。那時正值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大饑荒時期,除了少得可憐的糧油副食定量供應外,買不到任何可以充饑的東西。作爲醫學院的教師,仍然免不了餓到水腫,早上起來在前額一按一個凹;尿頻尿急,常常來不及去厠所而尿濕褲子。我當然知道這是“營養不良性水腫”,但有甚麼辦法?
同事告訴我,郊區農民有賣田螺的,於是我常去買來吃,也寫信告訴爸媽我可以買到田螺,“報喜不報憂”,免得他們擔心。幾次以後,爸爸回信說:“每次都說田螺田螺,那些橡皮塞子(黑黑的田螺肉,很像藥瓶塞子)有什麼營養?”不過他們也無可奈何。
有一次,一個農婦用衣服遮遮掩掩地抱着一隻母鷄到醫學院附近郊區來賣,一問要二十元(我月薪56元),我喫了一驚。偶然與一位來自州縣的同事談起,他笑著說:“聽說上海郊區農民一隻鵝賣一百多塊呢。”我咋舌,說農民要發財了。他不以為然,小聲說:“你知道農民養隻雞容易啊?每戶限養兩隻,養多了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其實也沒有飼料多養。還要定額交售鷄蛋,收購站的人每個月提着籃子到各家收購。我看那農民抱着雞來賣,很可能是家裡有人生病或其它原因急需錢用。還得偸偸賣,給城管(城鎮市場管理委員會)看見會被沒收。我們城裏人雖然也難,起碼還有定量供應。農民交了公糧和“餘糧”(一種強迫徴購的苛捐),還有甚麼?糠菜半年糧,農民難吶。”我聽了心裏惻然。其實他不敢說出更多事實:農村餓死了多少人!
雖然物質條件非常惡劣,但我滿腔熱情地投入工作,一心爲人民做些事情。科裏安排給我的課最多,幾乎把能排的時間都排滿,連晚上都要給中級醫士及護士進修的“夜大學”上課。我是最受學生歡迎及院務委員會肯定的青年教師之一。醫學院按上級指示進行教學改革,重新編寫教材,我是重點組的成員。我勞動積極;連業餘體育活動都領先。按照他們的說法:曾慶斯樣樣都好,就是重專輕紅。
黨支部曾動員我參加“黨課”學習——申請入黨的第一步。事實上誰都看得清楚,你要“上進”,得到特權和利益,不入黨是不可能的。可是我怕政治,怕那樣的“黨”,雖然黨員也有好的,也有不辭勞苦、認認真真做工作的,但我看不慣那些踩在別人頭上往上爬的黨員,或寧左勿右,形左實右的黨員,而往往那樣的黨員才得勢。我看到黨員雖然有特權,卻也受到更多制約。共産黨的統治就像一張網,群衆在底層,各級黨員是層層網眼,自上而下收緊網眼,才能控制群衆,我不想成爲網眼,因此婉言推卻了參加黨課的邀請。但我會“聽黨的話”,會認真做好業務工作,願意以實際行動“爲人民服務”。
可是,即使我想這樣做個“順民”也不可得。業務提升了,工作做好了,但你不是黨團員,就是“重專輕紅”。還在北醫師資進修期間,我寫了一篇關于血沉研究進展的論文,經二弟補充完成,1963年發表於《中華醫學雜誌》。這很自然地成了我“重專輕紅”的物證,雖然不便明說。但無休止的政治學習,批評和自我批評,鑒定,評比,“重專輕紅”的帽子如影隨形。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運動,“不靠攏黨”,“不跟黨走”的“落後分子”定性,更如加在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咒,無時無刻威脅着我。
由於共産黨內務實派施行了“讓農民喘口氣”的經濟糾偏政策,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大饑荒至1962年後期開始緩解。可是從1963年起,毛澤東又發動了連續三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運動”(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高唱“階級鬥爭,一抓就靈”,要“階級鬥爭日日講”。幾乎每天白天或晚上都有兩小時政治學習。氣氛越來越繃緊,隨後毛澤東更直接發動了舉世震驚的“文化大革命”,把國家人民進一步推入災難深淵。
(承蒙蕭振先生之邀,及網路技術協助,試將拙著<浩劫逃生記>連載於美華論壇。小人物小故事,也算是過來時代的一個小小見證。讀者高明,歡迎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