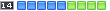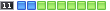[img]../images/fileType/jpg.gif[/img]此主题相关图片
[imga]../images/upload/2017/05/07/132332.jpg[/imga]
我的音乐老师
陈善壎
我没有进过学校,所讲音乐老师是工人合唱团的音乐老师。他姓曾,我不忍提起他的名字。他是音乐家。我结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靠制作人类骨骼标本为生的人了。
五十年代初期,我在一家工厂当学徒,很喜欢唱歌演戏的,参加过省工人合唱团,曾老师常常来辅导我们。他有名,人也精致,又正好有几支歌被我们满崇拜地唱着。后来晓得他还是一个进步音乐工作者,地下的时候写过骂反动派的歌,组织过迎接解放的群众活动;这就更坚定了我对他的敬意。
我不懂音乐,只是爱唱歌。每当他来,我尽量突出我的音乐天才以求他另眼相看。谁知他根本不理我。有一次他走出工人合唱团的活动室,潇洒多姿的呢大衣从我脸上拂过去,那感受就跟成年后女朋友的头发从我脸上拂过去一样。直到今天,在认真回忆他的此刻,才想到那时我不过十二三岁,一个快要三十岁的艺术家,怎么会把一个自命不凡的小鬼放在眼里呢。
他皮肤白皙,戴一副金丝眼镜。走起路来看得出急躁,总是一脚碰在凳脚上一头砸在门框上。只在他指挥我们的时候才能见到他的微笑,只在他跟我们一起唱的时候才觉得他是可亲的。他总是要求我们唱出力量唱出希望,要把新中国的朝气唱出来。
后来我离开了工人合唱团,把他也渐渐地淡忘了。
再次见到他的时候是那样离奇。我站在城外的一座荒丘上举着一把半损的锄头,这锄头不知怎么地卡进一口棺材的缝隙里了。我撬了几撬,立即冲出令人作呕的恶臭。土方队长(也就是包工头)贺驼子走过来,近前看了看,说到:“把酒癫子喊来,等他来收拾。”
不等人去喊,叫酒癫子的人已经闻风来了。他饶有兴趣地绕棺三匝,同时请几个夫子帮忙把棺材挖出来。我一眼认出此人就是曾老师。在我们下力的时候他席地而坐,从大衣口袋里拿出二两装的扁酒瓶,身边有一只麻袋和一把小钉耙。这回他用真正欣赏的眼光看着我了。
我注意到每当工地上先天挖出了棺材或者当天要挖掘古墓,曾老师就会悄然来到工地上。他远远独坐树荫下喝酒,有时拿着树枝古里古怪挥舞着。在不是贺驼子的工地上要是出土了骨头,因为人不熟,他会耐心等到收工,会在暮色苍茫中甚至深夜行动。
后来我就才知道,曾老师能这样准确地来到工地,都是贺驼子通风报信。
我刚来土方队的时候不喜欢驼子,都说土方队长是喝血的。慢慢地觉得他还好,还不见得怎样地心狠手辣。他高不过冬瓜,说起话来偏是盛气凌人的。“我不吓了你,老子楼上住的都是音乐家。”原来曾老师是他的房客。
一日,驼子在工地上置酒豪饮,男男女女没大没小地端着泥巴碗你一口我一口。我坐扁担上发痴,空空地看天看地。我起身去捉螳螂,看见曾老师在那里数蚂蚁。我带半瓶酒过去,才知他不是在数而是在跟踪。我装出对蚂蚁有和他相同的兴趣,跟随蚂蚁跑了好长一段路,最后蚂蚁列队钻进一座坟墓里去了。那里有一个很隐蔽的洞,他扒开碎石杂草,说道:“这可能是盗墓贼留下的入口。”而后又把它掩蔽起来。他走上来靠墓碑坐下,喝着我带的酒,重复着工地上打夯的号子。那旋律极单调,不过他重复几遍后就有了发展,开始变奏。
他简直跟从前一样没把我放在眼里。我故意哼一支他的歌。这招很灵,他闪亮眼睛瞧我。我边哼歌边装着看蚂蚁。不料他竟没再理我,突然起身就走,差点被一个树桩绊倒在地。我赶忙扶他,边走边说,说他曾经是我们的辅导老师。他显得尴尬。我感到可能是我过去的领导阶级身份作祟,便从容告诉他我已经不再是工人,是道道地地的土夫子。他明显亲热些,把手放到我肩上下个陡坡。
曾老师终于邀我喝早茶了。我每次都像赴什么盛会一样,早早起床赶到城边一家离他住处不远的茶馆与他晤面。驼子常常在场,大多是那些老茶客。我到贺驼子家里坐过几回,却不蒙邀请上楼,曾老师只在楼下假驼子“一方宝地”接待我。驼子老婆有点神经质,听到厨房里哧哧的声音,高喊“骨头开了,骨头开了”。她闪着一对大奶子,把一盆排骨汤端到桌上来。
我已经知道曾老师现在赖以为生的手艺是制作人类骨骼标本,贺驼子还是从地上捡了几张过期的合同给我看。“你看,他就吃这个。”这些合同每张除数量参差外其他内容都是相同的:名称——人类骨骼标本;规格——常人高;材料——真骨。或者是:名称——分离头骨标本;规格——常人头骨;材料——真骨。难怪他麻袋里颅骨总是多一些。
他每早跟驼子同赴茶馆,两人很默契地找个僻静角落坐下。驼子就在这时侯向他提供有关迁坟徙墓的情报。告诉他某坟无主,某坟不能动,或者工地上挖出了多少口棺材。曾老师并不专心听,闭上眼睛像睡着了;忽然睁开眼,为吃包子。
有个叫海爹的茶客,天天贩卖南门外闹鬼的新闻,讲得有声有色,情节离奇。每讲到关节处,便缓缓昂起屁股说:“等我拿盘包子来。”海爹刁钻精细,兑开水拿包子是他代劳的时候多,不论排多长的队,钻进去摸起就走,端到桌子上偶尔多一个两个的。他拣两个包子,一糖一菜,在包子肚子上各咬一口,再合拢压扁,精心捏出荷叶边来。随着他牙关节的纵横捭阖,吐出蓬蓬热气,一颗露珠大小的鼻涕沾他髭上发光。“我满舅子那天上山砍柴,亲自看见那鬼从坟里拱出来。”他说着,侃侃罗列出十数条证据。遇上冥顽不灵的,把头一扭,半天不齿那人。他强调:“老子几十岁了,会诌胡说?还有鬼的鬼,影子的影子。魍魉就是。”
驼子手捂茶杯一言不发,狡黠地笑。他双脚离地寸许,自在摆得清高。驼峰威武,显得桀骜简慢。
只有贺驼子敢当面奚落曾老师,笑他手无缚鸡之力,笑他孑然一身顾影自怜,笑他神楞楞鬼楞楞被人传为茶余酒后的谈资。不过只小声说,不让邻座的海爹听见。
逢上下雨天工地不开工,我就到驼子家去玩。可惜曾老师大都把自己锁在楼上。只在他要处理骨头的时候才能接近他。骨头拿回来要执行去除软组织和打磨关节面等等工艺,这些都是在后坪中搭的茅屋里做的。茅屋里有口大铁锅,我帮忙煮过人骨头。做完后,他递支烟酬谢我。
他收拾些骨头背上楼。驼子问他:“你为什么不去玩丧葬班子呢?有吃有喝。凭你的本事,还不是头把彩。”他看都不看驼子,严肃得出我之所能料。“艺术是为活人服务的,我还没堕落到那种地步!”这话听上去,就跟他背的骨头一样硬。那时侯死人多,城里的丧葬音乐班子得到蓬勃发展。刚为这边的“英雄”送过葬,又有那边的“烈士”要追悼。一天下来,有几张大票子兑现不说,还可吃得个脑满肠肥。
我这天坐得晚。贺驼子预言道:“你再坐会儿,包能听到他发酒疯。”果然,约莫晚上九点中的时候,楼板响起踢跶声。我记起他的烂皮鞋是钉了铁后跟的。这声音开始极轻,有如一只被风浪击得千疮百孔的小船躺在沙滩回忆往事,一圈圈波澜从他心的深处向空中扩展。踢跶声的节奏慢慢激越,楼板缝里有灰尘落下。驼子端茶避开去,独自坐坪里抽烟。他老婆抱着婴儿从内室出来,欢天喜地地叫:“啊,骨头响了,骨头响了。”
节奏变得紧而密的了,逐渐变得狂热、炽烈,变得多情而贪婪。整座楼房都在抖。我全身紧缩,怕一根牵系他生命的弦突然断裂。灰尘纷纷下落,驼子坐坪里叹气。
楼板上的节奏越来越疯狂,土地都在微微颤动。我相信只有入魔才能把生命倾泻得这样彻底。他是在舞蹈,此刻他是一个舞蹈着的音乐家。一个只有脚功能的舞蹈家在阐释失去旋律的音乐家。他的音乐只留下硬朗节奏,犹如生命只剩下叩击有声的骨头。
踢跶声停下来,寂静了好久。听见他开门。又隔了好久,听见他下楼。他只下一半,形销骨立倚在楼梯扶手上问驼子:“没酒了,你有么?”
雨季来临,这是土方队的淡季。贺驼子带上比他高出一头的老婆下乡走亲戚。我只得另谋生路,去一家街办工厂做钳工。一天下班,出厂门就碰见曾老师在麻石街上踟躇。一个可能是他旧游的人与他劈面相遇,站住想跟他打招呼。他却用如醉如痴的目光从那人脸上扫过,带着有点酒香的微笑蹒跚走了。我追上去,叫他“曾老师”,他很高兴,怪我好久不去看他。我邀他喝酒,进一家偏僻的小酒店。他记起来我是工人文工团里最小的成员,回忆了一些当时的情景,谈得很投机。
他忽然沉默,自顾自喝闷酒。他说,弹钢琴的不行,手指太短了。我以为他是说的从前乐队里某人。我断定他醉了,搀他回去。一路他都咕嚕着,不行,不行,再找一个。天上乌云翻滚,道路漆黑。我很后悔喝得太久了。前头还有好长的泥泞路。
我扶他上楼。他的手不听话,费了点功夫才打开锁。灯光一亮,我大吃一惊。
这是一间很大的空房,面积是楼下一间堂屋两间卧室一间厨房一间杂屋的总和。没有天花板,瓦缝里不时漏出闪电的白光。一个很整齐的阵容摆在我面前,那是一群制作精良的人类骨骼标本。它们被按照舞台上的乐团那样布置。每具标本的颈椎骨上都用绸带系了一个领结。这些标本有站的有坐的(要使标本坐着可要费很多心思)。一架旧钢琴前也坐着一具标本,摆出弹奏的姿势。他摸着它的指骨给我看:“太不修长了,对么?是个做粗活的。”我打了一个寒噤。
木板放在四块窑砖上,看来他是睡在上面。旁边火缸上的小碟里有吃剩的卤菜,横七竖八许多空酒瓶。乐谱满楼板都是,我发现有他新写的手稿。在我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忽然响起急促的踢跶声。他又那样踏起楼板,兀然林立的标本随着楼板的震颤摇头摆足,在昏黄灯光下产生惊怖心目的效果。
过了那惊心动魄的一夜,我知道他是不能离开艺术的了。离开艺术,他便是凡夫俗子,便是平庸的多余人。他已经有了集这种标本的癖好,面对这些连缀起来的骨骼,他有不同于比较解剖学家的发现。
他跟白骨打交道的时间不短了。起初不过为了果腹,许多医学院校及综合大学的生物系都找他定购人类骨骼标本。他有了制作的热情,觉得是门不错的手艺,同样需要专心致志,需要勇敢和勤劳。记不得从哪天起,学校不再上课了,再没人上门要货。就是原本定了货的也没人来履行合同。标本积压半楼,他整日面对这些标本发木。长久地无所事事,他开始精益求精于自己的作品,不断地摆弄它们,终于走进了自己的梦幻。他把这些由生命中最坚实的材料制成的作品组成乐队,是他赋予了它们灵魂。他又可以创作,又可以排练、演出了。在这城市边缘的木楼上,他把自己封锁在自己制造的幻境里。
那天早上我是顶着雨回家的,蒙头睡了一整天。我梦见他在荒原上呼唤,他呼唤一位大师,一位杰出的钢琴演奏家。他爬到山顶,看不清脸,只能听到声音。这声音已不是一个人的声音了,是雄浑的大合唱,继而变成万籁之交响。这个梦很长,老是重复几个镜头。有几次我清楚是梦,刚到醒的边缘又沉回梦里去。等我挣扎醒来之后,已是第二天下午两点钟。
没等到吃晚饭我又去找他。我想把他从魔境中拖出来,长此以往人会消耗殆尽。路上碰见送葬的队伍,一路十几辆汽车。他们用冲锋枪送葬。柏油马路上满是子弹壳。头辆车载的灵柩,二辆车上坐满丧葬班子的吹鼓手。他们声嘶力竭吹着最流行的丧葬音乐,暗示死者是死得其所并重于泰山的。
我直往城外走去。大门上挂着好大的老式铜锁。连去几次都是这样。等到贺驼子一个多月后从乡下回来,才请驼子打开楼上的锁进去。楼上依然如故,只是钢琴前的那具标本被撂到墙角去了。驼子认为,他是去了外地推销产品,这年月自己不找门路不行。
有件事情使我和驼子非常不安。那天我去茶馆找驼子聊天,顺便告诉他,有朋友介绍我去南门的一家街道工厂,那里的活要轻松些。驼子挽留我,说无论什么时候有难处就找他。
邻座有茶客挑逗海爹,“海爹呀,您老人家那鬼如今安在呀?”说完抿起嘴笑。海爹并无难色,喝口茶从容答道:“那鬼么?早打了。如今祖坟山清吉了。”
驼子和我同时一怔,茶没喝完就去他家商量这事。驼子很慌:“哎呀,这酒癫子!莫不是去挖那座坟了?我跟他讲过那坟动不得,那坟虽说无主,却在人家祖坟山上……”后来又说,“不至于罢,总得有个尸呀。”
曾老师终于没有回来。
我去了南门大古道巷的工艺美术厂。谁介绍的记不清楚了,可能是钟叔河?这家街办厂有点意思,是个“藏污纳垢,牛鬼蛇神成堆的地方”。正在天井里做石膏胸像的年青人是写《火烧红莲寺》的平江不肖生向恺元先生的孙子。躲在后院墙角煮骨头的是湖南师范学院生物系讲师郑英铸。做几何教具的陈孝弟是某大学数学老师,他一边工作一边给大学还没毕业的年轻右派讲傅利叶级数。旁边小房里埋头钉板板鞋的是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提到的“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她满脸沧桑,沉默、高贵。钢琴家罗世泽不知做的什么业务,跑上跑下。钟叔河夫妇做字画装裱,他们的裱糊手艺精到。与钟叔河莫逆的朱正戴着高度近视眼镜描图,他是解放后第一本《鲁迅传》作者。
这里有一个做人类骨骼标本的人,更怪的是也有一个驼子。这个驼子要是不驼便是美男。他待我好到只能用温存来形容。他姓张,叫张衢鹏,是这个工厂的女厂长易嘉兴的儿子。易嘉兴是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的身份兼厂长,我们都叫她易主任。这么多牛鬼蛇神能聚在这里安身,多与易主任有关系。那时的街道干部没几个好人,而易主任不但人好,有着那个时代绝迹的娴淑。我不明白她怎么会被重用?几十年后的今天,她有一个孙女出了名,唱歌的,叫张也。
我问郑老师,你认识做你这行的一个姓曾的吗?他说,那是我徒弟,是我教他这门手艺的。郑英铸说了许多曾老师跟他学艺的事。(1980年后,郑英铸先生在长沙教育学院教书,工水墨画。上门求画者多惮其床下的一堆人骨头不敢进门。)
多年之后,蚂蚁、微生物,还有老鼠、黄鼠狼们足以把一个人的筋肉啮尽刨光的多年之后,我又回到了驼子的土方队。驼子在我重遇曾老师的工地附近又承包了工程。原来的工地上,本该出现一个大工厂的,现在立着的还是稀稀拉拉的手脚架。到处堆着砖头、石灰、水泥。
要掘一座大坟了。土夫子们奇怪驼子为什么抖个不停。我依稀记得这是我跟曾老师追踪蚂蚁的地方。坟墓被掘开,棺材早已腐烂。人们诧异地看到,在躺着完整的人体骨骼的棺材旁边,还有一具斜倾的骷髅。他一身雪白,他是干干净净的,右手握住钉耙,手电筒被朽塌的木屑埋了半截。我迅速注意到棺材里那副骨架的指骨,的确修长。
我觉得贺驼子早就有所推测,只是今天才证实而已。他捧起曾老师的颅骨,伤心地落泪。颅骨上有裂纹,是为钝器所伤。驼子完全懂得把人当鬼打的扁担砍下来的痛快劲。他猜想,那夜曾老师被打伤后钻进坟墓里躲避,就这样再没能钻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