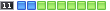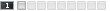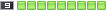荒唐年代荒唐事
树 立
大跃进年代离现在不算太远,但发生在那个时候的许许多多离奇事件,人们巳渐渐淡忘了。年轻人听老年人讲大跃进,根本无法相信。说这是在编故事吧,人世间哪有这么多的荒唐事儿呢!它比《天方夜谈》还要《天方夜谈》!
年青人最大的疑问,是不相信自已的父兄辈当年竟是那样的愚昧,会做出那么多的“国王的新衣”的蠢事;对没有穿裤子的皇帝,竟然视而不见;对许多人明明把事情做错了,做糟了,还在往脸上贴金并大声叫好的现象为什么见怪不怪呢?他们总是问了又问:在我们这么大的国家里,大人都这么傻,小孩呢?为什么那个时候连一个能够发现皇帝没穿裤的小孩子都没有??
年纪大的人只能苦笑,只能哑口无言,无法作答。但是大跃进的荒唐事,我们无法忘记,我们还是要讲。你就把它当做《天方夜谈》罢,信不信由你!
以下讲的就是几个大跃进的荒唐事。
(一)旷古未闻的深翻改土运动
在人民公社成立后当年(一九五八年)的冬季,出现在中国大陆广大农村的深翻改土运动,是一件旷古未闻的奇特事情。
中国疆域辽阔,南北气候迥异。南方好些地方,如地处亚热带的广东省,这里气候温和,雨水充足。冬季无严寒,也宜于种植,故一年可以三熟。在往年,当地农民每当秋收农事完毕之后,家家户户就忙于冬种。勤劳的农民因地制宜,有的种番薯、木薯,有的种小麦或各种蔬菜,故此每年能增添不少收入。可是这一年恰好遇上公社化,一切农事活动的安排都必须听命于公社,上头骤然间下了死命令,改变了农民历来的传统做法,全省很多地方都把冬种改为“深翻改土”运动。
上头规定的深翻改土方法十分奇特:他们要求社员们把耕地的泥土由表到里一层层地挖掘下去,一直挖到二米甚至二米以上的深度,然后把挖出来的表层耕土埋在底层,底层挖出来的新土则置于上层。
这样做的目的很清楚,那就是用很深层的泥土来更代原来上层的泥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们认为:那些长久埋在地下的泥土,比表层的泥土养分更多,更适合于庄稼的生长。这一耕土的“大翻身”措施,将大大地有助于来年夺取农业的特大丰收!
为此各个公社取销了冬种,组织了大量的劳动力,投入声势浩大的轰轰烈烈改土运动。书记声称亲自挂帅,社员们吃、住都在田头。各个公社领导都狠抓进度,开展了“劳动竞赛”、“评先进”等多项活动。
一个冬季过去了,轰轰烈烈的改土运动也完成了。但农民们付出的艰苦劳动事后并没有获得原来设想那样良好的回报。相反,由于他们用了实际上是没有肥力的深层生土,代替有肥力的浅层熟土来种植庄稼,吃力不讨好,结果受到了自然的惩罚:收成不是增加,而是大大的减产,有的田地竟然颗粒无收!
(二)拆屋积肥 叫人哭笑不得
广找肥源,争取农业丰收,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是广大社员的心愿。如果领导者能按客观规律办事,真正发动起群众,群策群力,应该是有所收获的。无奈当时许多掌握大权的公社领导干部,由于缺少科学知识,而且头脑发热,好大喜功,又高高在上,听不得别人的话,所以尽搞瞎指挥。这样的人当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比如把农民还好好居住着的泥砖屋强令拆除,把泥砖拿来做肥料的做法,就是这样的例子,叫人哭笑不得。
强令将农民正在居住的屋子拆下做肥料,这事发生在中国南方的许多公社。且说位于笔者家乡附近的一个公社,千百年来,此地95%农民居住的都是用泥砖砌成的土屋(当地老百姓称这种房子为“土楼”),谁知到了公社化的时候,公社领导竟一时心血来潮,硬说这些屋子的泥砖,经过人的长期居住与多年的风化,里面堆积着大量对农作物生长最有价值的养份。因此决定拿来做肥料,他们一声令下,就把许多原来好好的房子拆除了。
那时×× (村名)共有14座土楼。当年被拆毁的有涂楼、下田楼、雍容楼、陈厝楼和向北楼5座。部分拆毁的有大寨楼、松柏下楼、上山门楼、缵美楼、德宅楼、桃仔□楼、饶厝楼和臼窟楼8座........
但是,用这些拆下来的屋子泥砖种植作物的结果表明,这种泥巴并不藏有什么特别的营养成分,对农作物也不见有什么了不起的肥效;单靠这样的泥巴,而不再施肥的庄稼且会歉收。
当时农民对这种胡作非为当然敢怒而不敢言。但在事隔若干年以后,有人敢说话了。有人还把这件事当做历史事件,记载入当地近年出版的《××县文史资料》内,让他们的子孙后代,都知道当年曾经发生过如此这般的荒唐事。
(三)削发积肥,成千古笑话
发动社员把头发剪下来献给公社作肥料这事,那个时候在许多公社都很盛行。因为有些领导同志听人说头发这东西很有营养,有助于农作物的生长,而长在人的脑袋上,却没有什么用处,乃可有可无之物。于是他们发出了号召,要广大社员们捐出头发。当时许多社员都听从了,尤其是那些年青的男女社员,他(她)们怀着对党、对公社的无限热爱,积极响应上级的号召,都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自己的心爱头发。就笔者所知,其时仅粤东某地的某一个公社,包括公社干部、社员和公社中学的老师、学生在内,一下子就有一千多人剃下了头发,男的马上成了光头佬;女的没了辫子,只留齐根的超短头发,形同尼姑。大家都满怀着激情,敲锣打鼓,把头发献给公社做肥料。不过,头发虽然是捐出来了,也做为肥料弄到田里去了,而这一造的庄稼非但没有长好,反而格外的瘦小,有的还枯黄死掉了,结果农作物的收成大大减低,有的农田连种子的成本竟收不回来,社员们白白耗费了几个月的劳动力。事后许多有经验的老农都偷偷在议论这件事,他们都说:人的头发这东西,质地异常坚韧,在土里是最难溶化和最难被庄稼吸收的。就算它有什么好的营养,埋在地里也只是占着茅坑不拉屎,一点肥效都没有发挥出来,耽误了植物的生长,庄稼不歉收才怪呢!
(四)遍处可见的红专大学
许多人都见过大学,或者上过大学,知道大学是怎样的一个去处。,而在大跃进时的人民公社,却办起另一种与众不同的大学。这种大学尽管它的规模都很小很小,但数量却是很多很多。这一类的大学叫“红专大学”。
在全世界上,红专大学可以说是仅见于中国大陆的一种大学。在全国农村公社化以后,因为要体现建立公社宏伟规划,说公社是工农兵商学五位一体、政社合一的组织政体,必须有教育部门这一块重要的设置。
公社号召农民要学习文化和提高文化水平,以适应当前大好形势的要求,上级的领导们认为昔年农村里办的什么“农民识字班”、“扫盲班”现在已是层次太低,不能适当代的要求了。于是就办起了高学制的红专大学。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喜欢“红”这种颜色,民间一直认为它是吉祥、如意和喜庆的象征,但在大陆解放前后这几十年,红还有另一种寓意,它代表革命与进步。例如称革命的军队为红军,称农民的打土豪、分田地为红色暴动,叫革命政权为红色政权……。喜欢使用诸如红色的旗帜、用红布或红色的纸写革命标语…….., 到了全国动乱的文革年代,更爱这个红字:比如红宝书、红像章、红司令、红太阳、红色的忠字牌、红色的海洋……..,还有那些挥舞着拳头和皮鞭、起来造反的,都是挂着红臂章的红卫兵。
至于一个人,如果认为他的思想“红”了,说明这是突出了政治,是进步、是忠心于革命的表现。
在我们这里,“专”则是指专心致志于文化、科学技术的学习,而且学有所得。
公社办红专大学,意愿倒是很好的,就是要培养大批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民公社,又掌握科学技术的又红又专无产阶级事业可靠接班人。
想要看看中国公社里的红专大学没有任何困难,因为它遍处都有,并且无需申请和得到许可。在我参观过的许多公社中,无一没有此类大学。大体上是每个大队都办有一所红专大学,在一些人口较多的公社里,不只生产大队办有红专大学,连小小的生产队也有办红专大学的。
中国农村的红专大学,应该是世界上投资最少、甚至是无需任何投资就可以办起来的大学。
公社化那段岁月,笔者刚好受到学校的派遣,带领几个学生到公社里接受贫下中农教育,与他们日夕相处,有幸亲目看到公社建立的好多所红专大学的真实情景:
公社的红专大学通常都设在农村的某一所简陋的空房里,校舍与农民住的房子基本没有什么区别。还有不少红专大学并没有自己独立的房子,它与公共食堂是同在一个地方。这类大学的门口都挂有一块写着“红专大学”四个很大的汉字的木质的牌子;有的校名则是写在纸上的;还有的是用红漆把字直接涂写在门口的墙壁上的。
大学房子里的任何时候都是空荡荡的。这里没有教师,没有课室和实验室,更没有图书馆,连个打球的简易球篮场都不见。说老实话,在我们的几次的参观中,没有一次撞见有红专大学的学生在这里上课。
那么,红专大学这房子是做什么用的呢?据我所知,在白天,那里在很多时候都是空无一人,只是到了晚上,公社或队里的干部同志有时会来这里开会议事;或者召集社员们来听传达上级的指示,或者宣读文件什么的。至于那些招牌挂在公共食堂里的红专大学,在公社大办食堂那些日子,虽然热闹非凡,但进入这个地方的只是一日几次前来吃饭的社员。
(五)报‘丰收’假戏真做 ‘反瞒产’苦了农民兄弟
中国大陆的绝大部分人民公社是建于1958年的9月,到了10月下旬,在不足两个月的短短时间里,据公布:全国各地已建成的人民公社就有26万多个,据说这时全国99%的农民(约一亿二千万人)已被归入公社管理。
从这个时候起大约有一两个月,公社过的是风风光光的日子,它受到伟大领袖和各级政府的充分肯定,全国舆论赞扬之声,更是不絕于耳。可是谁也想不到,它很快就衰落了。
公社的衰落,与当时被领导誉为“新生事物”的公共食堂的倒台,在时间上几乎是一致的。
在公共食堂开办后不久,细心的人已看到了种种不祥的朕兆了:首先是公社食堂拥有的粮食很少,而且是愈来愈少,但它还是按照上头的要求,一天开出三顿干饭。有些地方的公共食堂,还加上上午、下午的中间时分两个“点心餐”。这样,一日就开出了五餐饭,任由社员吃饱。粮食这样随意胡花浪费,必然会受到惩罚,全国几乎所有的公社食堂,短的不到一个月,长的也只有两个月,粮食的供应就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明眼的社员都看出它关门的日子屈指可数了。
公社食堂为什么没了粮食?农民的口粮到哪里去了?原来,大跃进和公社化以来,全国各地为了迎合上级官员好大喜功、狂热虚荣的心理;为了证明所说的“人民公社好”,把做人的诚信抛到九霄云外,不惜竭尽吃奶之力,拼命巴结,大刮浮夸虚假之风,无中生有地编制了各种天文数字,虚报粮食大丰收或特大丰收。上级对下头这样的做法当然正中下怀,因为这些天文数字正可列为自己的伟大政绩,因此也就以假为真,并回过头来把它做为高指标向农民征购粮食的根据。这么一来,公社的大部分或绝大部分粮食当然被名正言顺地征收走了。
但是事情并不到此为止,因为原来上报的假丰收数字实在是太大太大了,公社要完全还清国家这么高额的征购任务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上头却不理你这一套,认为公社还是私藏了很多的粮食不上缴,故此下了死命令在全国开展了一场所谓“反瞒产”的运动!有些地方,连农民留作种子的谷种也给弄走了。
农民的口粮原来就不充足,加上公社化办食堂的胡花浪费,当时已面临难以糊口的境地,“反瞒产”运动的开展,对他們来说无异雪上加霜,生计愈更艰难。笔者家乡有一位叫林×实的人,不久前在该县出版的《×县文史资料》如实地记述了当年“反瞒产”给当地造成的灾难:
“……高估产带来的高指标征购,调走了包括农民口粮、种子在内的大量粮食,仅剩下的粮食不够农民糊口,且 (粮食) 又全集中在公共食堂里。当时西理溪村 (地名) 的公购粮任务每年34万多斤,在全公社任务最重,食堂办不到一个月,社员每人每月只有13 (市)斤大米,还不够吃稀饭。食堂里每餐的粥,水多粥粒少。村里有一社员 (名林道镇) 每逢去食堂用餐时都说:“去食堂漱漱口.....
“……粮食严重缺乏,食堂里煮的是‘瓜菜代’,每餐社员吃的是番薯头、藤、香蕉头等杂物”。
情况是如此严峻,此时凡是头脑稍为清醒的中国人,都知道如果再这样胡搞下去,一场全国性的、更严重的饥荒就会很快到来,大家都为此而忧心重重,只是不敢说话。而上头的官员,他们并不了解农村的实情,只凭听汇报来发号施令。在各地已经陷入饥馑的严峻时刻,他们还认为全国形势大好,到处是特大丰收,因此仍然在为公社和公共食堂大唱赞歌,继续搞瞎指挥,雷厉风行地大力开展“反瞒产”运动!甚至在中国最具权威的报纸《××日报》上公开说出“公社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这样的混话,提倡大家要“吃好的”;要“食堂办小吃部。”真令老百姓哭笑不得,人们很自然地想起了《国王的新衣》这个故事。
(六)到处是饥馑的人群
每一个经历过“大跃进”的人,都不会忘记这段苦难的日子:从1959年的冬月这个时候起,中国大陆就闹起了饥荒!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几乎处处都可以发现饥馑的人,他们之中既有老人和小孩,也有少年人与青年人。农村的情况比城市更为严重。这些挨饿的人一个个面黄肌瘦,面有菜色,显示出营养不良的病征,不少人更发生了水肿,我可是有生以来头一次看见有这么多的人发生水肿,也是头一回认识了水肿的典型外表病状:患者的皮肤都异样苍白、全身皮下都或多或少地沉积了水分,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浮肿,有些人两只脚因水肿液大量积蓄而异样地浮肿起来,如果用手指头按压一下浮肿的部位,这个部位就塌陷下去,形成一个小窝,这小窝久久不能平复。
究竟全国有多少人发生水肿呢?这是很难作出准确的统计的。我们对此且抛开不谈,不妨只看看当时一个小小的乡村、一个县的片断情况吧!
“…….当时村里 (指××县江东乡西前溪村) 有二千多人口,约20%的人患有水肿病 (大脚) ,村党支部书记林乾临一家8口,便有2人水肿……….”(林和实:《我亲历的大跃进时期生活》。刊于《广东省××县文史资料》第26辑,第21页。2006年12月广东省××市政协文教体卫史委员会出版)。
“1960年至1962年……..缺粮的农民用瓜、菜代粮充饥,有的到处找薯叶、薯根、野菜。不少人营养不良,患了水肿病、肝炎、胃炎等疾病。据1960年统计,全县发生水肿病就有2.4万多人,一些虚弱的人因水肿病及饥俄而死。”(陈建民:《狂热的大跃进》。刊于《广东省××县文史资料》第五辑,笫17~21页。2000年12月广东省××县政协文史委員会编印)。
中国大陆在这个时期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有究竟有多少?确切的数字只好留待历史学家去考证了。
至于饿着肚子,患有严重营养不良的,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论南北东西,更是不计其数,到处皆有。
在缺粮的日子里,为了解救饥饿,人们四出寻找食物,想出了各种各种各样的办法以解决肚子问题:吃草皮啃树根是不用说了,人饿到这个地步,连许多有毒的东西都顾不上生命危险也拿来果腹了,这就是古人说的“饥不择食”嘛!
像邮局每天早上摆出来的那碗散发着福尔马林 (一种有毒的防腐剂) 臭气、用来粘贴邮票的浆糊,很快就给先到的饥民吃进肚里;含毒的植动物像狗抓豆、癞蛤蟆以至厕所里的蛆虫,也都有人敢吃。
{七}难以忘却的身影
在学校里的老师的日子同样不好过。在一所大学里,我看到他们竟然把用过水合氯醛或乙醚 (两种都是有毒的麻醉剂,其中乙醚且带有浓烈的气味) 麻醉、 以及用来苏儿 (一种难闻的酚类有毒消毒剂) 浸泡消毒过的、做过实验的死猫,死兔和死鸭子都吃了。有一位生理学讲师,肚子实在太饿了,把给学生做过实验的癞蛤蟆(蟾蜍)带回家煮着吃,一家人发生中毒,呕吐、腹痛不止,幸亏东西是一家老小分着吃,只中毒而未致死。
在发生饥荒的年头,有一件我亲自感受的事,说来虽是很细小的事,但不知什么缘故,它却深深印在我脑海里,多少年来一直挥之不去,难以忘怀。
当时,我工作所在的大学中,有一位年过花甲的老教授,他早年曾留学国外,在这所大学担任教职已经好几十年了,是一位德高望重、博学多才、深受同事和学生敬重的学者。我记得就在1960年隆冬的一个傍晚,天已渐渐黑了起来,与老教授同一实验室工作的同事们都下班回家了,我因有点未做完的工作留下来。这时我发现老教授还没有走,他什么事都没做,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实验室的一个角落里,不知在苦等着什么。我出于好奇和礼貌,上前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需要我这个年青人帮助?我看他欲言又止,但后来还是不好意思地说出来:“谢谢您,没有别的事,我是在等配给的豆腐。”说完了话他仍然静静地坐在那里,耐心地等候送豆腐的人到来。
莫约过了半个小时以后,天已完全黑了,果然有一个小干部模样的人给他送来几小块豆腐,我无意中望望来人给的东西,看清楚那是人们平常所见的那种中国水豆腐,每块豆腐也就比火柴盒略大一点。干部把豆腐交给教授之后,并郑重其事地要他在一个本子上签名。然后,这位令人可敬又可怜的白发苍苍老学者,就小心翼翼地捧着他得到的特别补助物品──几块小小的豆腐和我道别。随后,他那形销骨立、枯槁瘦削的身影也就从实验室里消失了。
几块小小的豆腐,体现了领导对一个科学家、一个老知识份子的关怀,本来应是给人感到无限温暖、让人感激涕零!可是仔细想想,如果你不搞这场发高烧、说胡话运动,不搞这个吹牛皮、尽做荒唐事的大跃进,人家的日子还是基本上可以过下去的,何须你来送这个豆腐呢?弄得大家都这么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