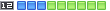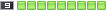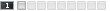小时候,只知道自己喝牛奶长大,从来没吃过母乳;直到18岁,侨居马来西亚的生身父母托叔叔找上门来,才晓得从襁褓开始抚养我成长的母亲,原来是我的养母。
母亲18岁时,经人介绍与背井离乡、时年38岁的父亲通信,不久便飘洋过海,由“水客”把她带到南洋去结婚。从此父亲当锡工,母亲在家养猪种菜,每隔几天就用脚车驮着菜拉到集市上去卖。
母亲与马来西亚游击队联系密切,怕事的父亲以叶落归根为借口,说服母亲一起带我们姐弟回到中国。谁知我们在父亲的故乡才过了几年“番客”的幸福生活,父亲就因病瘁死,抛下38岁的母亲,15岁的姐和10岁的我,从此我们就成了孤儿寡毋。
一个乡下女人,那年月怎么可能供得起儿女读书呢?于是,姐和母亲一样到了18岁就飘洋过海,嫁去了海南岛。尽管母亲把满腔希望连同家里从南洋带回来唯一值钱的一块手表送给了姐夫,然而,这桩当年母亲和同在自留地里浇水的亲家母包办的婚姻的结果,是姐和母亲一样,也在38岁开始没有了丈夫,不过姐是离的婚。
自从养父病故、姐姐远嫁后,母亲常常泪眼婆娑地叮嘱我,咱家五代单传,所以一定要发奋读书,出人头地。而母亲为了把我带大,受尽了生活的重负和坏人的凌辱。每天天刚放亮,她就蹑手蹑脚地起床为我做好早餐,然后急匆匆打开后门,从屋背檐下出发,肩挑箩筐步行6里地到镇上粮站挑未被拉走的谷糠,再把这一担担谷糠挑到加工厂碾碎卖给养猪场。同样,她年复一年,总是冒着剌骨的寒风,步行20多里进坑上山砍柴割草去卖。
记得读高一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我刚从县城中学步行回到家。吃完母亲照例给我准备好的一大碗干饭(她总是捞干饭给我吃,而自己喝的却是粥),一位“社教”工作队员来找我,原来是上屋人养的一只鹅不见了,说我母亲天天一早从屋背出门,肯定是她偷的,而妈却死活不认。那工作队员站在对方一边,要我明辩是非,同意让他们搜家。单纯、幼稚、学生气十足的我同意了,结果三、四个人翻箱倒柜也没翻不出什么名堂。
这真是一个法盲充斥的年代!而妈妈,她用自己的理解作出了反抗。当晚半夜,我被她的声声呜咽惊醒。原来她思前想后悲愤交加。她从没打骂过我,可后来她揪了我的耳朵,骂我为何这样不相信自己的母亲,这么老实竟然答应被搜家,像这样没有男人气概今后如何顶得起一个家!我从她的泪水里看到的是失望,是悲伤,我从来没有这样被震撼,从此我觉得自己才开始长大。
正是靠那种“人穷志不短”的意志,我成了出类拔萃的学生。然而妈妈她知道,那时如果没有好的出身,就会毁了我的前程。当叔叔拿着南洋来信偷偷地找来我家要认我,母亲做了饭菜招待他,并嘱我饭后送叔叔到墟镇上去搭车。送客时,她说来认亲我理解,只是公开了这一层海外关系怕耽误了你侄儿的前途。
生活在今天的年青人会认为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由于有了清白的社会关系,我才入了团,当上学生会干部;“文革”后期,才得以光荣参军、入党、提干。
我清楚地记得我随部队野营拉练路过家乡,第一次回家见到母亲的情景。
那一天,妈和作业组的人一起在坝子里给甘蔗施肥,看见逶迤的公路上尽是炮车,足足过了一天,她想:我儿子会不会也在这队伍里呀?如果在他会不会回家来看看呐?又想那有这么好的事!正把眼巴巴的目光收回甘蔗地里来,只见邻居一个孩子远远跑过来,气喘吁吁地喊:“森仔哥回来啰!森仔哥回来啰!”
妈妈乐颠颠地跑回家,我迎出屋来,叫声“妈!”——我看见的母亲竟变得满头白发,她慢慢走近,脸扭曲着,先是抽噎,没有眼泪,久久说不出话,用那浑浊的眼光定定地看着我,直至拉着我的双手,两行热泪才夺眶而出。她老人家抚摸着我的头,边说话边擦眼泪:“森仔,你瘦了,瘦了。”
后来,我结了婚,有了女儿儿子,母亲说舒心的日子总算开始。当听到我即将转业回家乡工作的消息,她高兴地与我们一起迎接一家团圆的明天的到来。可就在我正式转业前两个月,病魔便向她无情地袭来。
母亲身体从来就好,也许应了一句话,说是平常没病,一病就要命。妈住进了医院,被诊断为鼻癌。面对当时的经济能力和医疗条件,我们的眼泪只得在肚里流。她日渐消瘦,觉察到自己的病会愈来愈重。一天,妻和姐帮她洗完澡,她说看看水珠能不能像珍珠似的滑落下来,如果不能的话就活不长了。妈说出这样的话,石头也会流泪呀!
没有那一天会让我如此捶心顿足、终身悔恨。1978年的端午节,母亲已经病入膏肓,连粽子都懒得看一眼了。初九那天,她老人家昏睡醒来,说想喝一口猪肾汤。我让姐在病床旁守护着她,赶忙骑自行车去买,跑了6里路到西河肉铺,猪肾卖完了,只得又推车上大桥到了河东,中午炖好猪肾汤送到医院。当我快步来到病房前,却传来姐呜呜的哭声。我惊呆了,炖盅掉下地,我跪在妈的病床前,拼命地摇动她的手,拼命地哭喊,而她老人家却瞪着双眼,什么话都不会说了。
那年,妈妈才60岁。她是死不瞑目呀!至今,她老人家的遗言犹在耳边:“我放不下心,小孙子才3岁哟。”
时光飞逝。妈妈辞世整整32周年了,她最牵挂的小孙子也已长成大小伙子。每年回老家,我一家子都会来到她和父亲合葬的大青石墓碑前祭拜;每年清明节,如果我们不能回去,总会委托姐去烧香,问候双亲老人。
当年,因为穷,买不起好香烟孝敬妈,妈惟有卷烟叶,孙女还捡过烟头给奶奶抽;如今,我们富裕了,却无法报答那比天高比海深的养育之恩。当我常常叨念过去那让我们后辈愧疚和懊悔的岁月时,尽管内心隐隐作痛,却为仍然健在的所有前辈感到庆幸,当然也应为所有后辈祝愿:珍惜时代、珍爱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