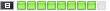文/心之初
[imga]../images/upload/2010/12/26/021733.jpg[/imga]
圣诞夜,枯坐在壁炉前,托着腮,牙在疼;看着壁炉里的火,红红烈烈,想起雪,想起白白一眼望不到边的雪。
生活在美国南方的小城,这里雪是希罕物,过七八年,或能见上一次。圣诞夜,真该有雪,应该有好大好大的雪,让圣诞夜,黑黑白白茫茫,好像天上的白云夜里下了凡。在我圣诞的印象里,圣诞老人最爱雪。
我生我长的西安,每年总要下几次雪。小时侯,每逢白雪漫天,到处银妆素裹时,我和小伙伴们就欢天喜地:天寒地冻,我们不在家里暖和着,要出来和天公比个,”惟余茫茫”,花季少年爱在雪里折腾。那时侯,我们自制一对尺来把长,十来厘米宽,底板安着两根粗铁丝的滑雪板。在雪上, 先金鸡独立,再后腿蹬地,做滑雪状,碰上地平有冰,人就飘滑在了雪上,一下一下,向前向前…虽然这间歇式的蹬滑,每次并向不了多少前,蹬好半天,快活一小会。岁月匆匆,几十年过去,却好像还记得当年的快活。当年真快活,那时我们年少。
少年不识愁滋味,少年没事爱折腾,毛主席当年是我们的贴心人,最高指示夜夜发,我们天天惊喜:“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八亿人,不斗行吗?”,问的多好?记得语文老师说,这叫设问。我们当年都铆足了劲对天斩钉截铁:不行不行不行。现在中国,十四亿人了。
人半老,像懂了些事,没事就不折腾了,爱守着火,想从前的事,无聊里,想当年的惊喜。
少年不知不折腾,无产者一生都爱穷折腾,直到把自己折腾成小老头,连胡子都白了。日子可真是一杯酒。我有时都不太清楚我的故乡是哪?在他乡,我知道:我的故乡在中国;而在中国,人常说:故乡是两辈子朝上生活的地方。可我爸我妈和他们的爸妈,都是重庆人。四九年底,他们给翻了身,不蹲不爬不躺了,听党话,别故乡,支援大西北,把我生在了西北。新中国,养个孩,很受苦,妈为我吃了很多苦。我问妈:后悔不?妈说:不后悔。西北的雪呀西北的冬,没有东北的雪大东北的冬冷?为什么?因为“人生长恨水长东”吗?
北风还那么吹呀,雪花还那么飘?三十来年前每到过年我们就都爱唱这“北风吹”,这曲子这调子特别凄婉。一晃,几十年都走了,爹早回不了家了;但我想妈,她明年八十八。妈说会听我的话,再怎么着,也要活到画圈老人那岁数。人老多病,活着得坚强,活着,为儿子不停止对故乡的思念,为儿子多回家。实在说,真就是这样,有妈在,我对故乡的思念就是真真切切,虽然我对故乡的很多么鹅子一点也不理解。去年陪妈住了两天医院,今年还做恶梦,一年过了想起,背上还出汗。我没法分担妈的病痛,今年也就写了五封信。
小时侯滑雪,有能行的,可以左右脚一起呼尔咳呦地就在雪上滑很长很长,我不能行,我老觉得自己就像只甲虫。谁曾想?三十功名尘与土后,为找八千里路的云和月,找到美国来了,没两年,儿童节后,人民政府在天安门前和自己掌控的小人民玩起了真格,让人肝肠寸断。风风雨雨风波,几十年也说不清。人生如了雨,雨过天不晴,人就呆在雨里算了,雨后总会有彩虹。
我读研究生是在美国有雪的地方,雪比西安的雪还大。我记得我在美国的第一个圣诞,那天雪真大,和个美国人住个大房,不敢开暖气,睡不着,一大清我早就哆唆着身子,去雪里练车。北风也是那个吹呀,雪花飘得不同,我在车里手排档:起步,挂档,给油。。。没了救世主,一切全都得靠自己。到美国才懂国际歌。学会开车,才能挣钱。
在南方一住十六年了,人都有些温了。想起从前,还有一丝豪迈,却很难鼓起从前的劲。怎么才能有和《热爱生命》那雪地生命的张扬一样的生命?今年这个圣诞,想雪?想看漫天白雪飘飘洒洒,想替味雪天湿润的清冷。
雪,让四季分明,让春天温暖;雪孕育来年的丰收,雪让人心里有浪漫。
壁炉里的火,快灭了;DVD机里的歌,还在唱:“我爱你白雪飘飘的北国”。百灵鸟春天才在蓝天上飞过吗?“此夜曲中闻折柳”,门外有了响动,是雪吗?推门出外,家家的彩灯都在闪闪,却只是冬雨在晰沥。
[imga]../images/upload/2010/12/26/021752.jpg[/imga]
12/26/2010
[em92][em92][em92][em92][em92][em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