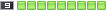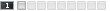回望童年
“童年呵!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冰心
放牛小子•蚂蚁
过完年,春天就来了。当春风呼隆隆地吹过,河里的冰和田里的雪就柔软起来,不知啥时就没了踪影。这时候,地里钻出一些细嫩的草芽,在地下睡了一冬的小虫子也醒来了。在我们辽南山区,最早跟我们玩的小虫子我们叫它“放牛小子”,为啥叫这个名字我们无从得知,总之娘是这么告诉我们的,娘的娘也是这么告诉娘的。
“放牛小子”是一种浑身红艳的小虫子,状似蜘蛛,但却又从没看到它结过网。或许是因为颜色扎眼的缘故,或许是因为它是经过一个漫长的冬天后我们最早见过的小活物,它也就成了我们这些孩子的最喜欢的玩物。
放牛小子个头很小,只有小米粒那么大,但跑得却很快。在早春的山野上,在一片枯色的荒原上,忽然有一些红艳艳的虫子溜溜达达地在跑,还真象放牛小子在追逐着牛呢。
在暖洋洋的太阳光里,我、二孩儿、锁柱几个孩子撅腚猫腰,趴在地上,手握着小瓶子,象抱窝的小母鸡,一动不动地,期待放牛小子爬进我们的瓶子,全然不管娘早上给我们换上的干净衣衫。这小东西实在太小了,我们的手指在它们面前则是庞然大物,稍微一动,都会把它们碾为尘土。无奈,只好用棍子驱赶,让它们自己爬到瓶子里去。
我的棍子根本不管用,因为放牛小子太小,打不得,骂不听,它总是沿着自己的路线走。二孩儿的法子倒很灵验。他用一只脏呼呼的小黑手挡在放牛小子的前面,便成为了它的山梁,放牛小子便挺着胸膛向前爬去。当它攀上二孩儿黑白相间的小手指,二孩儿便抬起手,将手指塞进了玻璃瓶里,放牛小子架不住山脊的抖动,便翻身掉进了瓶底。这样的采集,着实使我们这三个四五岁的孩子忙乎了半天,直到下半晌,浑身若泥猴子般的我们拿着逮到的四、五十个放牛小子去找蚂蚁。
蚂蚁到处都有,在田间,在地头,在路边。随便翻开一块石头,一窝一窝乱洋洋的蚂蚁吵吵闹闹地就出现在我们的眼前。锁柱找了一窝跟放牛小子差不多大的小蚂蚁,打开瓶子,把放牛小子放进蚂蚁窝,我们想看它们打架,想知道它们谁更厉害。
四五十个鲜红的放牛小子在一群黑色的小蚂蚁中格外扎眼,可与庞大的蚂蚁家族相比,它们显得很孤单,很渺小。它们的胆子真小,在密密麻麻的蚂蚁围攻下,竟然会惊慌失措,四处逃窜。而小蚂蚁则象一批泼皮流氓,一拥而上,咬的咬,夹的夹,不大一会功夫,我们那些红衣小子,竟然丢盔卸甲,溃不成军!真为它们丢脸,瞧它们那畏畏缩缩的窝囊样子,连点反抗精神都没用,英雄做不了,连狗熊都做不成,白穿一身鲜亮的衣裳了,真是中看不中用!而二孩儿也愤怒起来,他气那些蚂蚁,仗着人多势众,一派无赖相。当一群蚂蚁扛着跟它们个头差不多的放牛小子一路趾高气扬地回巢的时候,二孩儿愤怒地擤出他那两筒黄呼呼的大鼻涕,甩在蚂蚁身上,我们看到十几个小蚂蚁被黏糊糊的鼻涕黏住,挣扎着、惊恐地挪不开身子,开怀大笑。而锁柱更绝,从裤裆里掏出家伙,一帘瀑布便飞溅下来。那成百上千只蚂蚁霎时遭遇了洪水之灾,我想它们一定老害怕了,不然它们干嘛扔下战利品在水里拼命挣扎?不过这些小家伙还真顽强,它们一个一个拥挤在一起,为另一些蚂蚁搭起了浮桥,于是便有一些蚂蚁逃离了苦海。
“放牛小子”为啥就不能学学蚂蚁?它们独来独往,多没意思啊!看人家蚂蚁,遇到敌人就大家一起不管不顾地往上冲,全都是一副不要命的赖皮架势,所以他们的阵容才能发展的那么强大吧!刚才那也是几十只放牛小子哦,如果它们能团结起来一起与蚂蚁厮杀,或许不会死得那么惨、那么快吧!
放牛小子真傻,我决定从此再也不理它们了!
刀螂•机匠•蚂蚱
当小草长出了大叶子变成了蒿草,当桃花谢了长出了青涩的果子,当太阳把我们身上厚厚的衣服扒掉,让我们光着胸膛在田野里疯跑,这时候刀螂就出来了。烈日炎炎的午后,就在我爷爷奶奶们坐在老槐树下耷拉着脑袋眼皮打架的时候,田里的庄稼、山上的树叶也因太阳的灼热蔫巴起来。这时候刀螂也没了力气,死眉耷眼地躲在树叶下、草丛里打瞌睡,而我们捉刀螂的时刻也就到来了。
刀螂,就是所谓的螳螂。因为它长着两只镰刀一样锋锐的大前爪,所以我家乡的人都叫它“刀螂”。
刀螂有好几种,那种浑身灰土土、个头小,身子细的刀螂,长得磕碜,俺们是不屑一顾的。而另一种褐色身子夹杂着绿色波纹的刀螂总让我们感到不清爽,好像它们生下来就没洗过脸似的,我们也不搭理它们。我喜欢的是那种长得魁梧英俊,浑身碧绿,肚大体壮的那种,它们挥舞起两只大镰刀像骁勇的武士。
扒开细密的草丛,掀开茂盛的树叶,那大脑袋、细脖子、大肚子、浑身碧绿的大刀螂就会挥舞着两只大镰刀向我们示威了。
我一直弄不懂刀螂那么纤细的脖子是怎样扛起那只巨大的脑袋的,还有它的两只跟蜻蜓一样的大眼睛,总是恨恨地瞪着我们。不用担心它们那双大砍刀抽冷地就会向我们劈来,因为这时候,它很老实,仿佛正午的阳光吸干了它们身上所有的力气,它们很少挣扎,也不威风,任我们抓来摆去的,它们心里一定很生气,很害怕,它们的那双大眼睛里一定印着愤怒,可我们是不会理会刀螂的感受的。三胖子从家里带来一个破瓦盆,我们将捉到的刀螂放进去,浇上几滴凉水,刀螂们便立马精神起来,瞪着眼睛、乍着翅膀,挥舞着大钳子,你一刀,我一拳,两只刀螂就干起架来。而我们一帮孩子趴在地上,围着破瓦盆,叽里哇啦地使劲地吆喝,都希望自己的刀螂能够取胜。二孩儿的刀螂战胜了三胖的刀螂,带弟的又战胜二孩儿的刀螂,最后,我的大“金钩”战胜了他们所有的刀螂,取得胜利!埋怨、气闷、得意、喊叫,在夏日强烈的阳光里,我们的心情也燥了起来。
而失意与狂躁不会持续多久,我们就会在飘着浓香的瓦盆边兴奋起来。一群孩子偎在在瓦盆边,眼睛盯着盆里烧的刀螂,炭火劈劈啪啪地响,那些肥硕的刀螂在火炭的炙烤下,塞满焦黄籽儿的大肚子开始“呲啦、呲啦”地冒油,那浓烈的香味在空气中弥漫,急号号的我们便顾不了火的炙烤,伸着黑乎乎的手探到火中抓出刀螂,两只手不断地倒着,烫得“嘶喽、嘶喽”地叫着,然后迫不及待地塞进口中,顾不得斯文,顾不得烫人,那喷香喷香的味道,真是让人垂涎欲滴。
我一直不知道“机匠”这种昆虫它的学名叫什么,它是一种跟螳螂相似的昆虫。它们的个头也差不多,也是通体绿色,长着长长的触角。不同的是,“机匠”头是方形的,伸出的嘴老长老长,像我奶奶嘴里吧嗒的烟袋杆。螳螂的两只前腿发达,靠两只大刀一样的前爪战斗捕食,而“机匠”则靠后腿的劲力跑跳如飞。它们的两只后腿长而粗壮,跳起的高度在一米以上,是个地道的跳高运动员,因而捉“机匠”的难度自然就比捉螳螂难上很多。
在露水浓重的早上,太阳还没从我家对面的山脊后钻出来,锁柱就来我家喊我来了。一大清早,刚从炕上爬起来的疯孩子,头不梳,脸没洗,饭不吃,就跑后山根儿捉“机匠”了。刚冒头的阳光,把千万个草尖上的露珠反射成千万个小太阳,小太阳在被我们的脚下踏碎了,它们的眼泪打湿了我们裤腿和鞋子。这时候,“机匠”就蹦跶不起来了,它们背着沉重的露珠就如背着沉重的苦难。它们盼望着太阳光早点照耀到它们的身上,烤干它们的翅膀,烤干它们的苦难,然后它们就可以挥洒自如地飞、自由自在地跳了!
面对我们这样一群孩子,它们的灾难来临了!草甸子上,一个“机匠”趴在草棵子里,它们跟草混杂在一起,一动不动,企图躲过敌人的眼睛。可我们是谁啊,山里的孩子,个个都火眼金睛呢,不消精意去找,脚丫子在草棵子里一顿倒腾,那些“机匠”就自己爬出来了。这时候,不用费力,手掌一拍,“机匠”边老老实实地落到我们手中。
玩“机匠”的乐趣在于这东西会磕头。就像过年的时候我们跪在炕上给老奶奶磕头作揖一样,用手捏紧它的两只粗壮有力的后脚,“机匠”便一颠儿一颠儿地点头哈腰了。“机匠”磕头的样子真有趣,身体用力前挺,脑袋使劲向下,一撅一跳的,个个都是磕响头的招式,这让我们很开心,我们甘心情愿地接受着机匠的受礼。
“机匠机匠你织布,给我闺女织个花棉裤……”这样的歌谣我不知听到母亲唱过多少遍,也许,这叫“机匠”的虫子就是跟真正的机匠织布差不多?我没有看过机匠是如何织布的,因为如今的花洋布比那老粗布好看多了,谁还穿那机织的老粗布啊?所以我们只知道村东头狗剩的爷爷是老机匠,可我们从来没看过他怎样织布!连狗剩都没看过!
让我们发烦的是蚂蚱。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的长相难看,灰不溜秋的短身子,四方头,一张硕大的嘴上龇着两只大黑牙。让我们生气的是它们忒能吃,那张大嘴巴永远也吃不饱,专门祸害庄稼,好好的一畦谷子,不大一会儿,就被它们啃得精光。它们的家族十分庞大,比蚂蚁还多,而且会飞,吃完了这块田里的,就飞到另一块田里。天气干旱的日子里,它们更加猖狂,傍晚的天光里,它们飞来飞去,铺天盖地的。奶奶说它们就是官话说的蝗虫,蝗虫泛滥的年头里,我们的肚子就吃不饱了。我们村里的人们都恨它们,以至于我姐姐他们小学校各班都布置了一道相同的作业,就是每个学生每天必须捉20只蚂蚱。
夏日的傍晚,田间地头、荒山草甸,都能看到我们捉蚂蚱的身影。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吵吵嚷嚷、疯疯闹闹提着瓶子、拿着袋子,抡着树枝、笤帚,撵着蚂蚱拍、打,那小东西其实能跳能飞,只是太多了,捉它们很容易。用长着厚厚实实、密密麻麻松针的松树枝子拍,一下就能拍死五六只。有时候我们干脆放火烧,捡来一些枯枝烂叶均匀地散在草甸上,放火点燃,火苗就会迅速蔓延。那些蚂蚱们在火和浓烟中仓皇地跳跃着,挣扎着,霎时间就全部葬身火海,顷刻间就化为灰烬。
蚂蚱是我们所不齿的东西,只有鸡们才把它们作为美食。家里的鸡每天都能得到这样一顿大餐,因而它们也拼命长肉,使劲地下蛋。吃了蚂蚱的鸡下的蛋个头大,而且双黄的居多,蛋黄都是红黄色的,特别的香。母亲把积攒下来的鸡蛋拿到集市上卖,就会给我们换来花布衣裳和新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