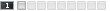老屋檐下燕窠(下)
刘荒田
(紧接上文)我坐下,風從巷子的尾端灌入,呼呼吹動春衫。得其門而不能入的歸人,和遙遠的記憶成為貼鄰。緊閉的大門仍舊結實,儘管已露出萬千條紋路,似老人手上的青筋。門旁邊,青磚牆壁上有兩個窗戶,我踮起腳,窺看我知青年代的讀書處,我和妻子的洞房,兩個兒女從襁褓到學步、學語的所在。那時,我愛在午夜在陽台上遙望廣漠大地之上,由銀河所搭建的凱旋門;愛在子夜起床讀書,晨曦從窗子透入,在光的瀑布裡,遙看碉樓奮力撐起的深藍色天空。如今木窗已朽爛,所嵌的玻璃碎了半邊,颱風暴雨襲來時,裡面肯定變為澤國。人去樓空的虛無,不在無人,而在緩慢而難以遏止也無法修復的廢圮。我往裡頭張望,帶綠苔的青磚牆壁後,龐大無比的黑洞。我進不了家門,進不了往昔,進不了鄉愁。
錄影機開始運轉,我略略整理了稀疏的斑白髮,清清喉嚨。明知道這形象絕對地沒看頭,但好歹要開始了。我對著扣在襯衫領口下的微型麥克風說話。說什麼?有什麼非說不可?我壓根兒忘記舌頭的運動——因了抬眼時,看到門楣上兩個泥窠!它們占據趟櫳之上左右兩個角,遮蓋了工匠畫的花鳥。我眼睛一熱,死死盯著檐下,不發一言。錄影機停下來。
我差點對手拿錄影機的人作一番離題甚遠的發揮:我的兒子剛滿一歲,在禾堂蹣跚學步的時光,一天早上,我在屋裡讀書,五、六位女鄉親在禾堂搬運泡過的稻種,忽然聽到「小門口」外起了騷動,我惦記著交給鄰居蓮媽媽照看的兒子,立馬跑出房間,隔著趟櫳的圓柱,看到傻頭傻腦的兒子站在門前石板上,他仰頭盯著一個老婦人。老婦人就是腰駝成四十五度角的蓮媽媽,她正艱難地爬上看場人坐的長凳。我慌忙拉開趟櫳,走出來,看個究竟,蓮媽媽專注地高舉合成蓮花形狀的兩隻手掌,掌內是兩隻啾啾哀叫的雛燕。我馬上明白了來龍去脈——小燕子從巢裡掉下來。我大聲勸阻走平路也不容易的蓮媽媽,要她下來。她不搭理,只說:「快好了,乖乖,回家去。」終於,她的手搆上泥巢,小心把剛長出白色粗硬羽毛的雛鳥放進去。我扶著長凳,讓她下來。懵懂的兒子拍手歡呼。雛燕回家的春天,已消逝三十多年。眼前還是那泥巢嗎?我終於恍然大悟:進村後若有所失,就是為了看不到燕子。恐怕到下月,燕子才回到窩裡來。
我不知道採訪是如何完成的。把椅子交還給波嫂的陳主任揩揩汗,鬆了口長氣,為了活計終於收了尾。餘下的是剪輯,配上音樂和字幕之類。我沒問他效果怎樣,也沒請求他在節目播出後給我寄上一張CD。我只是要像早已辭世的蓮媽媽昔年呵護雛鳥一般,找一個心靈的「小門口」,儲存我的鄉村,我的出發地。
(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