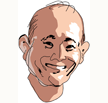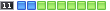文/心之初
今年的春,来得姗姗。冬天到的时候,我就盼着春天不要太远。去冬还没来时,我就在常在心里盘算,开春后的园子里要干些啥,种些瓜,种些菜,种些花。春天是生命又生的季节,也是种植生命的季节。种下些生命并天天照料,为了是“见不着南山”,也能有点悠然。
站在了人生的半山腰。学着拥有拥有,学着悠然悠然。本想种些牡丹呵牡丹,但又听说牡丹怕热,于是就种些牡丹的俾女---玫瑰,这玫瑰大概不铿镪吧?但我期盼它们鲜艳。花圃上我全撒上了絳红的木屑。后院已是花红叶绿。
春暖鸟叫,有空我就爱在家呆着,呆着有时就发呆:在家送时间走的最好办法,就是翻书灌园,一动一静,悠然自得。随手翻开本《中华散文珍藏本》的牛汉卷,我又被打着桔红印的话吸引,这位历经坎坷而又童心依然的和闻捷差不多高的牛汉那首没写完的诗,我每次去读每次都感动:
记忆是一条弯弯曲曲的长长的河流
隐没在遥远的永远不能再进入的尘雾里
它的源头是母亲一滴一滴的乳汁
我看不不见生命的源头
但直到现在
仍听得见母亲乳汁叩响的第一声记忆……..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喜欢他的这几行诗,每次都读得心头怦怦跳动。今年开始,已经八十七岁的老妈妈每个月都给我写一封信,然后就开始她的期盼。一种沉沉的感觉,时时压在我的心上。这万里之外,我能给妈,做点什么呢?妈说,她不要钱。老母亲现在几乎什么都不能吃了,但心还在每天跳,经常还激动,是生命在往回走吗?
爱,这样难?我认真回妈妈的信,但我常不知道该写出怎样的信让母亲感到安慰?那么些艰难的岁月,是怎么走的?我真记不得吃妈妈第一口奶时的感觉了;不过,我相信,我一定吃过,因为那味道,常常在我的梦里出现。想起,心里就是甜的,不管和妈有多远。
我有不少中文书,打算从今年起,读完一本就扔一本,也不知到我“一路走好或走不好”时,能不能把书架上的这些书全都读完,扔完。我不期盼“满卷诗书喜欲狂”了,故国月明中。说是“书到用时方恨少”,但好些中文书怕是没有用的时侯了。要能把书读到用时不用找,该多好?好书该和命读到一起并化作独一无二的思想。幸福不是毛毛雨,人生不过毛毛虫。
虎年春情节前,我就种了好些红蛋蛋小萝卜,如今已然很茁壮了。小萝卜拌上粉丝,弄上酱肉,摊上两张春韭软饼,用土尔其酒杯乘上美国红葡萄酒,看着老婆的杏眼,望着她的柳眉,吹着我的新牛;窗外,落日悬着,晚霞挂着,一片血红。黄昏挺好。商隐当年的“意”也不知干嘛不适?两天前翻看《李商隐大传》,才知道穷苦少年李商隐也有“维特之烦恼”。还知道了点温钟馗。“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写这般婉约词的人原来并不伟岸好看。
第二天,星期六,老婆居然起得比我还早。昨夜我九点不到就睡了,她去别人家挖韭菜。“春眠不觉晓”,吃韭(菜)要趁早,宁吃春韭一撮,不吃秋韭一堆。“一虾二肉三韭”的饺子,是我家三口的共爱。现在,这世上充满了爱,但在俩“五0后”一“八0后”的家,能有那么点共爱,就该烧香了。我伸个懒腰,眼一瞄,小山似的韭菜早已洗好摘好堆上厨房的“长岛”,下午饭的韭菜饺,够我差不多折腾俩钟头,先不管。
浇花浇菜好像要晓浇,“莫道君行早”。太阳冉冉在探头,我一手拎水管,一边看东方,一并听鸟叫,不时伸懒腰。韭菜迎着太阳在长,小葱站在两旁发呆,番茄苗一天一个样了,窝笋仰天大笑,黄瓜架子已搭起,苗还没出。红蛋蛋的萝卜樱在晨风里扭,大木耳菜明天该出苗?养个狗像自己生的,种的菜当然也是自己养的。培育个生命,便也多懂点了生命。我们是生命,我们该懂我们。
早饭吃个茶鸡蛋,翻到贾平凹的《哭三毛》,三毛死得奇奇怪怪,就像好作家的情怀。老贾老三都痴爱中华文字,彼此欣赏彼此文章。俩人好像没能见上一面,三毛就勇敢地走了。死前却专门写信告诉老贾:你名字中的“凹”普通话里要读AO。陕西人大多都跟你读WA(说是贾平娃自己就读WA)。AO还是WA,其实不重要,我们就正处乱读时代。
三毛死了,但她那灵动激情,旷达纯朴的文字还在。我没力气走很多地方,偶读读三毛的那些游记随笔便也能知道好多这世上的好地方的一二。三毛的信,贾平凹一读就想哭,他想和三毛角交换交换灵魂,是呵,世上通过文字而互相敬重的人是该交换灵魂。灵魂是人的最真。月有阴阳圆缺;人有阴阳两隔。生者和死者,彼此尊重。灵魂不死。文字是最清澈表达情感和思想的。
花开春暖好眠眠,但眠眠太多对人不好;人该和草一样,在春风里又生,在太阳下向阳。但人和草不同,人会翻书灌园,不让水往脑里流,不让草往心里长。
4/13/2010
[em39][em39][em39][em39][em39][em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