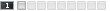(三) (3)
自然喽,吴桂圆不会知道,放封之後,那个做妻子经历怎样?故事不是夫妻
俩自说自话透露的秘密。叫庚九妹的女人的个人肉体与心灵的感受,都不是她吴桂圆可以推测出来的。
放封那刻,庚九妹在感受腰疼背痛里感受腰眼难耐的胀痛剌激,像所有女人一样(後来知道共有六个女性) ,忍不住肚腹胀裂,不自顾羞耻跌伏在黑箱底下,然後气急败坏蹲俯下来解放内急。那阵间感觉腿眼如神采飞扬,压迫感慢慢髮弛了,被解脱的精神在喷发中飞扬,腰腹和腿眼之痛化作虚无,心灵呢反而像断线的风筝飘浮,感性的快意尚未令理性觉醒,整副身体变得輭绵无力。当意识和感觉迷离之时,她收束著牛仔裤腰,也收束了胯下腿眼的神和气。她抬头就望见了阳光如针灸刺入感觉,感觉令理性觉悟,心眼感觉的解放之感也瞬间飘离,连处境的真实身体在哪里也尚未理解,连船影浮起又沉伏的姿态都未清楚看到。她想爬起到丈夫身边,已无能力了。被蛇船仔搀扶起来之时,她被他孭上背之时,她祇无可奈何的望著他的肩膀。她恐慌的心一直想:蛇船仔带我去见医生吗?放风後我会回到黑箱来吗?然後呢,然後。都是後来的感受和遭遇了,走进命运的註解里,刻骨铭心。
複杂的记忆仍然打彼处发生又从这里开始,诉说的都是偷渡的思维和感动,因此记忆极其清晰但複杂。但都成为定局了。记忆刚才跌撞黑箱外解放的情景,小解带来四肢百骸的解放,都是知羞耻又莫可奈何的…她终於认可被这个蛇头仔孭进一个地方,放在一张软垫上。有人抽动自己的手和脚放在牀上。她感觉自己躺卧牀上,矇胧中看出这里是房间,知道孭自己的蛇船仔离开房间。现在,细心放自己身体的人应该是医生了。记忆回到心田。回想船怎样颠簸身体,怎样头晕脑胀和酸痛无力,感觉身体发烧,但感受的真实远比黑箱舒畅千百倍不止。那时呢,多渴望眼前的人是医生。接著,她被他抱著睡在软软的牀塾上。船靠荷兰国码头,还是靠甚麽加勒比海甚麽岛国码头?然後登上飞机直飞美国还是甚麽地方?…但愿船直航纽约码头。矇矓矓听到有人说话。意识是医生。睁眼就见到医生了,原来就是那个说话文雅的甚麽船官。凶神恶煞的蛇船仔站在牀边。蛇船仔也穿了一身医生白袍。
「妳排洩障碍,加之晕浪,所以病喽!」船官医生说。
她在枕上听,默认。
「女人容易生病,吃药之後妳感觉会好些。」船官医生说。
确定船官真是医生,告诉他我月信变化可以吗?两个月没有月经,我想是怀孕了…渡过茫茫大海…我怎办?她用双臂撑著腰股,想坐起来。
「甭动,我们要给妳打针服药。」心里认定的医生说。
「谢谢医生。」她对著医生说。
「大令Q,帮忙给女人打针服药。」心里认定的医生说。
「尊命,贺西大副。」已经站到牀边的蛇船仔答道。
「大令Q,这趟船这麽多女病号?货柜空调坏掉?」别洛克西的大副声音。
「夹顿,这无关我责任呀。那是机长和电工的问题。」蛇船仔答道。
听到蛇船仔甚麽「大令Q」的怪称呼,认定的医生是大副叫甚麽「贺死」(?)她想马上坐起来,但不能。她看到叫克死的大副原来是洋鬼,人倒和颜悦色。他朝她扬起左手,拿著打针筒的右手示意,指示她转动身体,他要在她股屁打针。她没有转动身体的动作。
在陌生人面前裸裎露体,怎做都是羞赧的,她感觉自己脸孔热辣辣。
「妳没有见过医生打过针?」大副问。
大副又示意她转过身体背向他。她还是没有动作。
「我治病救人呀!妳有病不治等死吗?」但听叫大令Q的蛇船仔说。
大副表情有些忿意,又示意她转过身体背向他。她还是没有动作。
「妳想未踏上美国就赔掉命,值得吗?」大令Q说。
「叫他离开房间可以吗?」她终於说话了。
「他是船上服侍你们食宿的船倌,他现在照顾妳身体。」大副说。
她听到这话惘然了。
「你们中国人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懂吗?」大副说。
但见大副拿著针筒弯下腰,示意蛇船仔给她转动身体。从此她祇好万般无奈地化被动为主动。在两个陌生男人面前褪下穿得札札实实的牛仔裤,好不容易褪出腰股,多麽难为情!背著身体,感受了一阵子微微的剌痛,感觉剌痛之後退出针筒,感觉人家在屁股上擦药液,有些微的药味飞进鼻孔。
「打针完毕,妳好好休息吧。」大副说。
她匆忙为自己收束裤子,把羞耻掩饰。
「大令Q,去打桶水来,给病人清洁。她浑身发臭啊!」大副又说。
「尊命!」但见大令Q还朝大副敬了过个军礼。
但见蛇船仔大令Q跨开步走了,随手关了房门。
「妳可以在这里休息,直到病好。」大副坐下来安慰她。
「大副医生,很感谢您。」
「不谢。大家都是中国人。」大副说,他朝她绉了下鼻子,又说:「蛇船仔打水回来,妳好好抹洗身体,然後好好休息,懂吗?」
「哦…大副医生,多谢您啊!」她是由衷感动了。
「不谢,身体好,甚麽都可以做。」大副还是这句话。
蛇船仔大令Q打水回来时,她已经感觉体内药力功效了,感觉的不止肚腹内轻松舒畅,由脐眼而下慢慢有股微微浸浸的温暖,令她全身舒畅。舒适之感慢慢充满全身,令她因之不由自己的在牀上舒坦四肢。那股从未有过的温暖流荡身体,脑海充满的快意把身体俘虏,彷彿把偷渡的豪情壮志带到眼前,生命力无限的昇华也在体内爆发,令她连思想药力功效属於治疗还是药力驱动的生理感觉都被俘虏了。生理感觉本身盛载的反应,慢慢令她在被俘虏的感受中变得无所适从,惟独腿眼的温暖令身心无限舒畅。独立的思绪随心所欲,驾驭的生理现象却告诉心灵,多麽渴望被丈夫紧紧拥抱,然後好好睡一觉。多少日子以来心灵给紧急的行动控制。突然知道月信未来之时,兴奋和慾念都随偷渡发烧了。
(带著沉重的心思偷渡,怎想都不是心甘情愿。汪洋大海祇在感觉中 随波涛起伏,想念的彼岸渡头是英国还是荷兰还是美国?不知道。此刻心灵 飞到哪里呢?我的心又回到黑箱。心灵沉沉欲睡的感觉黑暗无边。黑箱空气 比童年蹲茅坑呼吸的还浑浊,抵禦蹲俯黑箱的困苦难耐,好像把生命力全部 消耗。大令Q凶神恶煞令所有人惊畏,他手上那根电棒像公安,比童年那 在县政府见到母亲被公安拳打脚踢还凶险!…船长打的甚麽药液呢?他真是 医生吗?一针就令人身心舒爽。但温暖之感为甚麽令我魂不守舍呢…大副医 生打的是甚麽针呢?哦哦…我怎办呢!?…)
可是,她的感觉不受意志控制。她多想好好睡一觉,睡醒後好好感谢船上医生。然而,就是心灵无法掌握想睡的意念,她微微张开的眸子,令她身轻如燕飞腾。那时候她知是适才医生打针的药力发作,浑身感觉温热难耐。大副是在此时进来。她万分慌乱的背转身体不敢望大副,後来大副来到牀前,她都无暇思想了。
「打针後妳很舒服,是吧。给妳服药,不再呕吐,身体感觉特别舒爽,是吗
?」大副的态度十足亲切。
她没有回答大副,祇把心思收藏。
「我给妳洗身後,妳会更舒服。」大副微笑说。
「我不想洗。」她下意识的决定,回答。
「不能不洗身,妳困在黑箱一个半月了。女人叁日不洗浑身难受。现在妳享受其他人没有的特权。」大副微笑说。
「…」她不想说心里感觉,那时感受的是感觉与理性的矛盾。
「静心下来,我给妳抹拭身体。」大副是命令的口吻,口气也亲切。
(丈夫啊…)她在意识里叫了丈夫原家镇,瞳孔里照著大副的神情。
「乖乖,做完後好好休息。」大副亲切的声音。
「医生,你究竟想幹甚麽?」她突然把意识说了。
「为了可怜妳。」大副说:「妳不能败坏身体偷渡吧?不人道的遭遇是妳做梦也想不到的,妳感受如何?」
「…」听到这话,她整副心魂错乱,理性也瞬间崩溃。
「乖乖,让我帮助妳。」大副说。
「请问你叫甚麽?是不是医生?…」打哪里来的心思呢?都是女人天性了。
「就叫我大副呗,也是船上大夫。妳我萍水相逢,一面之缘随波逐流,谁还知道谁是谁记住谁,是不是?」大副敢情地说。
「我有男人。」也不知为甚麽说这话?像由天而降的心理,在此时此地还是会想起丈。
「妳先生?妳有先生…我没有这个权利照顾妳先生。」大副说。
「毛巾给我,我自己洗。」她这样要求大副。
「妳身体弱,我来帮妳洗。」大副命令也似说道。
「好,我不想反抗,我给你权利,但你回答我你是哪里人?你可以保證我和丈夫到美国吗?」她突然这样说。
「我祇可以保护妳到最近的岛屿码头,未来的路祇有听天由命,所有人都是
这样。」大副说。
「这条船从哪里来?」她固执地问他。
「我祇能让妳知道我是台湾人,管船是哪里。」大副说。
「台湾人!你能保护我吗?」她衝口说了。
「现在我是爱护妳,给妳治病。」大副说道。
(哦…)她打心里哦著,无可奈何望著大副。像刚才给她打针时一样,他示意她把身体转动背向他,藉於掩饰她的羞赧。她未动弹,面对著他,祇好随他为所欲为了。她著他右手开始扳动自己身体,让腰肢背向他的手动作和毛巾移动的感觉。而那时呢,她心灵完全知会药液作用,生理是本能反应,令她在心灵深处体会羞耻与抗拒的无奈。矇矓中看到的是戴军帽穿白袍的身影,意识告诉心灵是适才给她打针服药的大副。但见大副随手关了房门。她听到关门声,大副走近牀第。大副弯腰,他双手抽起毛巾水珠淋漓,又用手挤压,站到牀边坐下来了。在一阵垫褥起伏後,乍地心在胸脯里鹿撞,羞耻载後知後觉,猛然袭来的意识在心灵窜动,想逃避的惆怅令她无所适从。矇矓间见到大副双手朝空中搧了搧白毛巾,她刹时也感觉灑在自己脸庞上微微的水寒。但浑身仍然被温暖浸透,暖意在腿眼脉源牵动搏动,把意识如迷样地昇华,如似自我倾吐窃窃私语。迷矇里看著大副右手拿去他头上的海军帽,他昂下头脸像朝空气沉思。他的眼镜闪烁。她的瞳孔映射著神经,如江水淹大堤淹淹息息,令她静动毫无掩饰,连羞赧的袭击也是多馀的。…後来又是谁的身体压迫呢?衝击自己肢体和腿眼的击逼动感,直到真实的痛苦袭来,心灵笼罩著无限羞耻和恐惧。
那时她痛哭失声了,心灵的的羞耻澎涨而跌宕下陷,让她突然见到自己的狼狈不堪。…她恍恍惚惚见到自己跌仆厰房,从厰房地上爬起,给强暴的厰长啪啪两个耳光,後来就亡命地逃出厰房。自己怎样回到家里也不清楚。秋日照著落叶飘飘忽忽。她看到丈夫站在祖屋台阶上望著她。…而此刻被占据後的身体觉醒呢,波浪翻腾似铺天盖地笼罩下来。她恍惚惚又望到波涛远处那个大副垂首望著她的胴体。但最终甚麽都消失,连波涛都毫无声息,台湾大副随她的羞赧被淹没。
一九九九年二月九日北卡森林镇笔记
二00五年元月十五日初稿於查尔斯敦散仔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