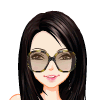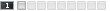捧着白百合的她上了车,车远去,程禹站在街角望着那辆车和后车窗上她的背影,车逐渐消失,这一次,她又忘记了回头……
他习惯了以这种缄默伫立的姿势站在她的身后,习惯了用这种宁静端望的目光跟随着她和她的影子……
程雨回到家,把百合花装在阔口的柱形玻璃花瓶里,安置在卧房的书桌上。
临桌而坐,对着百合,对着那两本日记簿,她从行李包侧袋里取出那封信,一并摆在桌子上。
她的思绪奔扑,忽前忽后,忽上忽下,莽撞了好一阵,才慢慢地安静下来。
她拿起信,抽去信笺,把信封放在眼前,那个名字,影影绰绰,幻绎成一个身影,一个眼神,一曲琴声,一方纸条……片刻之后,那些影像、那些印痕、那些气韵渐渐淡化,最终回到两个字:“程禹”……她把信封对折起来,一折再折,然后在桌边放手:那方形纸块落下,仿佛一叠昨天。纸篓里传出“倏”的一声,那个名字,带着所有的梦都从她心间穿梭而逝。
那两页信笺像要诉说些什么,微启着一道缝隙。她铺开,摩挲着:
[B]程禹:这封信迟到了五年……[/B]
[ALIGN=CENTER]错身而过 [/ALIGN]
拖起行囊,拖起离乡的路。飞机起落的地方,连接出对另一个国度的陌生和惶恐。
等候登机,房间低矮,令人窒息。冰冷的长椅上,捧出你的一册册日记,你十几年的一路无言终于在我寂静的心房里隆隆地开启。
旋开笔,面对苍白的信封,踌躇。怎样才能写你的名字,端庄而郑重?
即将离去。能否,一笔一画,写的你的名字;写我对你,一声一声的呼唤。
蹒跚着,挣扎着,不敢投入信箱的,是你的悲哀,我的无奈。
倘若,这是最后的投寄,谁能告诉我:能否割断你十几年的苦待?能否颠覆你十几年的固执?能否阻隔你十几年的爱恋?能否结束你十几年的对我的想念?
十几年前,倘若你能握我的手,今天 ,我们是否会有自己文香墨韵的家园?十几年后,倘若你喘息着冲进离境大厅的门口,拉住我的衣襟,阻拦我的离开,不顾一切,现在我是否会跟你一起,回归我们的国土?
我们的缘份,是否,永远一路无言?
十几年的坚持,十几年的执着,十几年的青春,十几年的祈祷,十几年的一往深情。假如,你等来的是:我的一个信笺,一个祝福,一个抱歉, 一个再见,你是否会停足不前?是否会继续一路无言?
开始无法休止的流浪,海角天涯,我载着你的遗憾,我的伤感,孤独飞翔,你我是孤独的左右两翅么?只能一生相望?
你还在呼唤么?你还在远望么?你还在苦守着一个名字和一桩心事等候么?
草黄了,花谢了,水瘦了,山也老了,鸟也倦了,你的沉默还没有打破。
我应该把你收藏在我动脉和静脉交错汇集的地方?还是应该寄给你我曾搁浅许久的希望,写上幻念里幸福的注脚?
每一个月台上,车来车往。
万里之遥,你在老地方等待月圆,还是在穿梭中寻找花开?你沉睡着,还是清醒着?我带伤而去,留给你是红尘不减渺茫的愁醉,还是柳暗花明推云见月的新夜?
那个我的名字盛开在你日记的第十几年的凌晨,临屏写你,写你十几年的一路无言,手边你日记表决:我们的故事不曾凋零,依旧和你的生命一起延伸。
这一本本日记的纸页上--你的倾诉:当眺望褴褛成等待,当等待固执成痴滞;当岁月沉积成回忆,当回忆褪色成忘却,你还在原来的地方,为我站成一块不老的岩石。
即使,我们今生只能乘坐错身而过的列车?
你能否开口?能否告诉我梦和现实的距离?能否指引我看见北斗,看见黎明,看见你的心声?你,能够,合起你的一路无言,搂住我心底的彷徨,陪我一起走?
你一路无言,叫我不敢回望,你没有告诉我,要怎样缝补你生命中的这个十几年。也许,我承载不起。
又一辆蜿蜒的列车叩轨而来。许多蒙尘的季节仿佛在它身后长啸而逝。
步入徐徐开启的车门,还是让它擦肩而去?越是不想牵拌你,却越是被你牵拌。越是不愿你纠葛,却越是被你纠葛。
我又如何知晓:哪一个月台我应拾阶而上?哪一辆列车我应重启脚步?
读懂你的十几年之后,我的心是否还会飞?你的心是否已经不堪疲惫?
人们都说:走过,路过,别错过。
错过了你,错过了自己,我还可以再错过谁?
她抚摸日记本上蓝色的丝带,长长叹出一口气,轻轻拉开蝴蝶结,再拿起展平的信笺,夹进去。把日记本抱在胸前怔怔一会儿,放下。再仔细把丝带打成蝴蝶结,最后把日记本推到百合花下。
她起身离开。
桌上,百合与蓝丝带映衬,寂静的唯美,仿佛独自走远的诗句……
[img]../images/fileType/jpg.gif[/img]此主题相关图片
[imga]../images/upload/2010/01/29/012114.jpg[/img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