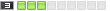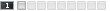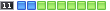相较于社会的发展变革,有一些东西是缓慢甚而静止的,那是传统,仁和,美善,那是最中国化的东西,它们在一代代中国人的心里,和灵性和快乐和爱在一起。
——题记
有些喜欢是宿命。见了就欢喜,从心灵到毛孔无一不熨帖,是一种没来由的欢喜。静日玉生烟,只觉得心里满满,忍不住想要啸歌,想要告诉人,还怪责别人的无知无觉:这么好,你难道不觉得?青山妩媚,渌水荡漾,满目春可爱,那姹紫嫣红一直地开,太阳底下世界和暖可亲,叫一声连鸟儿鱼儿都会答应似的。所以,看人有一见钟情之说,观物有物我相忘之境。
有些喜欢是渗透。初始不觉得怎样,见之恍若未见,思虑里没它,视域里不纳,只知道它在。就像画里的飞白,是一种空空的存在,你见,或者不见,它就在那里,不悲不喜。突然有一天发现,见时不觉得怎样,没时却心里空空,俯仰走卧已离不开它,梦里醒里心心念念都是它。这时,那空白已悄悄幻化为空气,不独渗入生活,就连血液里也有了它汩汩的流动。
戏曲于我,仿佛宿命。“遍青山啼红了杜鹃”,是啊是啊,啼红了呀!“那荼蘼外,烟丝醉软”,看见了看见了,那轻烟可真是丝丝的细,柔柔的软,醉得人心儿都化成了水。“那牡丹虽好,他春归怎占的先”,可不是么?他怎占的先?难为你问得这么有情致!“闲凝眄,听生生燕语明如剪,听呖呖莺歌溜的圆”,一声“生”再一声“生”,真是燕语明如剪啊,那剪必得是亮闪闪的银,那燕也一定是娇俏俏的紫,那呖呖莺声也比不上这水磨腔的绵润媚人吧……这样的摇漾袅绕,一听之下就让人爱煞,让人心生讶异:怎么这么好?怎么这么入心入肺?怎么这么容易被感染而感动?怎么好像早在这里等着我今时今日来就来爱?叹息,再叹息,然后感喟:也是一种缘啊,命里注定了的,时间与空间无涯的荒野里可可地撞见,怎么能够又怎么舍得躲开?
戏曲之于我的人生,却是渗透。小时候随了外婆或母亲去看戏,也如《社戏》中的迅哥,只是喜欢那份热闹:呼亲唤友,相约去戏院,开戏前鼓乐齐鸣的打闹台,鼻梁上一片粉的三花脸,丫鬟上台来一扭一扭,小姐上绣楼一踮一顿,后台沿儿一群小脑袋挤来挤去争着看,明晃晃的头饰,摇摇欲坠的珠翠,那个普通的女孩上了妆竟花容月貌,有人对着大箱子叫“我的髯口呢”,有人心无旁骛地练习甩水袖,果真是水一样的流动,偏生又雪一样的洁白,舞起来像大朵的花,像团团的云,是梦里才会有的美啊……都看过什么戏,全然不记得。剧情是什么,也根本说不上来。事实上,对于那些哼哼呀呀老也不到头的唱,也真有大话西游里悟空对唐僧的厌倦。只是,会和小伙伴聚在旧屋,一堵圮墙下,一斜土台子,手上系一方白毛巾,装模作样地甩啊甩,想像着自己很成熟很美的样子。
真正的喜欢,是在长大一点,懂得欣赏后。记忆里那些亮闪闪的碎片,逐渐具备了意义,被重新认识,接纳,沉淀在人生的河床上。那戏属于梆子之一种,但又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梆子腔系,唱词时用本腔,也即真嗓,然后接以假嗓,谓之花腔,清脆婉转,明亮高扬,或喜悦,或激昂,或苍凉,间以鸟啼般的主弦,中州话的念白,使听众如饮甘醪,几欲醉倒。这是乡民们自己的剧种,只属于南阳一地,南阳古名宛,因而大家就直呼它宛梆,含着一股子亲切劲儿。它也当真亲切得紧,不但有卖苗郎、小姑贤这样的剧目,几乎等同于生活本身,而且把历史题材、宫廷生活也平民化,帝王将相都一身的烟火气。看那《打金枝》里,公主和驸马宛然是西邻那对小夫妻,郭子仪是村东头火爆脾气的大叔,代宗皇帝就是谁家有事都找他调停的老知客,皇后更是乡民们心里温柔贤惠又善理家的最佳主妇——皇家生活似乎也不过是柴米油盐,但一一观来又不觉得突兀,反而诙谐自然,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
豫剧也是乡民们所爱的剧种,但我真正走近它却很晚,大概是十六岁知道了常香玉之后吧。正是年少岁月,狂傲性情,拒绝家人的翼护,向往着女孩家也能走遍天下,读书喜欢“生活在别处”,唱歌喜欢“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听戏就喜欢上了“谁说女子不如男”——不拘操场、寝室、洗衣间,想唱就唱,唱得响亮,带动得一群“花木兰”跟着娇吼。及至后来看《穆桂英挂帅》便更爱,马金凤头戴金冠,上插雉尾,长帔,女靠,端庄矫健地走出来,轰轰三响后开唱:“午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天波府里走出来我保国臣。”帅旦的英姿,直要教人倾倒!她在《对花枪》里却是老旦,一桌一椅一根拐杖,开场唱着“老身家住南阳地”,如此一大段独唱下来,却并不令人烦乱,我这南阳人反笑微微地欢喜着。《花打朝》里她扮七奶奶,集花旦的活泼、刀马旦的英飒、丑旦的滑稽于一身,泼辣幽默,诙谐调笑,真让人爱不够!其他如阎立品、唐喜成、牛得草等名角,亦各有可以细赏之处。
看越剧和黄梅戏,喜爱里边的女书生,特别是戏中旦角女扮男装。冯素珍一介女流,走出闺阁,得中状元,“我也曾赴过琼林宴,我也曾打马御街前,人人夸我潘安貌,原来纱帽罩哇罩婵娟哪啊”,女驸马的英俊倜傥引人揣想:若真身在古代,我大概也会这样女扮男装戏嘲一下律条吧?祝英台也是女扮男装,却只赚得一段情,还落入了情殇的俗套,原非我心所爱,但戏里几段精彩的唱可为补偿。“小九妹”轻俏可爱,“十相思”幽婉深情,“十八相送”最是把戏做足——丫鬟和书童引道:“前面到了一条河,漂来一对大白鹅。”祝英台忙接上:“雄的就在前面走,雌的后面叫哥哥。”傻乎乎的梁山伯哪里听得懂?还只管较真:“嗳!不见二鹅来开口,哪有雌鹅叫雄鹅?”英台应得更加巧而调皮:“你不见雌鹅它对你微微笑,它笑你梁兄真像呆头鹅。”温软软吐出一句“呆头鹅”,再辅以俏生生的笑语,可恨梁哥哥不解风情,倒急坏了戏外的一干听众。黄梅小调《夫妻观灯》也是我深爱的,韩再芬伶伶俐俐的唱,“兰花兰香百花百香相思调儿调思相,我自打自唱自帮腔。咦嗬郎当呀嗬郎当瓜子梅花响丁当。喂却喂却依喂却,喂却冤哪家舍呀嗬嘿郎呀九月里菊花黄哪”,有大珠小珠落玉盘之妙。越剧《红楼梦》也有不少经典段子,林黛玉“看风过处,落红成阵。牡丹谢,芍药怕,海棠惊,杨柳带愁,桃花含恨。这花朵儿与人一般受逼凌!我一寸芳心谁共鸣,七条琴弦谁知音”,葬花之人断肠痛,听戏之人痛断肠。可惜的是,这两个剧种唱腔不固定,这几年总是被角儿们改来改去,有的差强人意,有的几乎不忍卒听。
一个出色当行的角儿,有时对一部戏一个剧种的影响,也像章诒和的那句话:可萌绿,亦可枯黄。我走近评剧,是因了新凤霞的名字。“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唱得是真好,但因为是现代戏,总觉得缺少了些韵味。《花为媒》整部戏闹腾腾的,配角一个比一个难看,赵丽蓉也没有老来小品里的灵性,好在此剧是吴祖光为爱妻精心改编的,李忆兰扮演的李月娥漂亮但不抢眼,把个“张五可”衬得恰到好处,新凤霞的扮相、身段与唱功都光照四座。“花开四季皆应景,俱是天生地造成。春季里风吹万物生,花红叶绿草青青,桃花艳,李花秾,杏花茂盛,扑人面的杨花飞满城。夏季里端阳五月天,火红的石榴白玉簪,爱它一阵黄昏雨,出水的荷花亭亭玉立在晚风前”,报的是花名,满园里却只见张五可冠压群芳。“芙蓉面,眉如远山秀。杏核眼,灵性儿透。她的鼻梁骨儿高,相衬着樱桃小口。牙似玉,唇如珠,她不薄又不厚。耳戴着八宝点翠,叫的什么赤金钩”,夸的是李月娥,镜头里偏只见张五可美得“美天仙还要比她丑,嫦娥见她也害羞,年青的人爱不够,就是你七十七八十八九十九年迈老者见了她,眉开色悦赞成也得点头”。
接触秦腔很晚,是在一部叫做《大秦之声》的电视剧里。“呼喊一声绑帐外,不由得豪杰笑开怀”,猛听得净角一声叫板,说不尽的慷慨悲壮,让人的心陡然一颤,如冷风里的一茎草般不胜负荷。原来还有这样的呐喊,这样烈性的唱法?此后便专门去寻秦腔听,虽知这是梆子之一种,可还是被那迥异的唱腔给震了一下。最想说的是《窦娥冤》,那大起大落的唱法,激越处声遏云天,低回处幽咽如泉,急切处铿锵凛然,出于口唇,起于心底,还真是最适合演唱关汉卿“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的冤愤。“广漠旷远的八百里秦川,只有这秦腔,也只能有这秦腔,八百里秦川的劳作农民只有也只能有这秦腔使他们喜怒哀乐。秦人自古是大苦大乐之民众,他们的家乡交响乐除了大喊大叫的秦腔还能有别的吗?”贾平凹如是说。现有这“崔颢题诗在上头”,对于秦腔,我在欣赏之外自是不敢多说了。
和地方戏相比,京剧的确当得上雅正之名。就像同时喜欢生活的凡俗和诗意一样,我喜欢地方戏大喊大叫真哭真笑的入俗,也喜欢京剧字正腔圆端着架子的范儿。唱做念打,手眼身法,名角们各有派头,也各有千秋。同光十三绝,清末名伶,自不必说。谭鑫培,京剧艺术成熟时期的领袖人物,文武昆乱不挡。余叔岩唱腔中正醇厚,被誉为“韵厚”。言菊朋注重抑扬顿挫,唱功含蓄雅致。马连良的唱腔灵巧华丽,表演潇洒飘逸,我最喜欢《空城计》里他摇着鹅毛扇对“司马懿”唱道:“你就来,来,来,请上城来听我抚琴。”儒雅洒脱,让人几乎忘却“演”戏一说,而产生诸葛亮本当如此的错觉。“四大名旦”里,尚小云和荀慧生无缘得近,梅兰芳和程砚秋却听得很多。第一次听梅兰芳,就喜欢上了那甜美到极致的嗓音,润如珠,明如玉,柔如水,一句“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又早东升”本身就像海上明月一样引人神往。台湾戏曲研究家齐崧说:“如果听梅兰芳的戏是等于吃鸦片,那么听程砚秋就等于是打吗啡。因为吃鸦片尚有戒除的可能,而一旦打上吗啡,则很难了,最后唯有以身相殉。”说得有趣,但还真有道理。初听程砚秋,那粗而沉的嗓音、长而拐的唱法让人不耐;再听,“春秋亭外风雨暴,何处悲声破寂寥”,似乎感觉到一些说不出的韵味;听得多了,想到一句古语“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正自随了他行腔且走且升且向前,却忽然沉下深谷返身踟蹰,柔和中内敛一股锋芒,润饰下别有几许沧桑。遥想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他们一个在黄金戏院,一个在天蟾舞台,唱对台戏。程砚秋端庄雅致,水袖儿翻舞得满台行云流水;梅兰芳俊秀出众,卧鱼儿完美得举座拍掌叫好。那盛况让人神之往之,只可恨岁月阻隔,都被他带将春去了!
但若论高雅的典范,京剧其实不如昆曲。昆曲被称作戏曲活化石,唱词古奥,曲调典雅,固然有些已失传,但承继下来的基本保持原貌,最是难得。也可能正基于此,虽然文辞流光溢彩,唱腔婉转缠绵,却运途孤寒,少被大众亲近。我也是近几年才开始听,可一听到《游园惊梦》里“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停半晌,整花钿,没揣菱花,偷人半面,迤逗的彩云偏,我步香闺怎便把全身现。你道脆生生出落的裙衫儿茜,艳晶晶花簪八宝填,可知我常一生儿爱好是天然”,即刻有了惊艳之感;又听到“遍青山啼红了杜鹃”那一段,简直要热烈拥抱了;等到听“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时,便明白了聪慧敏感的林黛玉为何会心旌摇荡痴在了大观园里。如花的是容颜,似水的是流年,任是怎样的繁华也难避免陨落、毁灭、消逝无踪,一切的痴妄纠缠终究如雾、如电、如梦幻泡影,这样的彻悟不知不觉中就把戏内戏外的心儿给连通了。
戏里阳秋,各人心领神会。悟得几分,也是各人福分。全国共有剧种360多种,我只是有幸睹得一小部分,得其趣而自乐之,正像杜丽娘游园结束所言“观之不足由他缱,便赏遍了十二亭台是枉然,倒不如兴尽回家闲过遣”。倘有“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也自由他,我自在梦里看水袖和着渐逝的春光暗流转:起云手,且转身,翻水袖,两臂背袖,蹲下,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