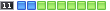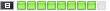圣 诞 夜
刘荒田
圣诞节,我得上班。换上洋鬼子,在这个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离开家里壁炉的火光而去赚可怜的工资,一如中国人在除夕夜不能和家里人一道守岁,是要引为大憾的。不过我是例外――我感到轻松,为了有这般冠冕的借口,逃开每年都不得不参与的家庭派对。这些年的圣诞夜,都是这样过的:到亲戚家去吃洋式烤火鸡和中式烧排骨并陈的晚饭,然后,10位以上的小孩子扑向圣诞树下的礼物堆,开拆写上自己名字的盒子,嘻嘻哈哈,惊叫连连,客厅飞舞着彩色纸片和酣畅的笑声。这阵子,我爱痴痴望着窗外。照例是冬天中最冷冽的一夜,树和悬在人家窗外的灯饰,都被冻僵了,泛着青光。汽车小心翼翼地驶过,仿佛在冰上。有情天地在没有人气的所在,以冷锋削出的寂寥反衬团聚的温暖。然而,恰在这样的场合,感到最不该感到的失落,撕开礼物盒封纸的声音,让我想起没有礼物只有饥饿和恐惧的童年,让我想起藐小的生命之河蜿蜒到异国,无论怎样努力都不能汇入主流,不是因为新大陆的土地拒绝我的渗透,而是我没有能力,甚至没有接受同化的愿望。小河进入大川,意味着前者的消失,而我的生命是汉语的水滴所汇聚的。即如此刻,孩子们忘情的欢笑,我就无法进入,尽管礼物堆里有我的几份,儿女送的,我的名字被叫出来时,我却象老姑娘上台领“晚婚模范奖”一般脸红耳热。
今年不必受这洋罪,很是轻松。下班时是晚上7点多。在路上打开收音机,短波一个电台在播放脱口秀,一个苍老的嗓音,和暖气一起鼓荡:“这辈子里头,只有5个圣诞节算得有意思,别的都是老一套:坐在沙发上发呆,耳畔响着老歌,厨房里飘来姜面包的香味。是啊,很腻味。不过,想想,一生中有5个圣诞节供回味,该满足了。”脱口秀务必幽默,但这个开头太苍凉了,怪不得没有噼噼啪啪的掌声和哄哄的笑声响应。我把收音机关掉,专注于路上。街旁,商店的橱窗和人家的窗台,灯饰尽忠职守地亮着。我想,人生即使获得满足,那又如何?礼物盒不拆,希望活跃着,一拆,希望便溜走了。儿时的除夕,最激动人的,不是打开利是封,掏出要么五分要么一毛人民币的瞬间,而是晨曦初现时,打开门缝,远近爆竹声夹着寒气和星光囫囵涌入,那种新鲜之极的憧憬。
到了家,快8点,我几乎可以分毫不差地推测:在亲戚家,晚饭刚完,几位家长拿起录像机,向着圣诞树下堆成小山的礼物盒,孩子们将要发起最快乐的冲锋。我在快乐的边缘溜过,一似雨珠溜过绿叶。没有遗憾,只有祝福。一似儿女幼小时,在甜梦里蹬掉被子,我微笑着替他们盖回去,顺手爱抚一下他们带笑的脸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