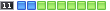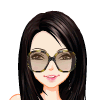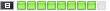去华人超市,偶然见到塑料袋包装的红枣,上写着“宫廷大红脆枣”,还有“纯天然绿色健康食品”之字样。想起了小时候吃过的脆枣,没想这朴素的零食,原来还有“宫廷”的头衔。就随手买了一包。
脆枣,应该是我河北老家的特产,因为在其它地方没有见过这种做法。那是去核的大红枣上炉烤干了的。一咬就碎,焦香甜脆,好吃得让人欲罢不能。手上的这袋“宫廷”脆枣,没写产地,枣子也似乎比老家的那种干绉很多,打开吃上一颗,没有那种脆枣的焦酥口感,又干又硬,咬得我两腮都疼了。吃得实在辛苦,索性放进锅里,加上一点水和糖,煮得熟软了。
想起了母亲讲个过的一件事。那时我一,两岁,正是六十年代初三年困难时候。母亲带我回她的老家,我们从北京到石家庄,在那里再转车到老家的村子。车站上有人叫卖脆枣,我闹着要吃。母亲拗不过,就卖了一把。她嫌脆枣脏,放在手绢里不停地挑着,吹着。这时,一只脏手伸到她眼前。她抬头一看,一个成年男乞丐,正在向她乞讨。母亲顿时来气了,大声斥责: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刚给孩子买了点枣,还没有吃进嘴里,你就来要。这么大个人,身强力壮的,干点什么不好,向孩子要吃的,你好意思吗?那个乞丐羞得低下头,一声不响地离开了。
我自然不记得当时的情景,但这个故事似乎就在我的眼前一样,多年不忘。似乎看见一个衣着整洁的漂亮城市女人,大声斥责一个脏兮兮的男叫花的样子。我私下对这件事的曲直抱有疑问。难道男人乞讨就应该被斥责吗?母亲也是农村人,也挨过饿,是否过于尖刻了呢?能干活的人,乞讨就不能被原谅吗?能够做活填饱肚子,有多少人乐意去乞讨呢?是不是没有活计可以做,或是做活计也不能填饱肚子呢?不知道究竟,只有胡乱地猜测。
枣子不仅味道甜美,还营养丰富,所以一直被人当做滋补食品。小时候供应紧缺,市上买不到大枣的。乡下带来枣,都被我当零食吃了。老家的大枣,比其它地方的大枣都好吃很多,个大肥园,皮薄,核小。晒干以后,果肉又软又糯,又香又甜,让人难以抗拒。现在国外卖的多是晒干的鸡心小枣,小得只有一层皮。大枣也比较干瘦,跟老家的枣没法相比。
我父亲的老家在北京郊区。那里也产一种枣,长长的橄榄形状,皮色在成熟后转红。吃起来甜中带微微的酸味,口感青脆,非常可口。每年打枣,父亲的朋友都会送来很多,吃得我肚子疼。
那些年,北京市面上卖一种伊拉克蜜枣,据说是跟中东地区国家做生意以物易物的结果,看上去粘糊糊、脏兮兮的。大人怕有传染病,不让吃,所以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后来去了南方,水果又多又好,单单没有枣。意识到枣是北方的物产,喜欢寒冷的天气的。到国外,也到处不见枣树和枣子。有一种椰枣,又甜又面,很像北方的晒干的柿饼的味道,明显地跟枣不是一回事。枣,被叫做中国枣。看来枣子这种东西,是果品中之国粹了。
《战国策》说“北有枣栗之利”,“足食于民”。延安的枣园,哺育过一个新生的政权。我想,自古至今,枣子滋养过数不清的人,为什么,生有如此食物的地方,人们还要挨饿呢?为什么,同样的地方,同样一群人,人们又变得不再那样挨饿了呢?世事变迁,挨饿到不挨饿。吃到嘴里的枣子味道,也不是以前那样的了。
当年读鲁迅的散文《秋夜》,开篇的句子让我印象很深:“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在北京的寓所,这个身为南方人的文豪眼里,枣树一定让他觉得很特别的。被人打尽了枣子,带着伤痕,落尽了叶子,在寒冷的秋夜里,直直的树枝指向天空,把星星指得“鬼眨眼”,把月亮“窘得发白”。
如果枣树有知,立于如此长久的天空之下,它一定看见日月星辰的运转,世道人情的变换,还有人民生活的甘苦。于是,它一面直指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面献出营养而甜美的果实来。
2009-1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