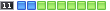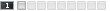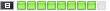汉诗的美感
——著名诗人洛夫主讲
赵丽宏先生主持
地点:上海市作家协会大厅 时间:2009.11.7下午2点
洛夫:
现在不是诗歌的时代,它的边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市场经济控制了一切。
我的诗集在花城出版社出版,从当时5万册,之后5千册,再后来3千册,以及2千册,没有再版的机会了。但不气馁,诗歌活动愈是频繁。冷漠中,写出温暖;虚假中,写出真实的美。无怨无悔,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下来,不受市场化的价格影响。
写诗是一种价值的创造,创造什么?
一是艺术价值的创造,如李白、王维的诗歌。二是生命内涵意义的创造,如杜甫、白居易的诗歌,贴近百姓。三是意象语言的创造i,如李商隐、李贺的语言。
诗是创造的行为,而不是商业行为。我在温哥华的生活,适意自在,无欲无求的一种人生况味,随心所欲不逾矩,以此养生。对名利持自然的态度,不必鄙视,、矫情。名利是人性的一部分,也是有正面的意义,名实相符也是正当的。
现在读诗的人愈来愈少,也属正常的现象。少有少的好处,更纯粹了,也更宁静了,回归诗意的本性,充满了美和善。处在艺术精神的塔尖,忍受寂寞是对诗人生命的考验。
朱光潜将东西方的美学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是诗歌最需要的审美意义。
中国传统美学断裂得太厉害;距离愈远的,那种高深的美质的艺术创造性,往往是超时空的。柳宗元在一篇散文《邕中柳中函作马退山兰亭记》中的美学观点:“美不知美,因人而彰”;王佑军的《兰亭序》兰亭的景物之美,碰到清流之徒的审美活动,(景物之美)要人去点亮它,变成感性的,成为意象,成为诗的境界。
诗是什么,诗的本质是什么?诗就是一个意象的世界,物理世界之外建立一个心灵的意象世界,达到一种情景交融。以我写于1981年的诗《因为风的缘故》为例——
昨日,我沿着河岸
漫步到
芦苇弯腰喝水的地方
顺便请烟囱
在天空为我写一封长长的信
潦是潦草了些
而我的心意
则明亮亦如你窗前的烛光
稍有暧昧之处
势所难免
因为风的缘故
此信你能否看懂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务必在雏菊尚未全部凋零之前
赶快发怒,或者发笑
赶快从箱子里找出我那件薄衫子
赶快对镜梳你那又黑又柔的妩媚
然后以整生的爱
点燃一盏灯
我是火
随时可能熄灭
因为风的缘故
(届时见PPT投影这首诗。莫凡——洛夫之子谱曲、制作、演唱。莫凡男中音,风格委婉动人、深沉悠长。钢琴伴奏。)
潜意识是灵光一闪,稍纵即逝。个人经验如何将那份灵气、情感化为意象,用最适当的文字写成一行行诗。“诗人是诗的奴隶,必须是语言的主人”,要对语言控制和驾驭。潜意识在一直活动,就于始料未及的时候冒出来;不断的思考,又在放下以后,自然地冒出来,正所谓“踏破铁鞋不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因为风的缘故》,此诗有两种解读——
一是为妻子陈琼芳而作;另一种是我个人感情的扩大人生际遇的写照。
洛夫:
另一种传统的美学观点是“无理而妙”。
先锋诗人认为诗歌止于语言,即语言的实验论。
马拉美认为,“诗歌不是以思想为形式,而是以语言为形式”,我不同意他的上半句。我认同孟子的“以充实为美”,在语言的背后有意蕴、有境界。散文的语言是载体,可以分开的,有人把散文比作散步;诗的语言与风格不可分割,人说诗是舞蹈,舞者与舞蹈不可分开。
我认为,将中国传统美学与西方超现实的手法结合为中国的现代诗,从古典中探索超现实的元素。李白的超现实中有非理性、绕过逻辑思维的东西。与西方的结合,仅仅是无理还不行。中国不仅仅无理,还要达到绝妙的境界。
李白的《下江陵》:“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妙在无理,现实中的不可能变成可能,表达了内心的畅快!
苏东坡的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于人的意料之外,却是清理之中,表达内心的感受;李商隐《锦瑟》的“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扑朔迷离;杜甫的诗中发现了超现实的幻境,他天宝年间站在塔上,写了“七星在北斗,河汉声西流”。
我年轻时写了一句“替松树奋力举起天空,听到年轮旋转的声音”,只是隐喻了生命不断成长的过程。我的超现实手法与其说受到西方的影响,莫若说是受到了中国传统古典美学的熏陶,获得一种意象的蕴涵之美。
赵丽宏:
洛夫的“汉诗的美感”主要讲了三个问题。
一, 诗是意象世界的呈现。
二,汉诗的无理而妙,诗是有意义的美。
三, 这种与生命息息相关的诗,不只是语言,还有诗背后的意蕴。
洛夫回答席间诗人的几个问题。
●您从什么时期开始写诗?
洛夫:20多岁起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戴望舒编的现代杂志。我到了台湾更扩大了这类介绍,在办《创世纪》时期,介绍了西方的现代主义,包括法国的超现代主义等,七八十年代,对台湾年轻诗人有冲击作用。
●结合你自己的创作,谈谈新诗这么多年来的变化。
洛夫:白话诗运动,胡适否定了传统,产生了误导作用。
台湾诗人向西方学习,有十到二十年,一直八十年代,诗人有了觉醒,诗人应该扎根本民族的土壤,一直游离在本民族的语言文化之外不行,还要回归本民族的文化,对精髓有所创新。因此回到“故土”是很自然的事情。我的诗中有很明显的传统文化的东西;开始也不是。有机性的整合,变成了自己的风格。
●谈谈你的魔幻的经典地位。
洛夫:我对“魔幻”不承认,也不否认。怕产生了道德上的悖谬。
赵丽宏:魔,不是魔幻。主要是变化莫测。
洛夫:赵丽宏先生是对的,是一方面。我记得伏尔泰说,“每一个诗人都有一个魔”。如李白的《下江陵》,诗人都有一个悖谬性的问题,以后会整合。年轻时我反传统喊得很响,后来的整合,觉得正常。
●你还记得您写的第一首诗么,儿子莫凡也写诗么?
洛夫:青春期写作,小说家、画家等一般都从诗歌开始,是情感的宣泄。第一次见诸铅字的倒不是诗歌,而是一篇《秋日庭院》的散文,有些诗意,15岁时写的,在报上发表。此后写了2—3年的诗,带到台湾后都遗失了。
之后从台湾回来,见到了当时的编辑,居然在废墟里找到少作十几篇,很惊奇!
认认真真作为行业写诗,是在创办诗刊当主编时的追求,开始写,有一个境界,与现实间的距离,与人生若即若离,二十多岁把握诗歌的本质。
儿子莫凡早年,读初中时写过诗歌,被我改得一塌糊涂,从此他就做音乐家的梦。
●谈谈在加拿大的情况。
洛夫:加拿大是多民族的国家,多元文化的并存,用英语、法语,对我不造成压力,常请我用毛笔写中国诗。在加拿大有较多的汉学家,把我的汉诗翻译成英文。我认为诗是不可译,中国诗不能翻译,背后的东西译不出来的,是语言障碍。
马悦然作为诺贝尔奖唯一懂汉语的评委。他说,中国有好东西,翻出来就不行了。
●能给新诗的发展、振兴开一个药方么?
洛夫:这是一个感慨。对于新诗,沈从文的批评是负面的,看到胡适的诗;中上年纪的人习惯写旧诗。复兴是必要的,但要统一,很困难。写旧诗的情感会格格不入,但我觉得几十年从事的实验,有成功和失败的,总要去做,旧诗可以应酬,终究可以借鉴一种传统的美,不适于现代情感的语言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