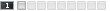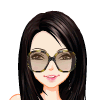文/心之初
在忙活的日子里,人怎么还爱棋呢?用我们当年的话说,叫人是个东西,但又不是个东西;要么想杀人,要么被人杀。“杀人”不杀他的身子,只杀他的精神。但不要以为“杀精神”才有快感,“被杀精神”了也有快感,会感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人总得有点精神”。
咋天早上闲逛大雁塔,顺便还想去吃吃西安的“有名”,但不曾想到改革开放好,只把春来找;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今日农民不种田。有名的饭鋪都非得到上午十一点才开门,气得我只好买包西安最好的烟,反正老婆不在身边。没想到买了包假烟。抽根假烟,恨我的口感;买两个烧饼,把小肚填饱。反正在中国要么挨宰;要么上当。这大雁塔的吃处,也和走了多年的张陕西作家路遥一样:生命从中午开始。
一边吃烧饼,一边看店牌,谈不上感觉好,因为喝不着热水。但见有家饭鋪前的柱子上还写着:不准不快活。旁边“新打里”的印度料理还传出“大蓬车”的曲子,让人有点凄凉的感觉。正打算给自己点幽默,化紧张为轻松。却间路边一片人头。上前一看,居然人们在下象棋。看了一小会,一人垂头丧气,一人得音洋洋。我按捺不住,上前问那赢了的人:我能不能下一盘?那人点头。我坐上三块砖头,记那人让我现行,以示上手身份。我便“炮二平五”那人也“炮二平五”,吓我一跳,心想你既不是“风中秋叶”,也不是“红樱枪”,难道不知道后手列手炮吃亏?
心想归心想,棋得认真下。我点上支假烟,定会神,寻找假烟里的那点好烟丝的味道,也回想那些“列手跑”枪法。“马二进三”,“车一平二”,。。。“窟里窟嗵”,也就二十来步吧?我便让他那人垂头丧气。哈哈,对付这些马路棋手,老夫这生疏了多年棋艺,居然也还能斩人马不。后来,那人邹起了眉,加上众人的群策群力,能把棋下进有输没赢的残局,但玩死和早死有多大区别呢?四连胜两人后,我假托撒尿,走人了。哼着小曲:那是外婆的澎湖湾,白浪出沙滩。
我最早开始认点真下棋,是三十五年前了。那会神州人民“批林批孔“,赤县百姓在思考林彪和孔老二的关系。大人们白天批上一天,太阳落山后,上大多都因乏了,该上床的上床,不想上床的便打牌下棋。我们家属院的大门里,高高的路打下,便是人们快活的好战场。好几个象棋扑克摊。教授,处长,会计,出纳,做饭的,伙管的,修水管的,看大门在一起欢声,在一起笑语。大家互相讥讽,互相控苦;有“春风得意马蹄急”的;也有“别让巴常山挡住了你的视线”。这边“北风那个吹”,那边“我要把牢底来坐穿”。大家都既没地方弄钱,也没地方花钱。但精力、神不可谓不旺盛,生命不能说不蓬勃。那个时代“人都是有点精神的”,那么点精神有什么用呢?那年,我正是个正在待业听党召唤的十八岁的哥哥。扑克我从不爱打,太简单了。于是夏夜乘凉,就是看叔叔们下棋。
我牛叔是棋摊常年天天的擂主。他是我们学院的会计,还是个山西人。据说他因为太爱下棋,和原老婆离婚。后来又结婚了,我还吃过他的喜糖。他二婚后,依然把棋盘画在他家的小饭桌上。职业加上爱,牛叔下棋仔仔细细一丝不够,爱每个子,不爱丢子。他下棋的热情,就像山里的泉水,一晚上下个几十盘也没问题,永远的“屏风马”。他实践找真理验真理好多年了,平时老下棋的人都还下不过他。和他老下棋的是我的王叔,这王叔是河南人,热情好斗倔强,他棋术比我牛叔差点,但嘴厉害,爱说的口头语是:杀猪杀屁股---一个人一个杀法。但赢棋是靠脑子,我牛叔说不过就不说,光琢磨吃大子,赢棋。牛叔常因打遍全院无敌手而寂寞。他寂寞时也和我这半大小子臭棋下。我下不过他,但他的爱悔棋也让我十分不快,特别是他棋好时,也动嘴。老输棋的感觉真不好。
其实,除我牛叔以外,我们院还有一个高人,是个教授,人很清高,我叫他鲁老师。我那会正血气方刚,精神里也有“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的情怀,但赢棋不光靠志气,也不靠“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鲁老师有时帮我支两招,老牛被气得喘粗气。于是就挑战鲁老师,鲁老师下棋落子的手势姿态真是好,当然走得也好。任老牛凭怎么发力,也挡不住鲁老师的犀利。我后来知道鲁老师是成都六十年代象棋赛的前几名。
后来鲁老师叫我到他家里一杯清茶一盘棋地下雅棋,顺便传我几招,还给我讲些棋理,又教我读棋谱,还借我一本《胡荣华专辑》。有过些经验,输过些棋,再读高人的棋,听大师讲棋,那些话那些棋,真是让人“喜欲狂”。两三个月吧,我牛叔便不太能赢我了。实践固然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我们得先知道真理是什么。如果不知道真理,我们检验什么呢?有段日子,我牛叔看着相当痛苦,脸上天天都是阴云。
一九七五年,文革把主席和总理都革得没了精神,尽管王张江姚很精神。大块的两报一刊社论还是天天让人头大,样板戏依然唱得声嘶力竭。那年,我们院所在的区(那会西安的大专院校都在南郊,碑林区)举办象棋大塞,各单位组三人团队,先团体后个人,我牛叔象解放似的高兴。他邀我和鲁老师参加。我只是家属,怎么参加!牛叔说:你把你爸那毛叽矶中山衣穿上,谁知你是象属?于是我便穿上我家老爷子的黑呢子衣,带个小眼镜,当大学教师看,脸是稚嫩些,但当院宣传队的大春看,还行。
那次比赛,团体有十二支队,像西安交大,邮电学院,石油学院,教育学院五0四所,治金研究所,财经学院。。。。。。比赛激烈,烟雾腾腾,我们队鲁老师和我的胜率差不多是百分之八十左右,牛叔的胜率能保本,决赛最后是在我们学院和西安交大间进行,那一战我和鲁叔(两个四川人)与两个阿拉老师(西安交大是上海交大迁到西北的)大战,战况相当惨烈。我鲁叔先拨头筹,紧接着我以黄继光似的壮烈的舍身战法赢得第二场,我牛叔便难得不泡磨雀,主动认输,我们赢得了那次团体赛的冠军。后边十几天的个人赛,我天天都操演兵法。在八进四的争夺里,我居然赢了指导下棋进步的鲁老师,且最终获得第三名,那次比赛的冠军就是日后八十年代的陕西省冠军白文典。
中国象棋很像中国文化,老帅身居九宫,车马炮舍身沙场,小卒在最前边呆站。汉界楚河的两边先列阵,然后车横行竖走,炮走炮路,马行马路,士象围着老帅,不用过河做战。下棋人的智慧和勇敢就是通过排兵,列阵,运筹,给对方挖坑,引敌人上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中展现。开始主要以占领军事要点让自己的将士们能很好协同做战,控制敌军蛮横,尽量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但心里得始终想怎样让对手的老帅动也不能动,被车吃被马踩被炮轰或被小卒拱。说起来好象并不复杂,毕竞就那么几个子折腾与闹活,但实际上学问很深,千变万化水深鱼少。咱昔日的祖宗,今日的俊杰写成的书就算拿出念博士的劲头,读破万卷书也不一定成。
在一九七五年到七七年考大学前的那些日子里,我除了上工打铁,下班就是下棋。作为区代表队的一员,我们每周都有两夜到我们区里的工矿企业单位,为丰富工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的丰复多采健康,做些贡献,下一晚上,也能挣上包三毛钱的烟。棋乐无穷,青春万岁。棋乐里,我啥都不爱关心,甚至到常香玉唱:“怎么怎么,揪出四人帮”,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得不行,有中学女生对我有了意思,我都呆若木鸡,每天只是快乐着我自己的快乐。
后来我上大学了,离开了西安。在大学,我参加过一次此赛,几乎就凭我一人之力,帮我们系获得了十个系的第五。在个人赛里我获得第五,但那次赛的全校冠军,在他的十盘棋里就只输了跟我下的那盘棋。我不明白为什么下中国象棋文科生要比理科生厉害些。前六名里两个是经济系的,两个是中文系的,还有一个是历史系的,他们互相有点“抬轿子”,让我从第三变成第五,得了一个本子,还和他们都成了朋友。
大学毕业后,我分到北京一所工科学校教物理。八三年考研,因左心室有点大,按政策我不过关。教那点工科物理,用不完我的精神,我关起门,喊了声共产党万岁,后来一边和我私定了终身的女朋友在北京西安各唱“十五的月亮”,无聊时就又下开了棋,反正报国无门。
我们物理教研室二十多人,教二,三十个班的课(还是大课),物理人的脑袋当然用不完。正好我校的象棋冠军就在我们教研室,他是老北大的,老婆还是蔡元培的孙女。我俩一手谈,我就三比零获胜,把我和他打成了忘年朋友。又过了一年,我们教研室来了个中科大的工花兵学员,此人竟是和聂卫平兄弟一起长大,还和聂卫平的第弟是京城桥牌队的搭当,围棋也有业余五段左右的水平。他特别爱和我侃,他目光特别炯炯,嘴巴特别利索,围棋更是高,且特别好赌,老要跟玩“象棋我让他车马炮,围棋他让我九个子”。开始我俩基本战平,后来我渐渐不支,因为让人车马炮下象棋太难了,比之围棋,高手对低手的施展空间要小得多,毕竟围棋更复杂。我常给他买饭,同时也喜欢上了围棋,偷偷夜读兵书。老何(被我下败老象棋冠军),也是个“双枪将”。差不多一年光景,我坐上了我们教研室围棋的第二把交椅。我们仨经常侃大山下围棋弄得不想吃不想睡。虽说挣钱不多,但有老婆当光棍的日子倒也过得很欢快,虽说夜深人静的时候也有些惆怅。
下围棋以后,我便不再下中国象棋了。围棋三百六十一个子,一样大小一样走法,都是元帅都是兵,“人人平等”,布局中盘收官,跳尖封关,辗转腾挪,追杀逃窜,吃和被吃,死了还能复生,实在在太来劲了。加上互相的唇枪舌剑,双方的抬杠,晸治攻势,心黑手辣,”棋可输劫不能输“的“砍头不要紧”和“死了也风流”的大义凛然,追杀敌军大龙,“宜将剩身近穷窍“,逃跑时“长征是宣传队”,一会“三十六计”,一会美军进攻伊拉克。赢了高呼万岁,输了肝肠欲断。杀对手和被对手杀,全是凌迟。
这中国象棋和围棋怎么居然都是咱中国人发明?足见咱中国聪明。这两样棋能让人在艰苦的日子里有乐子。生活里如果没有乐子,人被生活欺骗了,怎么“把那过去了的,都变成亲切的怀恋”?
围棋,趣味性要比象棋强得多,据说在中国是唯一让人还能不赌还能认真玩的游戏。围棋里边蕴藏的思想要博大深邃得多。低手欢喜吃子,上来就想把对方吃了,而高手总是大局在胸,走适度的棋,只想比对方好一点,除非对方找死。咱中国的帝王领袖好像没有一个围棋下的好,不知李世民如何?"大雪压着且挺直“的陈毅下得不错,但也只当到副总理。
发明围棋但下不好围棋,原先弄不过求道的日本,后来又下不赢思想活跃作风彪悍的韩国,更是没出过让人长久敬仰的巨星。吴清源是让人能长久让人敬慕的巨星,但却是在日本长大的大树。聂卫平曾证明日本的超一流是能战胜的,但又太爱美女,太爱名利,太爱胡说,沦为棋界闲谈的笑柄。陈祖德也为中国围棋的崛起立过大功,在他那本《超越自我》里自吹过许多,感谢郑敏之对他的救命之情,但日后也不知和谁去生了生了小小娃娃。声名大振的前后判若两人,是咱中国人和太多产生出这样的人的中国文化的悲哀。但愿古力,孔杰。睿羊,耀烨们,不要重蹈覆辙。李世世这会是休息了,但明年再出没准更加凶猛老道。
耀邦下岗后,我跑美国了,在过了弄懂国际歌的头一年后,念书入了正轨,和老婆哑铃式地和谐,一个周末我是快乐的单身汉,一个周未夫妻双双把日子过。虽说多花了份房钱,但自由爱情两不误。几乎天天和我同房的,是上海一大学的国际象棋冠军,他又教我下国际象棋。他住楼上,我住楼下(这哥们聪明异常,日后成了“三硕一博”)。我俩住的房子很大客厅很大空空荡荡,邻居全是黑人兄弟。周六的早上我俩研讨解放战争建国大业,中午吃大碗面睡个小觉,然后就进行国际象棋的二十四盘大战,我老输,不过也有几回,当国际象棋下成中国象棋时(只剩很少子时,战法便和中国家棋差不多了),我也赢过几次。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出国的浪头很猛。人们不管学啥能找着工作。我们物理系的研究生课堂,有时竟全是中国人,连老师也海峡那边的中国人。我们系有个复旦的中国象棋高人,此公目光笔直,天天穿一件长袖白衬衫,把袖子挽过小臂。我俩下中国象棋,他的胜率要高点。这小子也好赌,我俩常赌一个“阔特”。才高的人,大多都有点目空一切,我俩后来发展成三棋齐下,围棋我让他四子,他输多赢少;国际象棋我俩半斤八两;中国象棋,我四他六;嘴巴我俩旗鼓相当。三棋赌,他落点下风。但后来他看上个台湾女孩,把人家填成他信用卡的老婆,遭人痛斥,从此他目光总在女生身上的高处聚焦,还声称自己的目光是X射线,弄得全系女生,见他就跑。他锐利的目光,没处聚焦,就给神经了。我曾真心帮过他,但没成功。最后他在无家可归人的地方呆了半年多,后听说被送回国了,让人一声叹息。那年卢刚杀五人,让全美国震惊。
美国不好玩,但我稀里糊壁成了美国人。在这片土地上和我不太明白但又有些喜欢的文化里开始认真谋生,再没什么时间下棋了。“是非成效转头空”,快二十年过去,那些下棋的日子和那些曾经的激情和欢乐仍然让我爱着生命,爱着生活。
我抽完今生最后的一包烟,明天我将装上戴了冠的白牙。
二00九年十一月一日
[em42][em42][em42][em42][em42][em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