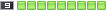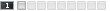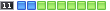星期天总是儿子先起床,叽叽喳喳吵着要吃的,接着老公起来,冲好牛奶,做好早餐,两个人开吃了,我才会被哄着起来, 这时候往往两人已经往我的卧室跑了好几趟。
这一方面是因为周末我会很随意地“开夜车”,还有就是可以在床上自由自在地思考,这常常接近于梦境,有时还就是因思梦而开始的。
吃完早餐,如果不出去,我就会上网浏览网页或写写东西,他们两人却是花样翻新,玩出不少的名堂。
按照习惯,我今早又坐在了电脑旁,还没有想好要干什么,耳朵就被一阵悦耳的笛声所吸引,仔细辨别,才知这笛声来自儿子的房间。儿子肯定吹不了这么好,一定是老公了。我静静地听着,在《梁祝》熟悉的旋律中,走进久远的往事深处。
老公和我是大学同学,是个优秀而极度不外露的人,从而也就给了我一次又一次大吃一惊又啼笑皆非的“重大发现。”
在我和他的生活中,我总有办法找出他的不足来抱怨爱情和婚姻的遗憾,这不足就是“我从小盼望和艺术家最其码是有艺术细胞的人一起生活,而你不是”。对我这样的埋怨,他总是一笑置之。
和他初次交谈,是在1993年的第一场雪后,我们相遇并一起去参加新生的学生干部竞选。爱显摆的我随身带了一本手抄本的个人诗集,想在关键时刻展示一下,从而加入自己最感兴趣的大学生文学社。
虽然入学时间很短,我甚至不知道同班的他的名字,但他已听说了我会写诗的情况,于是我就拿诗集给他看,他一边和我在雪地上慢慢走一边读着,很真挚地赞扬我写的诗好。 我问他有什么爱好,他说爱干几样事情,都干的并不好。
我因为他“没有艺术细胞”而有点轻视他,但受到这么风神俊朗的小青年称赞,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接下来我如愿进入文学社,他竞选当了班上的生活委员。在利用送信的机会,他给了我一张自己的照片,这本来也没有什么,因为之前我已经在班上宣布,“有自信长的帅的小伙就选自己最漂亮的照片送上来,别等到四年后老了再照给我当留念”。送照片的人还真有几个,于是有人笑我有征婚的嫌疑。我当然是极力辩解的,没想到这个“没有艺术细胞”的人却在送照片后很快就开始了对我的追求,让我在室友面前百口莫辩。
但是你既然“没有艺术细胞”,对不起你就根本不在我的选择范围,因此我总是在他想和我当同桌时抱着课本离开,在他送电影票时毫无顾忌地从他身边经过和其他人走进电影院。
后来偶然读到他写的诗,竟是非常灵动优美的那种,引得我为自己的傲气见到她就脸孔发烫,又好像被愚弄了一样地生出一丝丝的恨意。
和他熟悉了之后我将这种感觉说出来,他说如果我们能走到一起,他是不会写诗的,一个家庭中得有一个人稳如磐石当支柱,一个人灵魂自由飞翔当诗人,如果两个诗人生活在一起,那日子就会成乱麻了。
我很排斥他的这种说法,当然还是不会将他拉入我的选择范围。
第二年夏天欢送毕业生的晚会上,我是组织者之一,他也来参加了,要表演的节目是笛子独奏。此前我从未听说过他会吹笛。那天他以一曲深情悠扬的《涛声依旧》让我对他刮目相看。
我是喜欢吹笛子的,在高中时代压抑的集体宿舍里,我常常会幽幽咽咽地奏出一腔笛韵。当时吹笛子的女生很少见,这当作一种很另类的表现被大家在背后传说,我虽然并未在意,但高考的临近还是让我放弃了这短暂的爱好。
在他的笛声中,我又一次找到了那种自由和飞翔的感觉。此后,我总喜欢在黄河的涛声伴奏下听他吹出一支支优美的曲子。
写诗和吹笛,他慢慢接近着我的标准,我也就慢慢地接受着他的靠近,以至在毕业实习的时候,我随他一起来到了他家乡的一所农业院校。
那所学校的校长很喜欢唱秦腔,学生中也有几个唱的很出色的人,每逢周末,大家就会拉起一个班子来唱戏,那次他正从他所实习的百里外的学校跑来看我,校长便邀请他一起唱。他说:“我不太会唱,过会去凑凑热闹吧!”
校长走后,我大为光火,我说:“不会就不会,什么叫不太会?这样装腔作势,想给我丢人是不是?”
他说:“会一点儿。”
我更加生气了,一个劲地骂他说谎,因为在和我相处近四年的时间里,我就从没听他唱过一句。
那晚他去唱了,没想到一开口就惊动四座,竟然是字正腔圆,有滋有味,黑脸的包公,红脸的关羽,都让他演义的出神入化,吼着秦腔的他也看上去更增添了不少男人的气概。我是真正地崇拜起他来了,和同去的学友一起跟着他猛学《周仁回府》,终因“没有艺术细胞”而作罢。
在乡下任教的那寂寞的几年之中,他不时会去广袤的原野上为我吼秦腔,金黄黄的油菜花,红艳艳的九子梅,绿油油的小麦田,苍翠翠的大森林,都和我一起如醉如痴地聆听着他富有男人味的磁性的声音。
如今生活在了城市,平凡的日子中,他不写诗,不吹笛,不吼秦腔,却会在半夜为我打印诗稿,在早晨为我做好早餐,在我不时因写作阻滞,颓废地自觉“没有艺术细胞”的叹息中为我大唱赞歌,让一家人在他的“稳如磐石”中幸福安静地生活。
在我几乎忘记他“有着艺术细胞”的时候,他却以这清晨的一腔笛韵,唤醒我久远的美好记忆,让我在对生活的感恩中,静静地为他侧耳聆听。
2009.1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