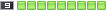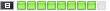原以为国庆过后可以闲几天,早晨到单位看没有事,就溜出来拿节前送去装裱的张学斌先生寄赠的楷体扇面《心经》。因为装裱的地点正好在新建的花鸟市场,因此顺便买回来两袋腐殖土和几个好看的花盆。
正动手移栽着心爱的兰花,领导的电话就骤然响起来。我是个不善说谎的人,想都没想就汇报说自己呆在家里,好脾气的领导并没批评,但坚持让我速去单位。看来有比较紧急的任务了。
到了单位才知道是某部队的一名战士被评上了“全国百名优秀士官”,过几天就去首都领奖,要带一张表现先进事迹的DVD光盘,我的任务是前期采访写稿。
坐上来接的部队的车,我还没搞明白要去的确切地址,因为这是支从南方来参加修筑高速公路的武警部队,我虽然去工程现场采访过两次,也为他们做过一个以总体工作为主的汇报专题片,但并没去过他们机关的驻地。
到了目的地下车,我吃惊得几乎叫出声来——这驻地竟然是我生活过多年的校园。学校的师生已经搬迁到了城市附近的新学校,因此我也知道是荒芜着的,现在看来它在部队战士的改造下已是焕然一新,我原来的花园也被半堵高墙隔到了我的视线之外。
按捺做想要去看看我的花儿的急切心情,我马上就投入了采访工作,因为以前对总体工程比较了解,连续不到四个小时,从座谈、记录到撰稿的工作就基本完成了,接下来的任务是将三千多字的初稿按要求压缩到一千多字,这项工作我一般会过上一些时间再做,这样好同时发现一些当时没想到的漏洞。
看看时间倘早,因此我向大家宣布了我和这地方的非一般关系,提出要到“校园”和我过去的宿舍走走。第一个目的地自然是我的花园。
当年我曾和孩子们一起在那里面种下各种各样的花草,课余便坐在花园中读书、批改作业,这些在报纸发表过的《我的心灵花园》中已做过详细的记载,但有一点我是没好意思写的,那就是我在强烈的妊娠反映期间于花园中一边昏昏然晒太阳,一边仅靠吃苹果和核桃维持生命的辛苦美好的岁月。是的,我的孩子是在这里出生并学会说话和走路的。我千方百计调离学校时他已能够和我在高高的七月花丛中捉迷藏。
我离开的时候是非常高兴的,一方面是从农村进了城,另一方面也是当时自认为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做教师虽然在高高的作业垛前总是发怵,但讲课和与孩子们相处还是有无限乐趣的,但我偏偏就认定了那不是我的理想职业。因此我总惭愧自己和无私奉献者相比,是属于追求个人理想的那种人。
岁月荏苒,不到十年的时间,我却又走进了怀旧者的行列,这个校园和我们一家在这里原以为失意却无比幸福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就与宿舍门前的花园一起,常常不经意地撞入我的梦中,让我生出深深的怀恋。
穿过粉刷一新的教学楼和一排排平房教师宿舍,就来到了我的花园。战士们显然已将这里改成了菜地,兰花、牡丹、芍药、菊花全不见了,只有一排排的冬青和千枝柏还在,而且长高长大了不少,显露着勃勃生机。这两种风景树不知在什么时候就成了我的最爱,我每到一个地方,似乎都要栽下它们或者它们中的一种。
在花园中转了几圈,我不由自主地又走进了曾经住过的宿舍,恍惚觉得自己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走出校园之后所经历的荣光和失落,似乎都和我没有了关系,我依旧是那个清纯的女大学生,满怀喜悦被几辆半旧的小车披红挂绿接进了这个精心布置的新房,投入我心爱的人儿的怀抱,上课,孕育、生子、种花,一家人挽着手儿在晨曦中锻练,在夕阳下漫步。假如人生不用去执着地追求理想,是不是就不用承受失意所带来的落寞呢?当我越来越因为忧郁的情绪而让爱人和孩子心疼不已时,我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更多呢?
不过假如我是个忧郁症患者, 我一定也是被称为“微笑忧郁症”的那种。不到二分钟的深思默想后,我就冷不丁说出要照相的念头,行动极其迅速的战士立马就拿来了照相机,并推选了最好的“摄影师”给我拍照。我就那样快乐起来了,高高兴兴在他们整整齐齐摆放着高架床的房间中照了不少的照片,并和大家合影留念,其时我正穿了件红夹克,果真算是“万绿丛中一点红”了。
回单位的车上,司机和同行的年青军官一致对我的“高升”表示祝贺,但我总是不由地设想,假如我当年一直没离开校园,又会是如何的生活呢?当然,不从职业而从写作者的角度来说,阅历丰富肯定是值得庆幸的了,我又何必太多地在意得失呢?何况除了偶尔的坏情绪,我的心还是当初那颗纤尘不染的心啊!
我想今夜,我们一家人一定会栽好兰花,让幽幽兰香在典雅的花盆中飘满居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