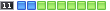“衣锦还乡”辨
刘荒田
在网上闲逛,读到一谜语:衣锦还乡,打一古人。谜底不难猜到:归有光。沿着谜面想下去,一位忘年交的脸浮现脑际。20多年前在旧金山认识他,他平生多难,解放初撂下两个年幼儿子,托亲戚照顾,和妻子流落到香港。他进小报当下层职员,妻子当帮佣,住石屋,惨淡度日。70年代来美,在小印刷厂当工人,直到退休。和他在茶楼聊天,他说最大的遗憾是离开故土后就没回去过,数十年没见过亲骨肉的面。我问,为什么不回去看看?可没任何限制啊!他黯然道:钱呢?什么像样的礼物都买不起,怎么向儿子媳妇孙儿女交代?怕这个怕了一辈子!我还知道,唐人街里,住在破败客栈的单人房里的老金山,从少时当猪仔被卖,直到用拐杖支撑的风烛残年,没有回过一次家,就是总想赚够钱,才打上十口八口金山箱,风风光光地回去,然而,财发不到,人却老了,病了,还乡终竟是梦。原来,衣锦还乡,对在异邦苦熬的游子而言,一直是终极的人生理想。
只是,细细想来,这些坚持“面子第一”主义的前辈,太拘泥了点。衣锦还乡,字面的意思并不如他们所预想的恐怖,它不是非要你带回去、在老屋厅堂里当众打开的几口大箱子,塞满成捆成捆美钞、股票、证券和金灿灿的首饰,也没有规定给乡亲每人送一千元红包加劳力士手表;它只是要你穿得风光些。三件头西装,胸袋的怀表拖一条14K链子,系着纽扣最好,若没有,一根精致的手杖也颇添威风。比起富贵还乡来,“霜打驴粪蛋,外面光”的回归,当然是低层次。不过,好歹还了心愿——不但是漂泊者的心愿,也是家园里依闾的母亲,早岁因新郎在外而和公鸡拜堂,尔后守空闺多年的妻子的心愿。乡是必须还的,家山、故园,就是流浪的目的,生命的皈依。连累累白骨,也要还乡呢——十九世纪中叶,在太平洋铁路工地死去的华工,是后来的同乡会乡亲,在沿途把骨头收集,装殓,再雇船,由招魂幡引领着,运回故乡。
想到这里,感慨无限。第一代移民拥有两个故乡、两种文化(如果能融入第二故乡的话),自豪在斯,苦痛在斯。总被割裂,总要回望,乡愁老盘踞于心,不管身在何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