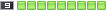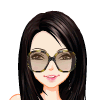近来,每个星期有一个晚上,我都去购物中心,借还光碟,再去超市买一些面包牛奶之类的东西。我喜欢这独自一人的夜晚出行。虽然不能比童话中的公主偷跑去灯火辉煌的舞会,但平凡琐碎的生活中稀少的惬意与宁静的感觉,却常常在此拾得。
我喜欢晚间驾车。闭紧车窗,晚间的凉气关在外面,有一种适意的隔绝与孤独感。街道上变得疏静。夜色过滤了城市的喧嚣和杂乱。偶尔驶过的车灯的白光,无声地滑过被雨水冲得发光的街面。窗外模糊的影像地被抛到后面。孤独地在路上,车上的音乐,车外的夜,都在身边流动,恍惚之间,驶进了另一个空间,世上的一切都变了,不变的是自己。
购物中心里只有超级市场开门,其余的店都关门熄灯了,卖中餐、印度餐的店里,还有人在收拾和打扫。大厅显得空荡荡的,光滑的大理石地面,映着几盏清冷的灯光。大厅的中央,是那些有光洁的木面和不锈钢脚的桌椅,多是空的,零星地有一对人、三两个人坐在那里,或是吃东西,或是在谈话。周末时,我经常带着孩子们来这里吃东西,坐在这椅子上的孩子们的身影,慢慢变高了,他们长成了十几岁的少年。有多久,我没有坐过高级餐厅椅子和优雅的咖啡座了。那些与单身生活相连的东西,连同那些失意、孤寂和落寞,在我的记忆中退色了。我更喜欢坐在这里,有孩子们在身边。看着人们来来去去,听着小孩子的啼哭吵闹,受着旁人的目光,接下无事的老人们搭讪。享受一顿简单的午餐,是平凡又充实的幸福。
超市的灯火通明,顾客很少。晚间是上货的时间,店员们推着上货专用的推车,上面摆着推着一箱箱的货物,哗啦啦地地货架之间穿行。他们不时停下给顾客让道。我推着购物车,小心慢慢地走着,眼光在商品中扫着,不时往车里放进水果、牛奶、肉、饼干之类的东西。下意识地,在心里共鸣着不知是从哪里传出的音乐声。时间就在这情景间消失了。孩子们小的时候,白天时间离不开,只有趁晚上他们睡了,我出来买吃的用的一切,同时也享受片刻的独自安静。那时候,我熟悉了这晚间超市。还记得每次都见到一个整洁斯文、面目端正好看的中年男人,他文质彬彬地推着哗哗作响的货车走过。我想象,他白天在办公室有一份工作,因为有家庭和孩子要供养,晚上又出来兼职,为了多挣一些钱。现在不见这个人了。我的孩子们已经从嗷嗷待哺的婴儿长成了挺拔的少年少女,这里却没有变,还是那些货品,还是那推车的声音,还是那些动听的歌曲。在这一排排货架之间流走的,是岁月、是我花样的年华、是平凡生活的全部。一时,我竟有一种失落忧郁的感觉。但在同时,又有一种心安理得。躲在一个人宽厚肩膀后面,平静地,无风无浪地过着人生,不正是我当初祈祷所得的吗?一家一户,一粥一饭,有儿有女,无惊无险,在我这敏感脆弱的心所能承受和向往的,是终极的理想。
外面的世界,有丰富的、不同的、充满色彩的生活,有很多的人,有面对面的对峙、碰撞、甚至格斗。但是,我跟人们最近的接触,只是对面一瞥,擦肩而过。我没有遗憾,不向往没有过的生活。别人的命运,或许跟我相似,或许大相径庭,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满足于在电影中经验别人的人生,别样的爱,别样的恨,别样的快乐和悲伤。我最喜欢的却是韩剧,那些家庭生活、人情、细小琐碎的种种,让我沉入其中。生活,越简单越好,人情,越丰富越好。在超市的货架前,体验的也是日月人生。我正在考虑买一盒冻酸奶还是冰激凌,听到了一个女孩声音,清脆悦耳的普通话,在跟男朋友议论着买哪一种冰激凌。这对男女,二十出头,时髦的装束,看他们的样子和说话口音,不像是海外长大的中国人,一定是出国不久的留学生。我想起了二十年前。我刚下飞机踏上异国的土地,一对朋友就带我去超市,为我买了很多吃的用的东西,还有一盒冰激凌,那女孩说:澳洲的冰激凌特别好吃。这对朋友一同在一个越南人开的洗衣店打工。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分了手,女孩到另一个城市去了。两个人临别抱头痛哭。男的后来买了一个南美国家的护照,也不知飘流到那里去了。一盒冰激凌,一声乡音,让我想起了他们。带着异样的怀念心情,我从冰柜中取出了一盒冻酸奶。
收款台那里,是个祖母年纪的女士,微胖的身体,花白的卷发。我熟悉这个面孔。多年前她就在这里。记得我们搭讪过,她告诉过我她在晚间工作。或许还记得我,她因疲惫而表情木然的脸,在我招呼的时候,发出了亮光。她有几个儿女呢?儿女有几个结婚了?小孙孙已经上学了吧?这么多年的辛苦,她还没有停下来,还要做多久呢?我问她,你现在每晚都工作吗?她说只做星期一到星期三。她把收据递给我,大而浅色的眼睛看着我的脸,把一声晚安和一个亲切的笑,送给了我。
推着购物车往停车场走,大厅里只剩了一个清洁工人在拖着地板。我成了一个孤单的购物者。手上车里装着不多的货品,从世上的许多的物质中拿来的这小小的一份。购物车的轮子没有走偏,骨碌碌地在空阔的厅间发出一串声音。我踏着这声音走,感觉似喜似悲,似真似幻,实实在在,又恍恍惚惚。
2009-8-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