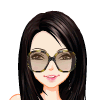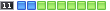外公,倘若您知道这题目,您断然是不愿我下笔的。您离去了这许多年,我这只字不提的情绪却在胸膛里疯长,今天,就权当我凭着这一页轻笺与我们的那些回忆叙旧罢。
[ALIGN=CENTER](一)[/ALIGN]
听母亲说,我这条命是外公捡回来的。母亲是外公最小的女儿,外公白天被扣着帽子挂着牌子满街游行,晚上逐街扫马路的时候,孱弱的母亲不堪承受,贴了大红的决心书,带着十六岁的花季,如同哥哥姐姐们一样,挤进了一去不返的列车。
几番风雨,军宣队号召母亲这样的“黑崽子”要彻底改造:和贫农结合。穷乡僻壤,母亲和父亲借了老乡的一间摇摇欲坠的窝棚开始共度困苦和饥荒。
外公收到母亲数千里之遥寄来的第一封信说:怀孕六个月了,听不到胎心音,老乡断言孩子恐已没有命数。
母亲第一次接到外公的电报说:速归!路费我还!
母亲后来才知道,她回城餐餐小饱的那些日子,外公大多以浆糊果腹,夜深人静,他在街巷里打扫,蹑手蹑脚揭下沿路的大字报大标语,细细致致地舔食纸张背面的浆糊。扫一路舔一路 ,直到天亮。
外公也是后来才知道,母亲生我那天被刁难,是因为母亲看上去太年轻,父亲又不在身边,而不是因为他被剃得狼狈不堪的头发。外公庆幸那天他一直不停地谦卑声明:我是罪不可赦的黑五类,我女儿是黑崽子,可我女婿是又红又专的贫农,这孩子应不算黑崽子。
不红不黑的我一声不吭地诞生,护士好言相劝:不足月,有这么小,活不了几天的,别费心了。我出生的第二天,外公借了辆自行车,把母亲和猫仔儿一样的我接回了潮湿阴冷的地下室。
那几个月,每天凌晨,天仍黑着,外公便小心翼翼护着褂子上的口袋回来,先是择洗着,再是守着蜂窝煤炉子熬煮着,最后母亲和我就有了所谓的“骨头汤”,母亲记得还尝过一次香气扑鼻的“虾皮汤”,一次“菜汤”。至于外公走了多少路,去了多少地方,费了多找周折捡回这些珍品,母亲就不得而知,外公也不讲的。不过,至少六个月后,外公捡回来的是我生气勃勃的笑脸。我那时很安静,唯独被外公抱在臂弯里的时候,就满面春风,笑不拢嘴。外公说:这孩子有心!
第七个月,母亲抱我再次踏上离城返乡的长途,外公站在车窗外呆呆地望着我,满眼是泪,车启动了,他忙跟着走了几步,停下,仍是呆呆站着,竟然忘了挥手和母亲道别。
[ALIGN=CENTER](二)[/ALIGN]
我第一次对外公有了记忆,是五岁的时候,外公带着外婆千里迢迢到乡下来看望我们一家。
运动过去了,他平反了,外婆却因运动中的惊吓和折磨而疯疯癫癫,并且逐日更加厉害。乡下僻静而开阔,外公希望外婆的病能够有所缓解。
父亲和母亲去上工,外公就在家里照顾外婆、我和大弟。印象最深的是外公很执著地教我写字,尤其是毛笔字。刚开始,外公用笸箩装了沙子,削柳成笔,一笔一划手把手地教我。
一天,外公带着我们去挖苦菜,走走挖挖,竟然挖到了一个废弃的烧瓦窑。外公满心欢喜地抱着五六片大块的断瓦回到家,洗干净晾着。又带着我一路小跑到了公社的大猪圈,他跳进去一边给一头大黑猪抓痒,一边悄悄地剪着猪毛。晚上,我要去睡觉的时候,外公仍然戴着老花镜在煤油灯的一豆星火之下,一根一根修剪着猪毛。第二天,我就有了人生的第一只毛笔。笔杆上还有外公用烧红的铁丝烫印的四个大字:字如其人。这是外公每每教我练字的时候都会说的一句话。
外公写得一手好字,我印象里他的信都是用毛笔书写的蝇头小楷。外公幼年就有先生在家中督导他们兄弟几人读书写字,而外公是书画最好的一个。我练字的时候,外公先在沙笸箩里写一个字,写得极慢,接着带我一起“读字”,把这个字的间架结构、笔画笔顺都读透了,他就看我用猪毛毛笔蘸了搪瓷缸子里的水,在被他打磨得方方正正的瓦片上写字。
外公通常都是让我站着写字,并且悬腕,也不得三心二意。我那时瘦小,气力不够,往往都是练得手臂酸软。有一次,外公教的那个字笔画太多,来不及写完,瓦片上的水印就干去,每写到一半我就把字写丢了。越写越急,越急越委屈,越委屈手越抖,最后,我索性坐在地上哭起来。外公一声不响地拾起笔,洗掉笔上的泥土,把笔端端正正放在瓦片上,然后把我拉起来,搂在怀里,一边帮我揉捏着手指、胳膊和肩膀,一边教我一句话: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我止住哭泣,听外公解释,尽管不太懂,但还是觉得很有道理。
外公教我许多这样的名言警句,那时我因着它们琅琅上口而喜爱,现在我却因着它们深彻生活而珍惜。我至今仍是极少搁笔的,写字的时候,也一样是凝神静气,也一样是悬腕站立,写的也一样是外公曾经告诉过我的话。
很长一段时间,我常常写斗方“万春”,外公告诉过我:记着这两个字,记着“枯木前头万木春”的道理:多苦多难,走过去,就是百花争艳万物复苏的春天。
我就写着这两个字,从乡下写到镇上,从镇上写到城里,竟然还从中国写到海外。
[ALIGN=CENTER](三)[/ALIGN]
和外公相处的日子是我心里的痛,也是外公这一生的伤。
我一路奔波求学,从小村,到小镇,在到小县,最后竟然考到了外公的城市,这或许是我与外公的生命之约罢。
外公唯一一次去知青办,是为了能够让我落户城市。我和他一起去了。
知青办的人讶异地接待我们,之前知青办多次上门询问外公,对于运动造成的损失有何要求。外公一一致谢,从未有过任何要求。他总说他平反了,全家都正名了,没收的房子连同家具也都退还了,退休金也补绪上了,五个子女虽然东南西北中,天各一方,但日子都过得去。还需要啥呢!搞运动的人都关起来了,新政府接了这么个烂摊子,不容易,他和家人没什么要求了。国家太平就好。
知青办的主任握着外公的手亲自承诺,保证处理好知青子女的问题。临别时,外公让我给主任鞠躬道谢,给办公室的其他人一一鞠躬道谢,这是外公很早就教我的:要心存感激。
一个月后,我正是落户城市,并且免费进入颇有名气的女四中。
女四中离外公家不太远,我走路上下学。外公的房子是一所古老的独立小楼。外公住在一楼,外婆锁在二楼,沿着旋转的木楼梯向上,三楼原是一个储物的小阁楼,玻璃拉门后,是一个斜三角形的四平米的空间,那便是我睡觉的地方。
每天睡觉前,外公都会上来看看我,帮我掖掖被角。我喜欢隔着门上一个个玻璃的小方格看外面的夜空。有月亮有星星的时候,夜晚就特别的安静美丽。
外公很早起身,对面的豆浆房四点就开门。外公就到那里去和炸油条的蔡大爷聊天,蔡大爷用大竹板夹从大油锅里把炸好的油条加起来放到竹篦子上的过程中,偶尔会有油条断了,掉在地上。外公有了和蔡大爷当时一起住牛棚的友情,也就有了特殊的机会:把掉在地上的断油条带回家。外公会在我起床前回来,并带回我的早餐,那却是他买的,一分钱一碗热豆浆,一分钱一根完整无缺的热油条。
外公是绝不让我吃掉在地上的半根油条的。也有不少时候,他没有早餐,只看他喝白水,不用问就知道,那天凌晨蔡大爷手准,没有油条掉在地上的。
也许他等的时间不够久吧,我建议自己买早餐。外公欣然同意。那以后,我早晨起来,就可以在最下面一级楼梯的角落找到两分钱硬币;就可以在排队买豆浆和油条时望见外公在蔡大爷身后帮忙的身影;就可以坐在便道上大口喝豆浆,大口咬油条的时候对着探出头来的外公粲然一笑;就可以在去上学之前高高地挥动手臂,隔着售卖窗口,隔着油条豆浆,隔着热气缭绕,隔着人声鼎沸,和等待半根油条的外公无声地道别。
好景不长,外婆的病越加严重,不再如同以前躲在家里哭闹背语录,外公开门给她送饭时,动作稍慢,外婆就冲出来,一改以往委屈申诉的样子,更开始往外冲,开始幻听,开始摔砸东西,开始打人,她满心似乎都是愤怒。而我就成了她斗争的对象,她听到我“告发”她,“诬陷”她。她疯起来扑向我的时候,力气特别大,外公每次都是挺身而出,几乎和她滚在一起。我常常是在外公“丫头!跑啊!快跑啊!”的喊声里,逃出家门。尽管如此,身上脸上带着伤痕去上学的情况还是屡见不鲜的。直到有一次,我的手臂被外婆的剪刀刺得鲜血直流。我捂着伤口跑到就近的医院,却身无分文,也不知道如何就诊。一个头上包扎着纱布的中年军人帮我付了医药费,临行时还硬塞给我十元钱。这件事惊动了学校。外公被请到了校长办公室。
几天后,外公和学校达成协议:我开始轮流在有条件的同学和老师家住宿。每家一周。周五晚上交接。
一晃几年,我没心没肺,在吃百家饭穿白家衣乐百家事的生活中仍旧快乐而健康地成长。那些日子里,我被一个个普通而拮据的家庭温暖着呵护着,懂得了人间真情的含义。我的学习成绩也名列前茅。开家长会应该是外公最高兴的日子,他早早地来了,坐在第一排的第一个座位上,座位是按照学习成绩排列的,桌子右上角贴着一张方形红纸,纸上写着名次和我的姓名。外公每次散会后,都会小心翼翼地把那片红纸揭下来,边对边角对角地折好了,郑重地放进他的中山服的上衣口袋里,再扣上纽扣,最后用手掌拍一拍。
然而,现在想想,那些年的大多数时间,外公的心却是煎灼于那植满无奈、痛楚和悲戚的每个日子里的。
每个周五下午,我一放学就看到外公坐在学校门口对面的石阶上。我就抱着书包和盛着日用品的小提包和他坐在一起等下一周我入住家庭的人来接我,学校安排好了的,我埋头学习,从来不问,谁来接我就高高兴兴和谁走。外公却担心,仔细问过上一周的情况,再叮咛我下一周寄居人家的礼仪小节,大多都是一样的嘱咐,大多都是一边叮嘱一边叹息,大多都是一边叹息一边深深地自责着,直到来人接我了,他就满脸激动地颔首点头,说许多感谢的话,然后愣愣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望着我在夜色中远去的频频回头的身影。
那时候,他的头上、脸上和手上已常见许多伤痕。并且他要我答应:“永远都不跟别人说起你外公。”我是很听外公话的,从那时起我没有和别人提及过外公一个字。很久以后,十分想念的时候,也只是在心底里迸发出那一声呼唤“外公呵!”
[ALIGN=CENTER](四)[/ALIGN]
终于让外公惭愧的心情可略微释怀的是我考上师范学院,住进学院宿舍的那一天。
外公连走路带倒车两个多小时,抱着一网兜东西,爬了六层楼,来到我的宿舍。抚摸着我的床,我的桌椅,我的壁橱,他激动得两手发抖:“丫头!好样的!你熬出头了!”他原本还想说些什么的,可嘴唇哆嗦了好一会儿,一双被松跨下垂的眼睑遮住一大半的眼睛里含满泪水。他竭力地克制着,转身解开网兜,一套崭新的粉红色洗簌用品,一套餐具,一条毛巾被,还有一罐他上午为我炸好的肉丁儿酱。他本想给我留下些粮票和零钱的,我告诉他我现在已经是在培养的国家干部了,每个月有三十元助学金,还有三十斤粮票,十五斤粗粮,十五斤细粮。他感动得拍拍我的肩膀:“丫头,好好念!别辜负了国家!”
之后,外公特地写了一封长长的感谢信,亲自送到校长室,并一一向正副校长、正副主任和我的任课老师们致谢。我是从班主任那里得知的,听得出她被老人深深打动着。
为了能够保证仍在边疆的弟弟们可以继续读书,我每个周末开始给学校附近的几个孩子做家教,少有时间回去外公家探望。外公每周日下午会来看我。每次都会带一罐肉丁儿炸酱,有一次竟然还带了一整罐麻酱,那时候每户人家两个月才分得一张麻酱票,两张麻酱票才能够买一瓶麻酱!我于心不忍,但外公坚持说我正在长身体,我吃了比他和外婆吃了更值得。外婆已经疯得不成样子,外公不让我回去,他的日子必然很痛苦,一提起外婆他的目光就瞬间黯然失色,满目苍凉,让人心碎,我也就很少再问。每次站在校门口那盏昏暗的路灯下送他走,目送外公那微微前弓的背影一脚深一脚浅缓缓慢慢地走远,直到消失在黑洞洞的长巷,我就想不停地呼唤他:“外公!外公呵!”……
我即将毕业的那年冬天的一个中午,传达室的大爷急火火地把我从校图书馆拉出来:“你外公住院了!”我心里一颤!“外公!”
冲进市传染病医院的加重病房的时候,我看见外公身着病号服躺在显得大的出奇的病床上。外公的单位派了人轮流守护外婆,外公说:“不碍事儿,你好好念书。”
从外公的病房出来,医生叫住我说:外公的病是肝硬化晚期,腹水很厉害,挨过不了两周了,要家属做准备。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从医院走到邮局的,晚冬的风撕扯着我的头发,拍打着我的衣襟,抽碎了我满脸的泪水……
六封电报发给姨舅们和母亲:外公病危,速归。
外公执意不允许我请假,我只好每天放学去陪他一会儿。他喜欢听我讲学校的事情,我就滔滔不绝地讲给他听,从老师讲到同学,从课堂讲到宿舍,从体操讲到文学……他合着眼很专注地听,偶尔会微笑,那微笑好难得,让我心里不住地流泪。外公说过:有骨气的人,有泪不轻弹,要哭,也只哭给自己听,哭完,抹净眼泪,路照样走,事照样做。外公是要我做个有骨气的人的,我记得的。
第五天,我到医院的时候,护士把我拉在门外:“你们家大人怎么回事?!老爷子挺不住了!上午输的血,中午就全便出来了!你家大人呢?!”我哽咽着,望着她:“我想,他们,在路上……”
那天,外公看上去很疲惫,他脸色蜡黄,颧骨凸现,我坐在椅子上,继续假装若无其事地讲学校的故事。讲了不到五分钟,他就示意我停下来,我靠近他,他无力地抬起手,指指枕头下面声音虚弱地说:“丫头,给你的。收好了,别告诉别人。”我探手进去,取出一个用外公常用的手帕包裹得严严紧紧的小包儿。外公不要我打开,看我放在大衣内侧口袋里后,他就要我回学校。
我多么希望能够多陪他一会儿!
“外公,你想吃什么吗?”外公费力地睁开眼睛,目光滞滞地望着我,嘴唇动了动,又动了动,竟突然笑了一下:“护士不让吃……病号饭一点儿味儿都没有……算了罢……”他又重新闭上眼睛,就在我转身之际,他喃喃地说:“好多年没吃过红烧肉了……”
我的泪水几乎要夺眶而出了!
记得在乡下的时候,我问外公什么最好吃,外公就告诉过我的:“红烧肉最好吃!”我那时还信誓旦旦地和外公勾手指头儿:“等我长大了,一定要给外公吃红烧肉!”
红烧肉,竟然在外公的心里记挂想念了几十年!
从医院出来后,我没有回学校,直奔外公家,在外公的抽屉里找到了一张猪肉票。第二天凌晨四点我就到了肉市门口,我排在最前边。那一夜,风尘仆仆的母亲赶到了,二话没说,她去了医院。之后姨妈和舅舅们也相继赶到,一并去了医院。
我抱着二两猪肉寒风里跑得满身是汗。在同学家借住的时候,我每天都会帮着做饭炒菜,红烧肉我见过几次,记得还清楚。捅开了前一晚封好的煤球炉子 ,细细地洗,慢慢地切,我一丝不苟地为外公做红烧肉。
我把香喷喷的红烧肉放在小饭盒里,用围巾裹好揣在怀里赶向医院的时候,太阳刚刚露头。想象着外公一口一口吃红烧肉的样子,我激动了一路。
进了医院,我在楼梯上奔跑,一层、二层、三层……我带着一身寒气闯进外公的病房。外公的床是空的!我浑身打了个冷颤!“外公!”
护士说,外公昨天半夜被送到急救室。
我趔趔趄趄撞倒急救室门前的那一霎那,整个人就轰然坍塌!
门内传出的是母亲的、姨妈的和舅舅们的哀号!他们撕心裂肺,一声接一声地呼唤着:“爸爸!”
我一脸泪水逶迤,一切声音却都哽在喉间。
推开门,双膝跪着,抱着层层围巾内透散着余热的红烧肉,我一步步靠近外公……外公走了,他没有来得及等到丫头的这一盒红烧肉……
母亲告诉我,外公原本要等我的,昏迷中仍唤着我,一声又一声。注射了两次强心针之后,舅舅决定不留他老人家了,外公是一边唤着“丫头”,一边离开的……
外公走了这许多年,我只字未提过关于我对他的记忆,关于我对他的想念,我仍是他听话的“丫头”罢!
外公的那一方手帕包裹着的是五十六斤粮票,二十七斤细粮,二十九斤粗粮。我至今珍藏着,一如他交给我的模样。还有许多他留给我的东西,我仍呵护着,如那把褪了色的粉红色塑料梳子,如那个绿黄相间的网兜儿,如那个发白的小军挎书包……但我如何能够把一声呼唤深藏在心底里这么许多年呢!
总以为,岁月能够风干了这沉甸甸的一声呼唤,谁料此时此刻,这一声呼唤赫赫然陡立在心头,竟然又立刻揪惹出我如此奔流着放纵着的汩汩泪水了!
就让这一声呼唤喷薄而出罢!
就让这一声呼唤迎昭世人罢!
就让这一声呼唤成就丫头对你的一腔思念罢!
“外公!”
[img]../images/fileType/jpg.gif[/img]此主题相关图片
[imga]../images/upload/2009/02/04/211732.jpg[/imga]
图片来自网络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