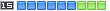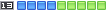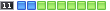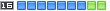《你这人兽神杂处的地方》 作者 陈善壎(3)
头香带来一块方巾,是她绣了好久的蓝方巾。她请郑玲转交土质。说这是表记,土质懂的。我们猜想,表记定是信物了。不知道土质用什么方式回应头香的;郑玲把表记交给土质后不久,就听说他们要结婚了。
头香要在鸟节结婚。鸟节这天地上撒玉米,树上挂粑粑。鸟跟云彩一样从空中飞旋而下。这在山外已经死了的节日张家村年年过,以致鸟都记得这天。它们记住了友好的山谷。天才朦朦亮,屋上树上石山上满是鸟。这天全村吃素,无论老幼都去蓝天下敬鸟。手头的高粮粑粑、荞麦粑粑、玉米粒粒撒完了就随意坐下来享受鸟的欢乐。头香选在鸟节这天结婚,来的客人不比皇家婚礼少,服饰华丽的客人满山都是。她没娘家人,伯娘邀拢几个婶姨唱应由她娘家人唱的歌,唱得头香泪流满面地笑。哑婆婆送她一块雕有鸟和花的琥珀,看上去是很有年头的东西。郑玲用自己喜欢的浅绿丝绸披巾做礼物,说贵重远不可与哑婆婆的礼物相比。婚礼没排场,新郎新娘大干一碗酒和大家一起敬鸟去。土质把头香送他的表记系在头上。头香也系着类似的蓝色方巾;那或许就是土质回她的表记了。
鸟节这天人也吃粑粑。人吃的粑粑有枕头那么长那么大,其实就是特大的糯米做的粽子;外头包着笋壳叶,到吃的时候切成一片片。在禾坪里吃。动口前要扔一点到空中,有鸟接住那是好兆头。这多半是仪式,不见有鸟接住。上了天的粑粑无一例外落回地面来。当然可以掷向树,鸟也不接,正啄食的鸟反倒惊飞起。晌午过后的活动实在些,去前山一块巨石上查看谁放的粑粑被鸟吃得多。鸟吃谁的多谁的运气好。我放的粑粑原封未动;郑玲放的粑粑渣都没有了。头香跳起来,大叫“小陈嫂好运啊”。
鸟节第二天,村口无端落下一个炸雷,闪电在进村的路上犁开一条三米长的沟。这天谭石蛟带了几个民兵来抓哑婆婆。他对七斤说,公社收到举报,那婆婆是逃亡的二十一种人,就躲在你们村子里。七斤想敷衍又没办法敷衍,好在怎么找也找不到哑婆婆。大家都庆幸找不到她,盐长说昨天给头香送完礼就没见过她了。这个无所从来无所去的哑婆婆!
哑婆婆睡的戏台本是清彻的,谭石蛟去搜捕时戏台上有十几条巨蜈蚣游弋。有一条从高处掉进他颈窝里,又弹起来咬他一口。后来毒发溃烂,他左边太阳穴留下一块终生的疤痕。
谭石蛟走后我们都去戏台。看到哑婆婆留下的图案;画得很大。头香看着那些图案阴郁地说“爷豁列”。我想这就是哑婆婆所说的了。我已懂得些土话,“爷”就是“我”;“豁列”是“去了”“走了”的意思。哑婆婆留下口信“我去了”是跟我们打招呼,免得我们着急。
头香的预言被后头的日子证实了,郑玲的运气处处比我好。我用三斤谷换一斤绿豆给她熬水清热解毒。她清热解毒了,我被控倒卖粮食挨斗。斗争会开过好几回,我都是主角。村里的地主份子和富农份子不过是陪斗。斗争会都是谭石蛟组织的。在台下喊口号的人,动手捆人的人是他从山外带来的民兵。这些人都是作田汉,他们捆人之前问过贫协主席九龄“出工哪个下手?”回答是“小陈嫂下手;小陈哥做事懒泡懒鼓的。”民兵们就把阶级仇恨发泄到我一个人身上,不捆右派份子不捆地主富农专捆我这个工人阶级。谭石蛟自己没被捆过,不解捆得这紧,这家伙三几个钟点为什么不喊痛。其实捆麻了没什么了不得的。难受在松绑。血液回流手臂的过程让人好汉不起来。不过松绑在散会之后,山外的人都走了。给我松绑的是村里的朋友们。能使谭石蛟畅快一下的场面他见不到。
后来我们走了。使我们非走不可的那些事件是另一种色彩的记忆,也就不说了。
我们是摸黑走的。
那天七斤去公社开会回来,把谭石蛟抓我们的布置告诉了土质,土质告诉了头香;头香就告诉郑玲了。我们就走了。山外发生的一些事情告诉我们“走”。
有些事情永远历历在目。我推着轮椅上的郑玲去公园的路上,会想起曾经在一个漆黑的夜里牵着她的手走过的崎岖山径。
她没有坚持带走诗。我把诗稿藏在楼上窗户边的墙壁缝里打算日后再回来取。那个时侯我们选择的不是诗而是活着。结果一离开就是几十年,自以为是的打算都成泡影。郑玲一度企图重写那诗,但不管如何努力,也没办法找回山中的感觉。
几十年中我们没有忘记深藏于山中的友谊。这段友谊或许成就了后来的诗人。这一点山里的朋友不知道,今天研究郑玲的评论家也不知道。都知道她的苦难,不知道苦难中有一颗发出光热的天体。
我一直惦念他们也没有忘记过藏在那里的诗稿。但我的能力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直到一九九六年秋天才找到机会回了一趟张家村。
因为路远,我计划先把车开到不可再前行的地方一个人进山,让陪我同来的朋友留在县城耍。那天毛毛雨,雨天进山的难度我是充分了解的,只指望几十年的光景已有了一条像样的水泥路。从城关镇的布局看,比我们在这里时进步多了。有一条水泥路进山不是没有可能。
车拐进通向张家的路了,心底某处沉积着的一些东西被搅动然后浮上来。路口的右边,建于十九世纪很不错的长亭没有了。我还记得长亭里落款是一九四二年由洋教士写的白话布道文的开头,“来来往往的人们啊。当你们在这长亭休憩的时候,请静下心来听我对你们说说人生是什么好吗。”布道文很长,我从没读完过,我就一直不知道上帝是怎样理解人生的。再走进些,已经知道水泥路莫想了。不过还是有一段路可以行车。
前面两边宽阔的山坡本是荒地,当年由驻军开垦出来种花生。驶过这片山坡就没有平地了。只在山的中间穿出一条坐车散骨架的路。走了不到一半无论如何颠簸不下去了。我只好下车了。逶迤进山的是由脚板开辟的也可以说不是路的路。
面对有如久别故人的山,虽有毛毛雨,我倒怡然起来。我走着,极悠然的样子。并不苦涩地生发出离开那夜的回忆,那夜从记忆的根部爬上来。像一只蜗牛,极慢地接近;忽然它变为蜥蜴一跃而起,那夜便封锁了眼前的一切。
那夜太黑,低头向地看,除了看不见,什么也没有。只能抬头望天。天光衬出山影,靠山的影子分辨路可能的转向。我牵着郑玲一点点地向估摸的方向移动。不是一步步移动,是一点点。黑暗提供的距离不足一步。我要确信我站的地方坚实。我不知道她站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一步之外是深渊还是沟壑。我要保证她突然往下掉时我能抓住她。在这条路上,即便不过是米多深的浅沟,沟底也布满刀片一样的石刃;还有蛇蝎群集。白天这条路是明明白白的,黑夜里却莫测诡秘。树在狂舞,变幻出各种可怖的形态。咆哮的石直指我们,让人联想充斥罪孽的三生。好象从地狱入口处突然腾飞的鹰,黑夜里弄出的响动可击溃草寇。宗教诞生之前的精灵醒了,狞厉的妖鬼就在身边。我们依靠自己给予自己的教育,依靠在黑暗中扶持着的体温坚持。这种情形下仅凭触觉和听觉已经足够了,我们不能看也不必看,轻易就适应了不用眼睛。但我知道她的眼睛一定跟我一样睁得大大的。什么都看不见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不要用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我们的眼睛,习惯为光而睁着,希冀在没光的地方找到光。
住在张家村,无论去哪里都要走长路。去还是回都是长路。刚来那时期,她问我“还有好远啊”。我实话实说还远得很。她说你说远我就走不动了;你总是不懂得哄。后来我就改说不远了,就在前头。翻过那山就到了。这夜我不断地说,别急,天快亮了。就要亮了。星星或许会出来。或许会有另一个走夜路的人的火把。我还做些不着边际的畅想。做些畅想可以使我们有力气。
我牵着她慢慢移。
我唱“我流浪在贝加尔湖滨”。我的歌声在暗夜里就是火炬。我说这是列宁流放中最喜欢的歌。山谷完美的共鸣弥补我胸腔的狭隘,我的歌就非常地好听。我们自己把艰难步履导演成勇往直前光芒四射的旅行。她听到歌勇气倍增,还说些十二月党人的事。她已做好了迎接前路种种挑战的准备。但我还是不会不说“天就快亮了”,再熬熬,必能见到第一道霞光。
我没哄她,后来天真的亮了。在解放军开垦的花生地那里天已让我们看得见路,看得见还没醒的城关镇。有了光的路多么好走啊,虽是只剩下一点点气力了,至少能看到周围是什么。
我拿出盐长帮我搞到的生产队的证明,买了当天第一班车的车票,两个人像贼一样溜上车。车在道县停下来吃早饭。我下车买油条在车站旁边的墙上看到一张令我窒息的“贫下中农就是最高法院•杀字013号”的布告。
直到车过道县好远才松了一口气。
连绵不绝的红色语录墙在公路两旁像站岗的红卫兵一样向后面退去。农舍的外墙无一不刷满标语。处处红旗招展,有集市的地方口号声震天。我们本就疲惫不堪,这样的枯燥更使我们睁眼闭眼地睡去。迷朦中我在想昨夜的事。认为这样的经历足够构筑一个仅属于两个人的文化;窄狭、封闭、顽固而不需要传播的文化。
我在山谷中一脚高一脚低。面对千古不易的画图,一路沉浸在当年直接的实在中。与那段艰辛的日子比,今天反倒显得无聊而琐屑。
到达张家村后我先去井边洗鞋。四棵桂花树不见了。闻到牛粪沤稻草的味。我没有急于进村。我知道我的朋友已近在咫尺。我要把这个一度以为老合投闲的地方跟记忆比较来。多了几根电线这是一眼就见到的,这些电线从树上过从屋顶过。然后一排新屋,既宽敞又亮堂。但和原先的古屋比,少了云山自许的孤傲。村后的靠山虽茂密,总觉得深邃奇谲不如从前。放养了许多黑山羊,这是他们新发展的副业了。山羊在巉岩间攀缘异趣于麂子、果子狸的出没。洗好鞋后我往回走登上高处,下面是曾被闪电犁出沟的地方。放眼望去,山峦依旧。烟雨中远景一如从前,不是寻常笔墨。但没闻到桂花香。平整的青石路明显失修。从所站的地方望去,门闾外的围墙早已破旧。戏台上堆积着牛粪,不用说戏台和围墙上画的人物花草了。我有些迷惘。为什么不关某家的事没人管?为什么应关每家的事没人管?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