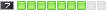走在故乡的路上
自从三姐在1959年出嫁后,在香港的毋亲就不回乡过春节了.因为在菲律宾谋生的父亲改了在春节时回香港渡假.那时都是我和哥哥陪祖母在农村的老家过春节.祖母总是在我们回家前就做好了过节的糕点.我们一进门就吃到可口的糕点.我们那条村除了除夕吃团年饭外,在年初一还要煮一桌菜拜祖先,并要蒸年糕,台山的年糕叫发高,其意思是发财旺相,这发高是过年必备的糕点.那时我和祖母睡在大门口的房间,哥哥睡在小门口的房间,煮饭烧菜都在小门口的厨房,哥哥是个孝顺的孩子,他总是很早就起床帮祖母烧菜和蒸发高,我小时贪睡,总在听到祖母大声地品评发高时才起床,祖母蒸发高的技术不好,总是时好时坏,她看到没有裂缝的叫银碗,有裂缝的叫微笑,裂缝大大的叫龙嘴.我和哥哥在旁边暗暗好笑,其实我们最爱吃银碗,但在年初一我们都不敢乱说话,那时父母虽不在身边,但有祖母相伴也令我们感到温暖.那年代华侨都怕儿女在香港这个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里学坏,多数让儿女在祖国读书.我们村有很多象我们一样的孩子在台城读书.那时哥哥在台山一中读高中我在台城镇一小读小学.
1959年祖国开始经济困难了,但我们没有感受过刘荒田先生笔下的饥饿,因为华侨除了有汇票购物外,还有优待证,当时农村是非常困难的,哥哥每个周未都带着米,猪肉,咸鱼----等等食品回去给祖母,但在1961年哥哥去香港后这个工作就由我这个六年级的小学生做.那时回乡要到台城东边的单车站搭车回去,当时单车多载货很少载人,有时从早上等到中午才搭到车回家. 一般我星期六回去,陪祖母过一夜,星期日吃过早饭才回台城,祖母很欢喜我帮她梳头,有次梳头时她对我说,知道这样子,当年嫁个卖菜佬还好一点,祖父是在广州高第街娶祖母回来做四姨太的,父亲很小的时候祖父就去世了,祖母从来也没讲过娘家的事,也许来到这个穷山村就没回过娘家.小时不知祖母话里的苦楚,长大后每想到祖母的话就凄然泪下,令人感到多么凄凉和寂寞.每次回台城我都先帮祖母梳梳头才出门.祖母带着我走过塘头潭村,走过板[没法写土字边的板]潭矿场,再爬上一个叫平顶山的小山岗,才让我白己走,在路上目不识丁的祖母总是叫我要好好读书,说一字值千金,祖母又叫我回到台城要听外婆和大姨的话 .我走过了三角塘来到了松树林边,回头看看,慈祥的祖母还孤独地站在那里看着我,她总是等到看不到我时才回家.
经过松树林的路有150米左右长才到四九旧圩,那松林路两旁的松树又高又大,大风吹来一阵阵呼啸的松涛声听得令人心慌慌,常常那路只有我一个人独行,小时大人都爱讲麻风病人的故事来吓小孩子,想着越想越怕,由慢行变快行再变小跑等看到四九旧圩才定下心.虽说害怕,但看到松树下那又红又大的毛牙婆[一种野生的草莓]还是抵抗不了诱惑摘十个八个吃.这些'毛牙婆'比士多啤梨还好吃.
走过四九旧圩来到四九新圩的单车站等车,那又是一件苦事,有时等得不耐烦我就搭11号车,自己行.如果我刚上路看到有载客的单车我会给多点车费请单车工人载我回台城,否则我会幔慢走过田坑村,香头坟村来到合水桥边.在盛夏的时候,我会走到诃边用清凉的河水洗诜脸,洗洗脚,然后斜坐在河边的草地上休息一会才再走路.每次看到那清清的河水湍急地流向远方,看到蓝天下飞翔的小鸟,我就想到了父母想到了哥哥和弟弟,我就感到自己似丢队的小鸟,觉得无限的悲伤和孤独.小时我多么希望自己能象别的小女孩一样可以依偎在母亲的身旁.但这样简单的愿望对我来说是遥不可及, 我多么希望那哗啦啦的河水能带我到达遥远亲人的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