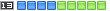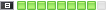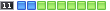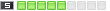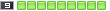文/心之初
一九八七年,四人帮歇菜十一年了,说话真挚而还可爱的胡总书记不明不白地下课一年多了,过完“而立”的我,带着自己的稠怅和人家的羡慕,走他乡。为“把自己的脑袋扛在自己的肩膀上”,我用说不了十句完整英文句子的外语言能力,拿着四十美元,怀揣着 “寻找可能”的梦想,茫然而高兴地来到美国。说真的,那时我都不知道“美国”是什么的干活,因为我不爱学英文也不想发大财。
我费了牛劲把托福只考了547分(离获得“资助”的资格要求的最底分数差三分),我进了研究生院但没资助(关系穷学生的生死存亡)。为了能读硕或读博,我得力挣在系里找份RA(研究助手)的工作。那时我根本就说不了几句英句,默念着“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口号, 走进了汤姆.卡瓦里教授的办公室。
我开门见山(背好的台词):有没活?(是不是把教授吓一跳我不知道)地问他。活?教授用他那大而深的眼睛看着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美国人看到我们那个时代的中国英雄的感觉),问:“你会干什么?”,我当时心在说:“没有不会的?(人没饭吃,会有什么不会?这大概也是宝总理最近总结的中国文化四大精华的第一精华)”。许下 “先用一个月,不要钱”的愿。就这样,卡瓦里教授让我进了他的实验室,说好先试一个月。从此我俩开始了 “两口子”式的“攻城不怕坚”。
我有了干活的地方,学位可以开读,心欢喜。
卡瓦里教授只比我大四岁,博士后刚当大学助理教授,拿到美国能源部的一笔钱,搞“负电子剥离”的研究(就是把氢原子身上的那个电子弄掉)。他的实验室刚开始建。我的头一个任务就是做些用于屏蔽电源的铁皮盒,老天也算有眼,正好上大学前我就是钣金工,做铁皮盒轻车熟路。画线,下料,咬边,敲打,成盒,生产出的铁皮盒简直就像个工艺品。当我把做好的铁皮盒第二天一早就拿给老板看,他拿在手里,转一转,翻个个,眼里有点亮地端祥了好一会(我当时的那个紧张!),然后问我:“你做这盒子用多少时间?”,“两个小时吧?”,我答。他又问我:“你的两个小时值多少钱?”,我说:没钱。他乐了(他忘了说好我头个月没工钱)。我结结巴巴地问教授:铁皮盒做得不好吗?他笑笑:不,做得太好了,只不过不值得花两小时。后来我才知道,美国人做铁皮盒,咬边是钻眼上螺丝,小时就是钱。
两个月后,卡瓦里教授发我俩月的工资(尽管他可以不发我第一月工钱)。说真的,当我拿着近两千美圆,突然有种人的感觉(人的劳动价值)。超我预想的钱,成了我的美能达相机7000i。我来美国的第一个梦想,两个月就实现了。我,一年级助研,新入学的研究生的首富和卡瓦里教授开始了近五年的“如同结婚”般的导师和学生的关系。他叫我名字,让我叫他汤姆。教授还是教授,学生还是学生,但这平等亲切的彼此称呼让人觉得我们像是生命相互托付的战友。教授话不多,我话也不多。好些时侯我俩一起干活,特别是晚上,互相都能听到对方的心跳(我眼眶都有些潮)。
美国搞实验物理的教授真能干,上课讲方程,下课做实验,上房能安装电缆,下地能铺设水管,画图纸,上车床,修设备,买东西,全自己来。四年多的日子,我俩成了我们物理楼里“任何时间都能找到的两个人”。
导师有三个孩子,但在我跟他读学位的四年多,他每天八点以前就到办公室,晚上通常是后半夜一两点回家,从没有星期六,星期天有时也工作。从他身上我看到美国人是怎样在做科学。我学会好多“能干”,但弄坏了我的中国胃。
卡瓦里教授从来不多说什么,有时我犯了错,他也不过多责备,只要求我:同样的错误别犯两次。记得有一次我在连续工作十五六个小时以后,不小心,按错了一个电扭,烧坏一个上万美圆的稳压电源,我难过极了,卡瓦里教授还安慰我。一千多个日子,我们的实验室从无到有,我们的实验也做出了些结果,我们的文章也发表在了美国最高级别的专业杂志(PHYSICS REVIEW)上。我们没拿多少钱,只是默默辛苦做我们自己选择的工作。
我离开导师已经十七年了,十来年前当我在IBM获优秀奖时,我打电话告诉了老师,他把我们一齐发表的几篇论文用一个包裹寄给我,可惜,我都看不太懂了。那些论文里,有我人生最美的一段年轻。到现在,每当我看见美国人,把手按在胸前,凝视着他们的国旗,我的眼睛都常常是湿的,因为我曾也有过但又走远了的心中的神圣。
后来我又经历很多“生活”,但我永远地记住了我美国的导师-------汤姆.卡瓦里教授给我说过的话:“生活只要是你自己选择的,就不应该有任何报怨”。
时不时想起席暮蓉写的《青春》,但我并不太伤感。我有过自己选择的生活。
前几天搬家,又看到那些论文,我的眼角,又一次湿了。
2/7/2008写
5/28/2009改
[em70][em70][em70][em70][em70][em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