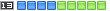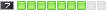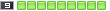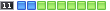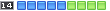文/心之初
我哥是个精神病。得病那年,张铁生和他一起考大学。不过,我哥究竟是不是真精神病,对我一直是个哥徳巴赫猜想。到现在,我也没搞清。现在他活得不错,花甲了,还给我吹,他在什么地方,刚玩过一个小姐,嘻嘻。还说追他的中年女很多。他比我强,结过两次婚,都离了。没有香火,只有欲火。终生不念书,活在朴实里。
从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初, 活到当下,没当官的爹也不用自己的脑力或体力,虽一直被认作是精神病并真当个精神病人,不用批林批孔不用评水浒不用唱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也不用唱“也许我倒下再不能起来”更不用下海也不用练滩或许还真是种活得容易些的方式,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一个有清楚头脑的龙传人,这些年谁不曾火里滚水里趟风里来雨里走,上山下海过洋,总得风雨总得春秋,连数“度”的工夫都没有;老得鼓劲老得泄气,奔向那看不清的远方。
一九七三年的隆冬,快到毛主席的生日了。一个黄昏,天铅灰,没有血红,下着雪,快黑了,我给“大救星”写完贺寿诗的祝福板报放学回家,快进我们家属院时,看到路上走过个穿件不白衬衣的汉子,右手挥着本红语录,迈着踢蹋的步子,脚和大地保持着亲蜜,腾腾地走走来。有点近视的我眯眼定睛一瞧,吓我一跳;哇,哥。我赶忙上前。
我俩一起进的家门。记不清我妈当时是什么反应了,因为那会的人成天都在“反应”,所以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较强。我爸是啥都不管,我姐在乡下,我还上高一。只因我哥太雷人了,家里顿时成一团,一片忙乱。我哥冻得只有出的气,有些“鱼”的眼上翻,嘴里还念叨着李瑞山(当时陕西革委会主任),也许是他就靠这一口气,才走到家门,活了下来,活到现在,幸福地当了个精神病人,生活过改革开放三十年,啃了几十年的国和家里老和小,现在还能领些低保,妈给点零花,弟给些赞助,守着亲妈天天唱“有妈的孩子是个宝”。我叫他的大宝,明年花甲。新中国的同令人,和祖国双赢。文化大革命,革出多少精神病。
冻得快僵的我哥回家两天后,人还像死猪一样,在床上打着呼噜。我已坐上从西安去阳平关的火车,去调查我哥在广阔天地炼红心怎的就炼成了精神病?我“滑稽时代早长大”(这引号引的是我自己的话),我妈在家“泪眼望儿儿不语”。我们家靠我妈独撑,实在出不了远门。老爸不管事只管写他自己的诗。大儿不醒,“小棉袄”在下乡,小儿寒冬腊月出远门,当妈的心,得怎样坚强?
我哥在陕西南郑县(汶川地震到陕西的那个县)的某公社某村下乡。我从西安坐火车到阳平关,大约八小时,再换汽车到汉中,再换汽车到南郑,再“远征难”,最后到哥村。我哥下乡那村,二十几户人家,全穷。四十多岁的生产队长接待我,给我吃碗热面,给我说情况,晚上就和他,他老婆他娘还有他的三个娃睡一个炕。那天的觉,睡不着。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最难大概是同住,和“创造历史的动力”同一炕,近距离听“动力”呼噜,我平生是第一次。这么多人睡一床,男女老少不一家。为了我哥,我得熬着漫漫的长夜。急了就唱: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你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你唱。毛主席当然是听不着的,他那会大概也不和“身边的赫鲁晓夫”同床了。现在想起文革,我还微微冷颤,因为“反常”,多少个家没安宁。那会人都是个蚂蚁在站起二十多年后,又听让我们站起的人的话,在热锅上慢慢爬着。爬,比站起不走道,毕竟还省些力气。胡里胡涂恍恍惚惚,几回回想起些毛主席的书,几回回想起些我和我哥。
我哥的小名是四九加一,大名则非常震憾,现在网语叫“雷人”,不知我那教汉语的爸是怎么想的。给我哥起名时,我爸正下岗,他非国民非共产。下岗下得自己说不定都想烈火中永生,烈火却不让他永生而只让他下岗(那会叫失业)。
我小时侯就嘴巴利索,拳脚不好;我哥正和我相反。他个不高,好像和庄则栋差不多,打乒乓和老庄是一个路数,是他们学校(可能还不止)的多连冠。他的眼,有点“鱼”,焦距短,看得宽,一瞪,一般人就得倒退三步。在我们家属院,算是赫赫有名,有他罩着,我在岁数小些的人里,便用我的小嘴,随便吹,别的孩也只能听着,没人和我抬杠。神吹,谁不喜欢?就像现在说的:瓜长得好,全是党的政策好。我给小伙伴们吹,党的政策就是我哥。
我哥的嘴虽是笨点,但人还是很灵,玩槤枷,抡小刀,甩三节棍,打右勾拳,打起群架一次就能招来上百号人,振臂一呼,人流就呼拉拉地向前。那有劲的时代!打架,就用你的身子压着另一个身子,用你的拳头打另一个身体。人都说老子英雄儿好汉,可我爸并不英雄。我哥,那会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小时侯在家,我爸老打他(对了,不英雄的爸就爱打自己的孩子,打出英雄),但我哥铁骨铮铮,从不认错,一上初中,就不回家了,我常想他,因为我爸打不着他,就打我,我从小就和我爸智斗,我没我哥好汉。
文革时,时兴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大多数人都坐火车。我哥不,楞和几个人徒步从西安走到延安,再从延安走到北京,见完毛主席,好像也没握着主席的手,又从北京走回西安,冻得跟个龟孙一样,还给我看他一个月的全部所得:一张“恩来弯臂”把“太阳”弯在腰间(小宝书上有像)的革命照,两眼圆睁,目光如炬,眺望远方,大棉袄裹身,心潮还起伏。给我看完,还拿啥一包,揣怀里。我是个不上学的小学生,只能叹气,把崇拜藏在心里。
一九六七年,祖国山河就一片红了,刘邓司令部玩完了,共产党夺了共产党的权,不劳动的劳动人民欢天喜地天天过没肉的年。红文兵们干得不赖,走狗烹吧,领袖大手一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城里,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我哥我姐就和浩浩荡荡的年轻男年轻女一起,去战天斗地,去寒冬腊月里盼春风。那会的春风好像不光是不度玉门关,好像是哪都不度。
我哥插队到了陕南,同组俩光棍。都说美女爱英雄,那是现在,英雄都是鸟英雄。我哥是真“英雄”,在“广阔天地”大作为,今天把这个灭了,明天把那个给砸了。他不太爱动脑,时不时被警察活捉,名字在西安火车站的高音喇叭里念,被妈领回家,每次都鼻青脸肿。青退了,肿消了,就给我吹他的厉害。在家吃上几顿饱饭,就又回“天地”去“厉害”。。。。。。
晚上睡不好,白天就不好。听一上午才听懂我哥他们生产队长讲的情况:我哥在他们区考了那年“考试上大学”的考,考了第一,考的啥没人知(好像主要是哲学),他“第一”后被通了知,然后他就在他住的黑屋里傻等,等了一个月,啥都没等着,他就“精神”了。“精神”得全村的人都躲,家家戶戶的门,都顶上大木头。队长领我去我哥住的那地方去看,土屋全黑,烟熏的黑,狗都不去,只有“盼天明”的人在那里盼天明。
告别了生产队长,握了握他纯朴的手,谢过他的接待,我又去我哥他们的公社。知道了我哥等不来大学入学通知的原因,是因为公社武装部长的女儿顶了他的名额(我记不清是哪位好心人告诉的我)。问世上哪里有公?只在纸上口号里。
我哥疯了,我爸气得半死又不得死,我妈也病倒,我夜里守着口吐白沫的我哥,曾有过次撕心裂肺的长哭:为什么,要遭这样的罪?寻常百姓,养个儿子,上不能报国,下不能孝父母?听毛主席话,疯在乡下。一人疯,全家便没了家的欢乐。
有一天早上,我哥嚎哭。等我起来,他已人事不知,桌上药瓶瓶盖狼籍。我忙叫上我的两个朋友,用担架把他抬到病房,医生说:要再晚一小时,我哥就完了。因为我,我哥没完,胜造七级浮屠,社会主义多了个寄生虫,八十五的妈现在还有个每天晚上给她端洗脚水的儿子。母亲为了不把负担留给我和我姐,坚强乐观打麻将,前些日子还给我说:赶上国泰民安。
在我哥被抢救的那个星期,没知觉时被灌肠洗胃,醒了医生就用四条牛皮带把他四肢牢牢绑住。我陪我哥也住了一周精神病院。病院里是一片“精神”,没“精神”的我早上就听那些电椅弄出的尖叫,看被拖过的条条“死猪”,握眼直人的手,共祝领袖万寿无疆。有歌舞团的美女,翩翩着《白毛女》,情真地唱:我要活。
半年以后,我哥活过来了,不打杀他人了,回家了,眼直了,说话呜呜,但最听我的话。我家最后托人费了大劲才把我哥户口弄回城里。重新变成城里人,我哥的病就好了大半,还和我一年参加了“革命”。他被分到建筑公司,当了个改革开放前的“农民工”。我上大学那年,他又“精神”了,吃劳保了。有次我问他是不是华子良,他还会幽默:地雷的秘密你知道就行了。这二十年我回去过四次,每次我都大包小包给他拿些衣物,他总跟我鞍前马后,给我讲他的生活和思想,每次都跟我决战乒乓决战象棋,每次完了,说上句:唉,人跟人,就是不一样。每次我走,他都眼泪汪汪,对我说:我会照顾好咱妈。
人的心里,都有些深深。我哥说这世上,就我把他当个人。零六年回去的时侯,我妈说我哥又和他的第一任前妻有了瓜葛。文革,不光革出调侃,还革出各种没法想象的坏人。我哥很怪,时而正常时而反常,离不开女人又找不着女人。
我郑重地问他:“你爱你的前老婆吗”?
“我爱”,他说。
“你愿意去上门吗”?我再问,
“我原意”,他答。
“你要多少钱”?
他说不上。我说,那你赶快去和你心上的人儿商量,再给我说,一口价。后来,她那人儿不接受他。三年了,他不再入“情”了,每天带个手机到处游,每天给我妈做些事,混个吃喝。
前些日子,看了本张洁的散文集,名字是《我们这个时代肝肠寸断的表情》。写过《爱是不能忘却》的她,“希望死了喂野狗,在个没人的地方”。她生在芦沟桥事件那年,七分之六的人生,是新中国时代。
我常觉得我们的人生,好像是活在个六合彩的时代,个人的前途成长命运生活不知是凭手气脚气还是运气?我上了大学,是碰上了运气,得以走远,但又时时想家。回家的时侯,和亲人和朋友亲热完长久的别离后,竟是说不出话。
5/26/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