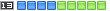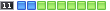文/心之初
美华文坛有个小鼠标像,叫天活活。
活在中国和活在美国,对我我这个快三十年在中三十年在美的人来讲,就像刘罗锅的主题歌里的老百性,心里边,有杆称。心里的称,并不只称轻重,也称人生。人生有轻重,轻重在心里。重如泰山,轻如羽毛; 脚下的土,天上的云。
小时侯就能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保尔说的“人的一生该怎样度过”背得一字不差,但长大也不知“人的一生”是啥?突觉,人一生,就是天活活。天天能照着自己想的方式活或能适应所拥有的环境在活,就算是幸福了。幸福就是人想。
年轻的时侯,老想上九天揽月,也想下五洋捉鳖。简简单单的人生,弄得重重叠叠飘飘渺渺。历史最悠久的国家,有着世上最多的人;有着世上最多的云山雾罩酒足饭饱;最多的“纸船明烛照天烧”和最多的“春风杨柳万千条”。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到处跑。跑天涯,跑海角,天上地下,跑着找宝。当年告别亲妈走他乡的时侯,妈妈她还很高兴,因为没用的娃娃才跟着妈。而昨天心里绞着痛输上长串号码拨通妈妈电话想跟亲妈说上几句话,妈告诉我:我正忙着打麻将。
游子穿在身上的衣,也不知换了多少?穿的人和缝的人,都有种念想。穿衣的孩早穿不着亲娘缝的衣,但他不一定忘了心里的娘。日子让人吃了很多肉,但走远的情怀,时不时地在心里朝着你袭来。
二十年前的这会,刚到他乡不久,住在个和海明威有着同爱的美国老太家,七八只大小猫在房里喵喵,电视里数不清的“八九点钟的太阳”在天安门广场野外睡觉。白天,他们唱歌,用着他们瘦小的身子。老太问我:我看了好几天了,为什你们天安门广场里,那么多的人,没有胖子?我还真回答不了,但我哼起了:我爱北京天安门,老太听个半懂。老太早已走了,带着她不明白的问题。我可爱的祖国,已有了很多胖子,胖得流油,胖得发愁。我想告诉老太:中国也有了胖子。
在远离故土的他乡,日子不停忙活着人,人忙天活活,天天为自己活。没当总统的中国男人,大多都克林顿了,没林顿艳福,有了克林顿白头。他乡的天活活,得靠脑子和身子,脑子里有些玩意,身子里有些力气。说中文的嘴,也就个吃饭的家伙。我和我的那片故土,“十年生死两茫茫”,廿年死生梦长长。他乡有他乡的快乐,他乡有他乡的清澈: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侯,不应为想(不是理想)做而做不着的事而悔恨,也不应为成败而懊恼。能驾鹤炕头,就挺幸福了,因为比生命珍贵比爱情价高。
在他乡美国,人的大半生,可做很多事,有事让你若狂,因为你挣到很多钱,没费太大功夫,也不担惊受怕;有事做得让你欣喜,因为你就爱做那事;有些事让你做得刺激,因为你生活所迫。还有些事你压根就不想做,做过却好象真懂了生活。新旧社会两重天,中美两国一天(天空)连。社资两字不用吵,东倒西歪各自偏。
满世界的龙传人,横着断山,野着茫茫;高原寒,炊断粮,不是英雄汉, 千难不怕难;我们不忘记,我们天活活。
写给四月二十二
[em14][em14][em14][em14][em14][em14] |